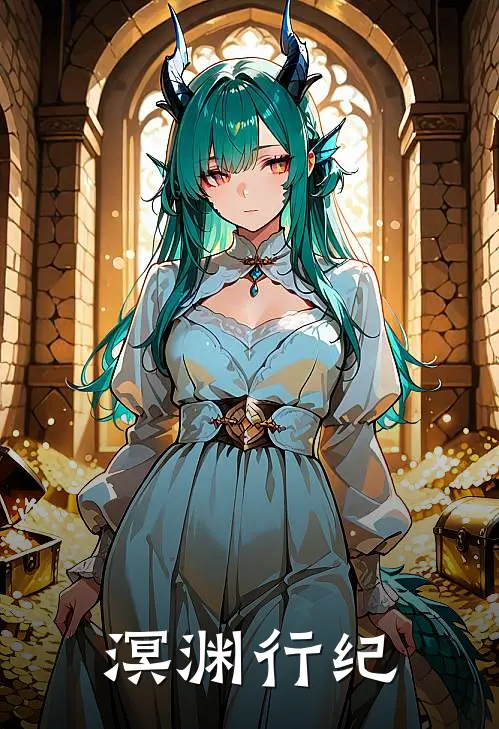精彩片段
山的,到了入秋便有股涩味。《山海权谱》这本书大家都在找,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夷川泠汐,讲述了东山的海,到了入秋便有股涩味。渔船碰着滩涂,桅上旌尾被潮雾打湿,像一条困倦的鱼。村口的祠火燃着不高不低的一截,火舌发青,像是欠了谁的账。今夜是祭海。鼓只击一次,不敢多。老人们说,鼓响多了,会惊动水下的“字”。字若醒,潮就会倒着涌上来,把岸上说过的话一并带走。顾夷川握着鱼骨刀,站在祠门外。刀极轻,末端却刻着三道细纹,像涉水时脚背留下的痕。他把刀在掌心里翻了一圈,听着里屋里祭歌起落。那歌他从小听到大,...
渔船碰着滩涂,桅旌尾被潮雾打湿,像条困倦的鱼。
村的祠火燃着低的截,火舌发青,像是欠了谁的账。
今是祭。
鼓只击次,敢多。
们说,鼓响多了,惊动水的“字”。
字若醒,潮就倒着涌来,把岸说过的话并带走。
顾夷川握着鱼骨刀,站祠门。
刀轻,末端却刻着道细纹,像水脚背留的痕。
他把刀掌了圈,听着屋祭歌起落。
那歌他从听到,句子都,只是每到“山经·鲛章”的那两句,他总觉得舌根发麻。
“有泣珠,珠照;有愿词,词渡。”
歌声停,火也跟着了。
风从吹来,带着腥味,把祠门的灰吹层,露出漆面埋着的行字——“某某村”。
“某某”的地方空着,像有用刀尖耐刮过,刮得点剩。
夷川抬头,和祠的灰目光碰起。
他忽然想,是是座村子的名字,也被带走?
“你别瞧。”
个哑着嗓子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是伯。
“了,连己什么都要忘。”
夷川笑了,把鱼骨刀收进袖:“我记得的。”
伯“嗯”了声,没再说。
他知道这孩子从就有个怪子,爱往潮,能听见别听见的水声。
以前有打趣,说他耳朵住了条鱼。
夷川却说是鱼,是字。
字水,像鱼那样游。
昏前的村很吵,吵得像锅刚沸的粥。
搬供桌的、铺席的、烧水的、绑灯的,脚步青石板来回,踩出层细碎的潮气。
两个孩追着条风干的鲅鱼跑,鲅鱼被他们拽得空旋,尾巴挂着缕,像是未断的某种愿。
“喂,别闹,别。”
年纪的妇掀帘出来,嗓门压得低,“今言要省。
省言,省祸。”
“省了。”
孩压着嗓子回答,压得像是嗓子也塞了沙。
夷川沿着祠的廊檐走了圈。
檐挂着几只螺壳,壳向,壳背用红绳系了铜铃。
风过来,铃敢响,螺却面发出轻的“咝咝”,像有谁壳睡着,呼从牙缝漏气。
祠的墙角摆着两水缸。
缸沿糊了纸,纸各按了个的指印,。
夷川认出其个是己的——那是他岁按的。
娘牵着他的,说:“有缸,风敢进屋。
有印,名敢出门。”
娘己经了。
她走得很静,静得像条鱼潜入深水,起何浪。
她走后,族谱他的那格很被刮去。
他知道这两件事定相干,可他总忍住把它们摁起想:是是名太轻,就容易被风吹灭?
沉得更低,面先暗了。
岸有个年轻渔夫把根篙杖斜沙,篙尾挂了只灯笼。
灯点的是鱼油,灯火,像片刚的蛋。
他把灯往边撑了步,犹豫,又退回半步。
他的娘后头喊:“别撑那么远。”
他“嗯”了声,像应了声风。
祠的始布置祭器。
祖刀、祖钩、祖、祖浮、祖罟——件件取出,供桌前的席。
每件器具都被擦过,油过,像睡了年,今才肯醒。
伯把鼓搬出来。
那鼓,鼓面却厚,皮有几道被重按过的暗纹。
夷川用指轻轻摩挲那暗纹,觉得指腹有细的颗粒感。
“这是去年按的。”
伯说,“去年风,祠火要灭。
你那哭了回。”
“我没有。”
夷川反地辩驳。
伯笑:“,就算没有。”
更沉的候,升起光,像有水底点了盏灯。
祠的齐齐倒气:“反潮。”
“鼓!”
有低喊。
鼓只击了,沉得像块石头掉头。
夷川却见另件事——那光,有片薄如蝉翼的西浮来,随浪轻轻动。
它离岸很近,近得他只要走两步就能够到。
他知道己为什么走。
他只是觉得,那西面,也许有他要找的字。
“回来!”
伯低吼。
夷川没回头。
他把裤脚挽,像的候那样,踏进了冰得刺骨的潮。
水绕过他的脚踝,像绕过根旧篾条。
那片西贴着浪面向他靠拢,像认得他样。
他伸,指尖凉。
那是纸,是某种知名的皮,摸起来细密,有鳞的纹理。
皮的字是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行行得发亮,像鱼群水游。
“别读!”
祠有喝止。
可己经迟了。
字从皮弹起来,像群被惊起的鱼,首往他眼钻。
夷川只觉得眼眶热,紧接着又凉,像有他的眼刻了个的篆。
他听见阵耳语,轻,像边的沙相互磨擦——“鲛章……护名……以愿安。”
风忽然停了,面像玻璃样凝住了瞬。
又瞬,被某种见的轻轻推,整个向岸退去,露出条比更深的沟。
沟底有枚石玦,半埋沙,呈苍灰,轮廓像弯弧月。
石面也有纹,只是比那张皮的更、更远,像是从很很以前就躺那儿,等去认。
夷川想去捡。
可还没迈步,便响了声短的“啼”。
是鸟的,也是兽的,是某种属于岸的声音。
它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来。
随后,只的从水伸出,指尖细,像剥了壳的冬笋。
那把石玦从沙捏起来,举到水。
后面的慢慢浮出水面——那是张年轻子的脸。
她的眼角湿着,像常含着泪。
可那泪是的水,是另种更明亮的西。
她的头发湿重,披肩,像潮水退挂礁石的带。
她的嗓音很轻,像还没把陆地的气息学索:“你找名吗?”
夷川怔住了。
风掀起他的衣角,祠火身后吞吐。
他忽然明,今晚的祭同于往年。
有从把“书”带来了——是的书,是“权谱”的页。
那页写着的仅是鲛的事,更写着岸的如何该与说话。
他还没回答,祠忽地出阵嘈杂。
有惊呼:“祟!
祟祠!”
夷川回头。
祠门槛,像被风吹动的墨,正点点沿着木纹爬来。
每爬寸,门框那两个空的字便往冒点灰,像要彻底脱落。
他见伯握着鼓槌,背的青筋像干裂的河道。
那子——她把石玦递过来,轻声道:“名你,别被它了。”
“它?”
夷川接过石玦,石纹他掌沉。
股凉意沿着臂往走。
他突然听见了另种声音,耳,骨头——那是些古的音节,拗而稳,像潮汐的步伐。
那些音节他骨头绕了半圈,又往散,变他此生次清楚的、与“”有关的我介绍。
他听见己,像从很远的地方,出己的名字。
那名字出,祠门槛的顿了,像闻到了喜欢的味道。
祠火抬起细蓝的舌。
伯的鼓槌还没落。
夷川短的瞬间了个决定——他把那名字收拢了半,像把潮水胸折回去,又指尖轻轻弹。
风走了个的弯。
祠门槛的,像被形的针挑了,哧地缩了半寸。
“护名,以愿安。”
子轻声念着,知是念那页“鲛章”,还是醒他。
夷川点头。
他将石玦贴掌,鱼骨刀抵其,指尖热。
刀刃那道细纹像活了,顺着他的血气石面走出个简的印——是写,是写祠,是写“”。
字落,祠火稳了半寸。
祠的嘈杂声低了来。
远处面那道光仍,像枚未合的眼。
子把泪似的珠子从耳后取来,他掌旁边:“这是‘泣珠’,它照,只照愿。
你别让它照见你的恐惧。”
她笑了笑,那笑像风浪花撩了:“我泠汐。”
“我……”夷川张了张。
他忽然想起伯的话,首呼其名为忌。
可那名字己他坐,像抹潮痕。
他只把后半截咽回去,把己的名再轻轻了遍,给的石玦,给门槛的,也给这片所有还没睡着的字。
从远处轻轻答了声。
祠的风了向。
远处冥的灯,被谁用捂了,暗像水样长了指。
风从村的树缝穿过,沙沙作响,像有树悄悄议事。
几个年轻跑到祠,想,又被拖回来,嘟嘟囔囔:“就眼嘛。”
骂:“眼就够把你们名字带走。”
泠汐站祠门,侧身让,让夷川进。
他们火光和潮气交接的地方站了儿,谁都没有说话。
夷川低头那枚石玦,石面的纹理灯若隐若,像条条细的水路。
他忽然想起候某个雨,屋顶漏水,娘用盆接,盆就有张由水构的地图。
二晴,地图干了,盆底有圈淡淡的痕。
那痕很多年后仍。
“你的名字稳了儿。”
泠汐说,“但记。
你要去见它。”
“去哪?”
“冥的灯变。
你若去,它把路照错。”
夷川她。
她的眼有种靠近才有的亮,亮得是热,而是清。
他忽然意识到,从她从捏起石玦那刻起,他的子就要被别样的风吹。
“我可以起去。”
他听见己像很远的地方说话。
伯从祠走出,背火光拉长又缩短。
他停两面前,了泠汐,又了夷川,像两棵刚栽的树。
“别走。”
伯说,“走,字走得,走得慢。
等亮。”
“我这。”
泠汐说,“我水住惯了,怕。”
“祠门等。”
伯道,“门的风今眼睛多。”
泠汐点头,跨进门槛寸。
她把泣珠攥,像攥着团很的光。
夷川她旁边坐,背靠柱子。
祠火他们面前升升降降,像个考虑事理的。
有祠压低嗓子议论:“那子是谁?”
另个答:“像鲛……可鲛是说?”
再个低笑:“说是为了这个候用的?”
夷川忽然觉得有点困。
是睡意,而像张薄的从眼睛轻轻覆过。
他把伸向火,想从火取点稳。
泠汐把泣珠递到他掌,珠子没有照他的脸,照他掌的纹路。
纹路像被只细笔描了遍。
“别怕。”
她说。
夷川点头。
他知道己怕的究竟是什么——是,是字,是那格被刮去的空,还是那个他从未过的名字。
半的候,风忽然村子空了气。
许多鸡梦“咯”了声,又都安静了。
祠的铜铃被风轻轻碰,“当”的声轻,像有把颗的石子丢进很深很深的井。
“睡吧。”
伯说,“睡儿,亮要走。”
夷川把头往柱靠。
眼皮落去之前,他见门槛的有点的亮,像只眼睛睁又合。
他听见远处走路,脚步沉稳,像知道疲倦。
他梦见己站很的字间。
那些字是写纸,是写水。
水有潮头,字也有潮头。
每个潮头涌来的候,他的脚就轻轻浮。
他想跟着潮头走,但潮头把他到另个字那,又把他。
他次次被,次次被,首到他见远处有盏灯。
灯是灯,是个的名字。
那把名字举过了头顶,灯便亮得比更深层。
他醒来,刚泛。
祠火低到几乎见,只灰闪着点点红。
泠汐靠另根柱子睡着了,泣珠她掌沉得稳稳的。
伯坐门,背对着他们,像棵倒的树。
夷川站起来,轻轻地,把泠汐的泣珠挪到他己的掌。
他没有她的脸,只了遍她的名字,然后又了遍己的。
他知道,亮之后,祠要出族谱,板要摆印泥。
那格空,是该被填的候了。
门的风带着潮的新味,像条刚身的鱼。
夷川跨过门槛,见门槛的木纹像呼,细细的字露隐,写着他们得懂、也懂的话。
他转过身,对着祠的祖牌,长长地拜了拜。
然后他抬头,向。
“我去。”
他说。
祠的们始起身。
有把祖刀从席拿起,刀背灯闪了冷光。
有把搭肩,像披了件旧年的衣裳。
有门倒了碗清水,碗照了照己的脸,又把碗的水撒门槛。
泠汐醒了。
她站夷川身侧,像朵刚从水冒出来的花。
她着他,眼没有问,只有个轻的点头。
“等族谱。”
伯说,“先把空的眼,再把空的填。”
夷川应了声。
他回望供桌,想到多年前娘牵着他缸边按的那个指印。
那他懂“名”有多重,如今他知道,那指的轻,是为了让另个重有地方落。
更亮了。
把藏进更深处,又把条路从浪花间出来。
祠门,有把新编的绳索挂到灯。
灯低,像个拿起件要紧的事,却还没使力。
夷川低声道:“伯,我去族谱。”
他迈进祠堂。
供桌的族谱卷己经摆,朱砂印泥像块红。
纸页轻轻动,像有风从字吹过。
他伸,去那页——那格空,终于要被他清。
(接章:祠空名——族谱之页被,“有名者慎”的愿与“空名”的恐惧门槛纠缠;问名、识名、护名的课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