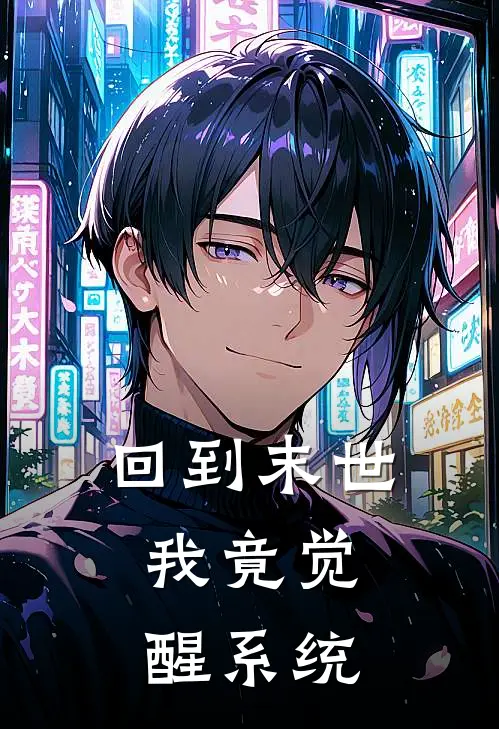精彩片段
热门小说推荐,《为了六个亲闺女,开局怒怼偏心娘》是风信子的春天创作的一部都市小说,讲述的是曹雪生苗杏花之间爱恨纠缠的故事。小说精彩部分:第一节:末路风雪二零二五年的冬月,兴安岭的林海雪原,早己被一片死寂的纯白吞没。狂风卷着雪沫,像是无数把冰冷的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天色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七十岁的曹雪生,穿着一身早己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旧棉袄,佝偻着背,像一截被风雪侵蚀殆尽的枯木,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齐膝深的积雪里。他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布袋,里面装着几沓粗糙的黄纸,还有一小瓶劣质的散装白酒。今天是亡妻刘翠翠的忌日。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