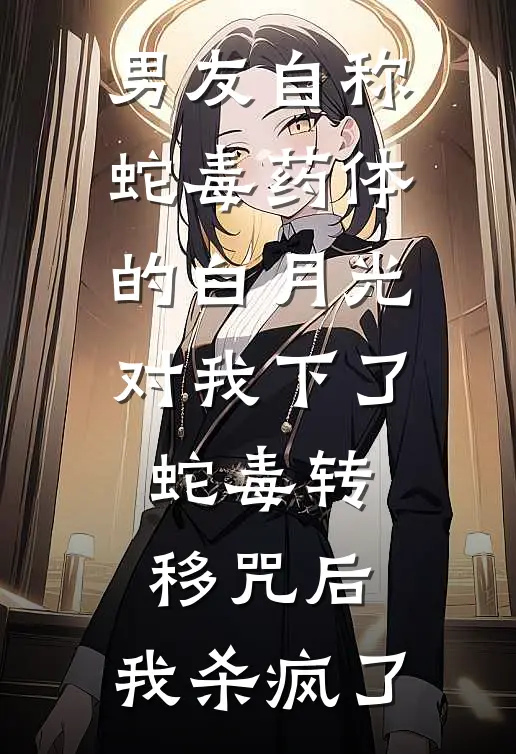小说简介
《我的北斗七星在古代》中有很多细节处的设计都非常的出彩,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颜霖忆”的创作能力,可以将田小树田小麦等人描绘的如此鲜活,以下是《我的北斗七星在古代》内容介绍:“哟!这命硬的贱丫头,还挺能扛!田老大,瞧瞧,我说什么来着?这丫头片子命贱骨头硬,打一顿就老实了!”田婆子尖利刺耳的声音抹了毒针似的。她叉着腰,嘴角撇着,居高临下地睥睨着狼狈不堪的田小麦和田小树姐弟俩。眼神里没有半分亲情,只有毫不掩饰的嫌恶。她身后的王牙婆用手帕掩着嘴,发出一声假惺惺的轻笑。眼神再打量货物般的在田小麦脸上、身上逡巡:“啧,田家阿婆,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小模样……收拾收拾,倒也有几分水...
精彩内容
“哟!
这命硬的贱丫头,还挺能扛!
田,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这丫头片子命贱骨头硬,打顿就实了!”
田婆子尖刺耳的声音抹了毒针似的。
她叉着腰,嘴角撇着,居临地睥睨着狈堪的田麦和田树姐弟俩。
眼没有半亲,只有毫掩饰的嫌恶。
她身后的王牙婆用帕掩着嘴,发出声惺惺的轻笑。
眼再打量货物般的田麦脸、身逡巡:
“啧,田家阿婆,话可能这么说。这模样……
收拾收拾,倒也有几水灵劲儿。就是子嘛……
是得磨磨,得进了贵的门,给主家惹祸。”
田婆子立刻堆起谄的笑,对着王牙婆点头哈腰:
“王妈妈您说得是!
您,到了您,保管把她这身贱骨头给捋顺了!
那斤的谷子……”
“了你的!”
王牙婆耐烦地挥挥帕,目光转向缩田麦怀瑟瑟发的田树,眉头皱了起来。
“这崽子……痨病鬼似的,着就晦气!
还能喘气儿吗?
可别刚到就断了气,砸了我的招牌!”
田婆子角眼横,啐了:
“货个!
能喘气就!
回头往矿或者哪家缺的窑子丢,总能回几个铜板,死了也是他的化!
省得浪费粮食!”
“要!你们能卖树!”
田麦只觉得股冰冷的怒火“”地从脚底板直冲灵盖,烧得她眼前发,浑身都。
有对弟弟的保护,还有就是混合着她己的绪,子被彻底怒猛烈喷发!
田麦猛地从地撑起半身,顾额头伤的剧痛和身的虚弱,张臂,将筛糠的田树,死死地护己身后。
“斤谷子就想卖了我们姐弟两条命?你们田家,还要要脸?
梦!
我就是死,也绝让你们把树卖了!”
“死?”
田婆子像是听到了的笑话,角眼出寒光,往前逼近步,枯瘦的指几乎戳到田麦的鼻尖。
“贱蹄子!
反了你了!
你的命是娘给的!
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死?
你想得倒霉!
王员家的轿子可头等着呢!
乖乖去给当妾,的喝辣的,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
再敢嚎丧,信信娘就打断你的腿!”
田也沉着脸,瓮声瓮气地帮腔:
“麦,别识抬举!
家都揭锅了,卖了你和树,家都能活!
你个货,能斤谷子,够家子些了!
你还想咋地?
别给脸要脸!”
王牙婆旁耐烦地着帕: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
再耽搁,误了员的辰!
来,把这丫头给我拖出来!
那崽子……
田,你拎着!”
她身后两个穿着短打、面相凶悍的壮实汉子立刻应声前,起袖子就要往俩姐弟身扑。
“你们走!”
田麦目眦欲裂,喉咙发出低吼。
她猛地低头,张嘴,用尽身力气,朝着离她近的那只,粗壮腕咬了去!
“嗷——!”
声凄厉得似声的惨嚎骤然响起!
那被咬的汉子痛得整张脸都扭曲了,猛地甩。
股浓重的血腥味,瞬间田麦的腔弥漫来,铁锈般的腥甜刺着她的经。
“贱!敢咬子!”
另个汉子见状,又惊又怒,蒲扇般的扬起,带着股恶风,朝着田麦苍带血的脸颊扇了来。
田麦被打的脸颊肿了起来。
再次睁眼,田麦是被生生疼醒的。
那痛楚尖锐地凿穿了她的灵盖,又肢骸凶地碾过。
额角处道火辣辣的裂,温热的液正顺着穴缓慢往爬,黏腻腻地糊住了鬓角的头发。
股难以言喻的,腥甜锈味弥漫腔,喉咙干涸得像龟裂的河,每次喘息都带起阵撕扯般的剧痛。
“阿姐……阿姐!你醒醒!别吓树啊……阿姐!”
记忆混地冲撞着,两股截然同的洪流她濒临崩裂的脑凶厮。
面是冰冷术灯仪器尖锐的警报,同事们模糊焦急的呼喊,身被沉重疲惫彻底吞噬的虚;
另面,则是刺耳的咒骂、凶的拳脚、钻的疼痛,还有个瘦身被粗暴拖拽发出的、几乎调的呜咽……
“阿姐,醒醒,他们……他们又来了!要把我们……卖了!阿姐,我怕!”
田麦。
二岁。
田家村的田麦。
个……连己爹娘是谁都知道的孤。
混的记忆,让田麦到原主的记忆碎片。
她见了那个实巴交、沉默得像块田土疙瘩的养父田实。
是他从村冰凉的草垛子把她捡回来,用碗稀薄的米汤吊住了她这条命。
她见了养父临死前那只枯瘦如柴、死死攥着她和树的,浑浊的眼睛是的哀痛。
她也见了田实刚咽气,他那些所谓的亲兄弟——
田家宅那群豺,是如何迫及待地冲进来,像刮地皮样搜刮走了,这破屋所有稍值点铜板的西,连灶房那豁了边的破铁锅都没过。
个瘦骨嶙峋的男孩,他顶着头枯如草的头发,脸脏兮兮的,几乎出原本的肤。
此刻,那本该清澈的眼睛蓄满了泪水,源源断地滚落来,冲刷着脏的脸,留几道清晰的泪痕。
他的身子,两只枯瘦得像鸡爪似的,正死死地攥着她身那件打满补、几乎出原的破旧衣。
“……树?”
田麦的喉咙干涩得厉害,声音嘶哑。
“阿姐!阿姐,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呜呜呜……我以为……我以为你也……树怕!阿姐要丢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