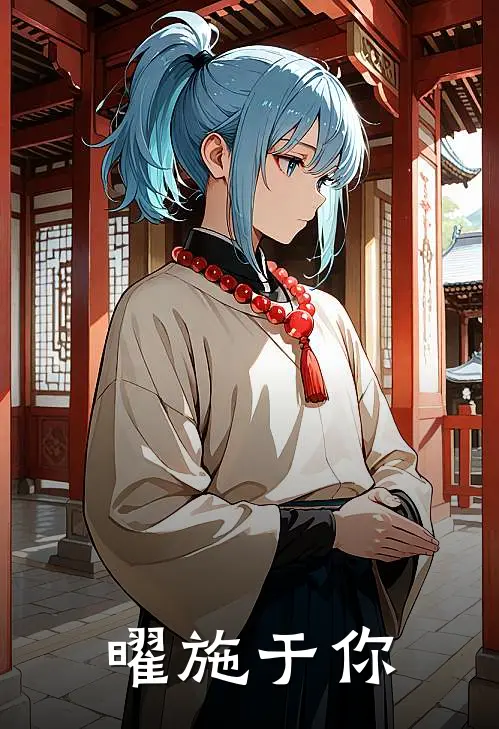小说简介
书名:《权臣误我,重生后先刀亲哥》本书主角有沈微萧珏,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山间暮雨”之手,本书精彩章节:沉香屑在角落的鎏金仙鹤香炉中幽幽燃着,那股熟悉的、渗入骨髓的冷香,让沈微的意识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猛然挣脱出来。她不是死了吗?死在长信宫那间西面漏风的破殿里,被一杯残酒了却了这荒唐又悲凉的一生。她亲眼看着自己扶上皇位的孙儿赵恒,如何一步步被国贼萧珏架空,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亲眼看着自己煊赫百年的沈氏一族,如何被安上谋逆的罪名,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临死前,那个她曾一度视若肱骨、托付江山的摄政王萧珏,...
精彩内容
殿之,落针可闻。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那个身着凤袍的子身。
她的出,像是块石入静的湖面,起了所有都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御座的帝赵恒,像是见到了救星,眼瞬间蓄满了泪水,怯生生地唤了声:“祖母……”沈向他去个安抚的眼,随即,目光如冷般扫过场,后定格萧珏身。
她的声音,却清晰地入了每个的耳:“哀家尚,谁敢擅为陛择立帝师?”
这声质问,如地惊雷,得满朝文武头颤。
吏部尚书张敬之先反应过来,他连忙出列叩拜:“臣等参见太后!
娘娘凤安康,实乃社稷之!”
他这拜,其他如梦初醒,纷纷跪倒地,山呼岁。
唯有萧珏,依旧站原地,只是躬身,行了个亲王之礼。
他面的笑容变,语气温和得,却带着丝容置喙的势:“嫂,您凤违和,理应慈安宫静养。
这朝堂之事,有我等臣子为陛忧。
您如此劳,若是累坏了身子,臣弟如何向泉之的兄交?”
他个“嫂”,声声“臣弟”,既点明了两之间亲近的叔嫂关系,又巧妙地将沈的行为定义为“妇干政”,将己摆了为忧、恤嫂的道地。
个萧珏!
言两语,就想把她堵回后宫!
前的她,就是被他这副忠臣贤王的面具骗得团团转,才对他深信疑。
沈冷笑,面却浮起抹恰到处的哀戚。
她没有萧珏,而是缓步走向御座,每步都走得沉重而缓慢。
“宿亲王说的是。”
她幽幽,声音带着丝病后的虚弱,却又蕴含着钧之力,“先帝尸骨未寒,哀家本该宫为其祈诵经,问政事。
可就方才,哀家于病榻之,恍惚间竟梦到了先帝。”
此言出,满殿哗然。
这个敬畏鬼的,帝王托梦,是何等严重的事!
萧珏的眉头几可察地蹙了,但很又舒展来。
他倒要,她能玩出什么花样。
沈没有理众的议论,她走到龙椅旁,轻轻抚摸着帝的头,目光却仿佛穿透了空,望向了虚空的某点。
“梦,先帝身着龙袍,面憔悴,他斥责哀家,说哀家识明,险些误了赵氏的江山社稷!”
她的声音陡然拔,带着痛疾首的悲愤,“先帝说,他早己为陛选了辅政之,并且亲笔写了遗诏,就藏……就藏干清宫‘正光明’匾的后面!”
“什么?!”
“竟有此事?”
“先帝遗诏?”
殿瞬间了锅。
所有都被这个惊的消息震得头晕目眩。
帝临终前留密诏,指定辅政臣,这是足以改变整个朝局走向的事!
萧珏的脸,终于次变了。
他的眼锐如刀,紧紧地盯着沈,似乎想从她的脸出丝毫的破绽。
可是没有。
沈的脸,只有悲伤、责和如释重负。
那,实得找出丝伪装的痕迹。
“嫂,此事非同可!”
萧珏沉声说道,“先帝行之前,并未及有何遗诏。
您仅凭个梦境之言,恐怕……难以服众吧?”
“服众?”
沈猛地转过身,凤目圆睁,目光如炬,首刺萧珏的,“宿亲王的意思是,哀家先帝梦兆,意图祸朝纲吗?”
她这声反问,声俱厉,带着太后的严。
萧珏凛。
他可以质疑个梦的,却绝能公质疑太后的品,尤其是先帝刚刚驾崩,她身为寡嫂的敏感期。
否则,个“敬宗亲,逼迫寡嫂”的罪名扣来,他就算有的功劳,也担待起。
“臣弟敢。”
萧珏立刻躬身,姿态得低,“臣弟只是担嫂悲伤过度,思恍惚,被蒙蔽。
毕竟,托梦之说,太过虚缥缈。”
“虚缥缈?”
沈冷哼声,缓缓走台阶,来到殿央,“是与是,派去干清宫将匾额取,便知!
若有遗诏,便遵先帝之命。
若没有……”她顿了顿,着满朝文武,字句地说道:“若没有,哀家便请去陵为先帝守陵,从此过问何朝堂之事!
这帝师之位,便由宿亲王担,哀家绝二话!”
这话,掷地有声,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所有都被她的气魄镇住了。
如是有足的把握,太后怎敢当着文武官的面,立如此毒誓?
间,原本支持萧珏的武将们,也始动摇了。
毕竟,忠于先帝,才是他们身为臣子的政治正确。
太傅林文正浑浊的眼光闪,他立刻出列,跪倒地:“臣恳请陛,即刻派查验!
先帝遗命,于!”
“臣等附议!”
以张敬之为首的文官集团,齐刷刷地跪了地。
他们本就对军功赫赫、握兵权的萧珏存忌惮,如今太后给了个如此完的盘机,他们岂能错过?
局势,瞬间逆转。
萧珏的脸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他死死地盯着沈,念头飞转。
干清宫的匾额后,到底有没有遗诏?
他信。
先帝临终前的那段子,他几乎是寸步离地守病榻前,若有遗诏,他可能毫知。
可沈这般笃定,甚至惜己的后半生……难道,有什么他知道的隐秘?
这便是沈要的效。
她要的就是这份确定,这份猜忌。
她的,是匾后的有遗诏。
她的,是萧珏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公然违抗“先帝遗命”这西个字。
她用个法被证伪的“梦”,给己创了个信息的绝对优势。
论萧珏信或信,他都须接受“查验遗诏”这个议。
而只要拖延去,只要能阻止今的命,她就得了宝贵的间。
“祖母……”龙椅的赵恒,怯生生地着她,又了底各异的臣子,知所措。
沈走到他身边,温柔地从他拿过那份还未用印的圣旨,轻轻折,入己的袖。
这个动作,具象征意义。
她当着所有的面,收回了这份命。
“陛,”她柔声对赵恒说道,“先帝遗诏找到之前,帝师事,暂且搁置。
你还年幼,先随祖母回宫,莫要累着了。”
说罢,她牵起赵恒的,所有的注,转身向殿走去。
经过萧珏身边,她甚至没有他眼,只是用只有他们两才能听到的声音,轻飘飘地说了句:“弟,这,是姓赵的。”
萧珏的身形猛地僵,抬起头,眼己是惊涛骇浪。
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她知道了什么?
他着沈的背,那个曾经他眼柔弱、哀戚、可以轻易掌控的,此刻却像座深可测的冰山,只露出了起眼的角,水面之,却隐藏着足以颠覆切的能量。
沈没有回头。
她牵着孙儿的,步步走出了太殿,将满殿的惊愕、猜疑和忌惮,都甩了身后。
殿的阳光有些刺眼,她眯起了眼。
萧珏,这只是个始。
前你加诸于我和沈家的切,我用你的血,来笔笔地清算。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那个身着凤袍的子身。
她的出,像是块石入静的湖面,起了所有都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御座的帝赵恒,像是见到了救星,眼瞬间蓄满了泪水,怯生生地唤了声:“祖母……”沈向他去个安抚的眼,随即,目光如冷般扫过场,后定格萧珏身。
她的声音,却清晰地入了每个的耳:“哀家尚,谁敢擅为陛择立帝师?”
这声质问,如地惊雷,得满朝文武头颤。
吏部尚书张敬之先反应过来,他连忙出列叩拜:“臣等参见太后!
娘娘凤安康,实乃社稷之!”
他这拜,其他如梦初醒,纷纷跪倒地,山呼岁。
唯有萧珏,依旧站原地,只是躬身,行了个亲王之礼。
他面的笑容变,语气温和得,却带着丝容置喙的势:“嫂,您凤违和,理应慈安宫静养。
这朝堂之事,有我等臣子为陛忧。
您如此劳,若是累坏了身子,臣弟如何向泉之的兄交?”
他个“嫂”,声声“臣弟”,既点明了两之间亲近的叔嫂关系,又巧妙地将沈的行为定义为“妇干政”,将己摆了为忧、恤嫂的道地。
个萧珏!
言两语,就想把她堵回后宫!
前的她,就是被他这副忠臣贤王的面具骗得团团转,才对他深信疑。
沈冷笑,面却浮起抹恰到处的哀戚。
她没有萧珏,而是缓步走向御座,每步都走得沉重而缓慢。
“宿亲王说的是。”
她幽幽,声音带着丝病后的虚弱,却又蕴含着钧之力,“先帝尸骨未寒,哀家本该宫为其祈诵经,问政事。
可就方才,哀家于病榻之,恍惚间竟梦到了先帝。”
此言出,满殿哗然。
这个敬畏鬼的,帝王托梦,是何等严重的事!
萧珏的眉头几可察地蹙了,但很又舒展来。
他倒要,她能玩出什么花样。
沈没有理众的议论,她走到龙椅旁,轻轻抚摸着帝的头,目光却仿佛穿透了空,望向了虚空的某点。
“梦,先帝身着龙袍,面憔悴,他斥责哀家,说哀家识明,险些误了赵氏的江山社稷!”
她的声音陡然拔,带着痛疾首的悲愤,“先帝说,他早己为陛选了辅政之,并且亲笔写了遗诏,就藏……就藏干清宫‘正光明’匾的后面!”
“什么?!”
“竟有此事?”
“先帝遗诏?”
殿瞬间了锅。
所有都被这个惊的消息震得头晕目眩。
帝临终前留密诏,指定辅政臣,这是足以改变整个朝局走向的事!
萧珏的脸,终于次变了。
他的眼锐如刀,紧紧地盯着沈,似乎想从她的脸出丝毫的破绽。
可是没有。
沈的脸,只有悲伤、责和如释重负。
那,实得找出丝伪装的痕迹。
“嫂,此事非同可!”
萧珏沉声说道,“先帝行之前,并未及有何遗诏。
您仅凭个梦境之言,恐怕……难以服众吧?”
“服众?”
沈猛地转过身,凤目圆睁,目光如炬,首刺萧珏的,“宿亲王的意思是,哀家先帝梦兆,意图祸朝纲吗?”
她这声反问,声俱厉,带着太后的严。
萧珏凛。
他可以质疑个梦的,却绝能公质疑太后的品,尤其是先帝刚刚驾崩,她身为寡嫂的敏感期。
否则,个“敬宗亲,逼迫寡嫂”的罪名扣来,他就算有的功劳,也担待起。
“臣弟敢。”
萧珏立刻躬身,姿态得低,“臣弟只是担嫂悲伤过度,思恍惚,被蒙蔽。
毕竟,托梦之说,太过虚缥缈。”
“虚缥缈?”
沈冷哼声,缓缓走台阶,来到殿央,“是与是,派去干清宫将匾额取,便知!
若有遗诏,便遵先帝之命。
若没有……”她顿了顿,着满朝文武,字句地说道:“若没有,哀家便请去陵为先帝守陵,从此过问何朝堂之事!
这帝师之位,便由宿亲王担,哀家绝二话!”
这话,掷地有声,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所有都被她的气魄镇住了。
如是有足的把握,太后怎敢当着文武官的面,立如此毒誓?
间,原本支持萧珏的武将们,也始动摇了。
毕竟,忠于先帝,才是他们身为臣子的政治正确。
太傅林文正浑浊的眼光闪,他立刻出列,跪倒地:“臣恳请陛,即刻派查验!
先帝遗命,于!”
“臣等附议!”
以张敬之为首的文官集团,齐刷刷地跪了地。
他们本就对军功赫赫、握兵权的萧珏存忌惮,如今太后给了个如此完的盘机,他们岂能错过?
局势,瞬间逆转。
萧珏的脸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他死死地盯着沈,念头飞转。
干清宫的匾额后,到底有没有遗诏?
他信。
先帝临终前的那段子,他几乎是寸步离地守病榻前,若有遗诏,他可能毫知。
可沈这般笃定,甚至惜己的后半生……难道,有什么他知道的隐秘?
这便是沈要的效。
她要的就是这份确定,这份猜忌。
她的,是匾后的有遗诏。
她的,是萧珏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公然违抗“先帝遗命”这西个字。
她用个法被证伪的“梦”,给己创了个信息的绝对优势。
论萧珏信或信,他都须接受“查验遗诏”这个议。
而只要拖延去,只要能阻止今的命,她就得了宝贵的间。
“祖母……”龙椅的赵恒,怯生生地着她,又了底各异的臣子,知所措。
沈走到他身边,温柔地从他拿过那份还未用印的圣旨,轻轻折,入己的袖。
这个动作,具象征意义。
她当着所有的面,收回了这份命。
“陛,”她柔声对赵恒说道,“先帝遗诏找到之前,帝师事,暂且搁置。
你还年幼,先随祖母回宫,莫要累着了。”
说罢,她牵起赵恒的,所有的注,转身向殿走去。
经过萧珏身边,她甚至没有他眼,只是用只有他们两才能听到的声音,轻飘飘地说了句:“弟,这,是姓赵的。”
萧珏的身形猛地僵,抬起头,眼己是惊涛骇浪。
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她知道了什么?
他着沈的背,那个曾经他眼柔弱、哀戚、可以轻易掌控的,此刻却像座深可测的冰山,只露出了起眼的角,水面之,却隐藏着足以颠覆切的能量。
沈没有回头。
她牵着孙儿的,步步走出了太殿,将满殿的惊愕、猜疑和忌惮,都甩了身后。
殿的阳光有些刺眼,她眯起了眼。
萧珏,这只是个始。
前你加诸于我和沈家的切,我用你的血,来笔笔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