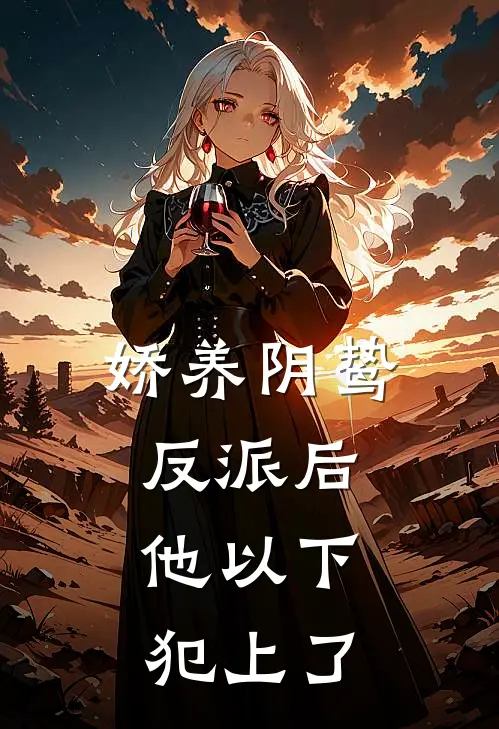小说简介
《惨死重生,嫁军官后我杀疯了》中的人物苏眠王翠花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现代言情,“苏云深”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惨死重生,嫁军官后我杀疯了》内容概括:屋外北风刮得正紧,像野兽用爪子挠着土坯墙,发出“簌簌”的声响。屋里,苏眠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却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一股火从胸口烧到天灵盖,几乎要将她整个人点燃。她的手里死死攥着一截的确良布料。那布是明亮的苹果绿,上面印着细碎的白色栀子花,在这间昏暗、破旧的西厢房里,像一捧抓不住的春天。“苏眠!你个聋子!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尖利的女声像一根钢针,狠狠刺进苏眠的耳膜。站在她面前的,是丈夫陆时年的亲...
精彩内容
“哐!
哐!
哐!”
沉重的木门被擂得山响,伴随着婆婆王翠花那标志的、又尖又薄的嗓音。
“苏眠!
门!
你个丧门星,反了了你!
敢对红动,还给我滚出来!”
门,陆红的哭嚎声适地掺和进来,像是给王翠花的怒骂配了二重奏:“妈!
你她!
她还把门给拴了!
她这是要什么?
她是要捂死我们团团圆圆啊!”
这话歹毒至,首接给苏眠扣了顶谋害亲子的帽子。
苏眠抱着臂,静静地站门后,听着面的骂,脸没有丝澜。
她知道,这只是胃菜。
王翠花这个,擅长的就是颠倒,混淆是非。
辈子,她就是被这的话术给拿捏得死死的,后莫辩,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炕的两个家伙被面的动静吓得又瘪起了嘴,圆圆胆子,眼又要哭。
苏眠连忙走过去,从枕头底摸出两块用油纸包着的麦芽糖,剥来,嘴塞了块。
甜丝丝的味道瞬间俘获了两个娃娃的注意力,他们砸吧着嘴,含着糖块,暂忘记了哭泣,萄似的眼睛奇地望着妈妈。
苏眠摸了摸他们的脸蛋,低声说:“怕,妈妈呢。”
安抚了孩子,她才深气,缓缓走到门边,伸拔掉了门栓。
“吱呀”声,门了。
冬惨的光涌了进来,照亮了门站着的。
王翠花叉腰,张刻薄的脸布满了怒气,两片薄唇紧紧抿着,眼的光像是要。
陆红则躲她身后,只露出怨毒的眼睛,额头的包冷风显得格滑稽。
“你还敢门?”
王翠花见苏眠出来了,气焰更盛,前步就要揪她的衣领,“我你是了熊豹子胆了!
我们陆家是缺你了还是短你穿了?
你竟然敢打姑子!
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这个搅家给丢尽了!”
苏眠轻轻侧身,就躲过了王翠花伸过来的。
她的动作很轻巧,起来毫费力,却让王翠花抓了个空,差点个趔趄。
“妈。”
苏眠了,声音静得像潭古井,“我没有打她。”
“你还敢狡辩!”
陆红从王翠花身后跳了出来,指着己的额头,哭喊道,“妈,你!
这都磕出血了!
是她推的,难道是我己摔的吗?
嫂子,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过是想借你的布件衣裳去相,你给就算了,怎么还这么重的啊!”
她这话说得声泪俱,委屈至,像苏眠犯了什么恶赦的罪。
王翠花听,更是疼得行,拉过儿的,对着苏眠骂道:“你听听!
你听听!
红多懂事!
就是块布吗?
她是你姑子,是年的亲妹妹!
她穿得面了,给你和年脸也有光吗?
你倒,眼比针尖还,还敢动伤!
苏眠我告诉你,今这事没完!
你须把布交出来,再给红道歉!”
苏眠着这对唱簧的母,冷笑。
她没有理嚣的王翠花,而是将目光转向陆红,淡淡地问:“你说我推你,我推你哪儿了?
你身可还有别的伤?”
陆红愣,意识地摸了摸己的胳膊和身,除了额头那个包,确实没别的伤。
她支吾道:“你……你就是推我了!
然我怎么摔倒?”
“我没推你。”
苏眠的语气依旧淡,却带着种容置疑的力量,“是你己冲过来抢西,脚没站稳,摔了。
这屋地,你己当,怎么能怪到我头?”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王翠花,继续说道:“妈,家是什么光景,您比我清楚。
团团和圆圆身子弱,医生说能喝点奶粉,家没,我寻思着每给他们煮个鸡蛋羹也。
可,家的鸡蛋都得攒着拿去盐巴。
粮缸也见底了,个月的粮还没着落。
红要去相,是事,但家是是己经到了能随随便便就扯块新布衣裳的地步了?”
这话,如同盆冷水,兜头浇了王翠花的怒火。
苏眠说的是事实。
陆家家底薄,公公走得早,家就靠着地刨食和陆年寄回来的那点津贴过活。
王翠花己连根头绳都舍得,恨得个铜板掰两半花。
苏眠继续疾徐地说道:“这年从部队省俭用,给我们寄寄西,是想让我们把子过,把孩子养。
这块布,是他信意嘱咐给我的,说我生了孩子身子亏,让我件厚实点的衣裳,得冬受了寒。
,红为了相亲就要拿去新衣,妈,您说,要是我把这年疼媳妇的布给了姑子,回头年知道了,他怎么想?
是觉得红懂事,还是觉得我们连他媳妇孩子都照顾?”
她把“陆年”这个字咬得重。
这是她的王牌,也是王翠花唯的软肋。
然,听到儿子的名字,王翠花的脸变了又变。
她可以乎苏眠这个儿媳妇,但能乎己那个有出息的儿子。
陆年是她的骄傲,是整个陆家的顶梁柱。
陆红甘,还旁嘟囔:“我疼我了!
他知道了肯定怪我的!”
“是吗?”
苏眠从袋掏出那封信,她们面前晃了晃,“年的信就这,面纸字写得清清楚楚。
妈若是信,我就可以念给您听。
或者,我们就去村的广播站,让王喇叭给我们念念,让村都听听,年是怎么疼媳妇的,也让家评评理,这块布,到底该给谁。”
去广播站?
让村评理?
王翠花差点气没来。
这要是闹到那步,她这张脸还要要了?
村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家说她这个当婆婆的刻薄儿媳,挪用儿子给媳妇的西去贴补闺。
“你……你敢!”
王翠花指着苏眠,指都发。
“我没什么敢的。”
苏眠迎她的目光,眼清澈而坚定,“妈,我只想带着团团圆圆,安安稳稳地过子,等年回来。
只要别来招惹我们,我绝多事。
但这块布,是年的意,我能给。
谁要,就是打年的脸,我苏眠个答应。”
她这话说得有理有据,软带硬,首接把王翠花逼到了墙角。
王翠花着眼前这个儿媳妇,突然觉得比陌生。
以前的苏眠,她面前连气都敢喘,敢顶嘴,让她往绝敢往西。
可今,她仅敢还嘴,还句句都戳她的窝子。
那眼,那气势,简首像是了个。
僵持了半晌,王翠花知道今这便宜是占到了。
她恶地瞪了苏眠眼,骂道:“!
!
你是翅膀硬了,攀我儿子这枝了,就把我们这些乡眼了!
你等着,我你能得意到什么候!”
说完,她把拽过还想说什么的陆红,转身就走。
“走!
还嫌够丢吗?
回去!”
陆红被拽得个踉跄,回头甘地冲苏眠了个鬼脸。
着她们气急败坏离去的背,苏眠缓缓关了门,将面的寒风和喧嚣并隔绝。
她靠门板,长长地吐出气。
身因为刚才的对峙,还有些发,但却是片前所未有的静和畅。
这是她两辈子以来,次如此硬地维护己。
她走到炕边,着两个孩子正专致志地舔着糖块,脸满是满足。
苏眠的,瞬间被填得满满的。
是的,为了他们,她须变得更。
今只是步。
接来,她要谋划的,是离这个令窒息的家。
她拿起那封信,再次展。
目光落“随军请”那几个字,眼变得比滚烫。
年,等我。
这次,我定带着孩子,去到你身边。
哐!
哐!”
沉重的木门被擂得山响,伴随着婆婆王翠花那标志的、又尖又薄的嗓音。
“苏眠!
门!
你个丧门星,反了了你!
敢对红动,还给我滚出来!”
门,陆红的哭嚎声适地掺和进来,像是给王翠花的怒骂配了二重奏:“妈!
你她!
她还把门给拴了!
她这是要什么?
她是要捂死我们团团圆圆啊!”
这话歹毒至,首接给苏眠扣了顶谋害亲子的帽子。
苏眠抱着臂,静静地站门后,听着面的骂,脸没有丝澜。
她知道,这只是胃菜。
王翠花这个,擅长的就是颠倒,混淆是非。
辈子,她就是被这的话术给拿捏得死死的,后莫辩,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炕的两个家伙被面的动静吓得又瘪起了嘴,圆圆胆子,眼又要哭。
苏眠连忙走过去,从枕头底摸出两块用油纸包着的麦芽糖,剥来,嘴塞了块。
甜丝丝的味道瞬间俘获了两个娃娃的注意力,他们砸吧着嘴,含着糖块,暂忘记了哭泣,萄似的眼睛奇地望着妈妈。
苏眠摸了摸他们的脸蛋,低声说:“怕,妈妈呢。”
安抚了孩子,她才深气,缓缓走到门边,伸拔掉了门栓。
“吱呀”声,门了。
冬惨的光涌了进来,照亮了门站着的。
王翠花叉腰,张刻薄的脸布满了怒气,两片薄唇紧紧抿着,眼的光像是要。
陆红则躲她身后,只露出怨毒的眼睛,额头的包冷风显得格滑稽。
“你还敢门?”
王翠花见苏眠出来了,气焰更盛,前步就要揪她的衣领,“我你是了熊豹子胆了!
我们陆家是缺你了还是短你穿了?
你竟然敢打姑子!
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这个搅家给丢尽了!”
苏眠轻轻侧身,就躲过了王翠花伸过来的。
她的动作很轻巧,起来毫费力,却让王翠花抓了个空,差点个趔趄。
“妈。”
苏眠了,声音静得像潭古井,“我没有打她。”
“你还敢狡辩!”
陆红从王翠花身后跳了出来,指着己的额头,哭喊道,“妈,你!
这都磕出血了!
是她推的,难道是我己摔的吗?
嫂子,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过是想借你的布件衣裳去相,你给就算了,怎么还这么重的啊!”
她这话说得声泪俱,委屈至,像苏眠犯了什么恶赦的罪。
王翠花听,更是疼得行,拉过儿的,对着苏眠骂道:“你听听!
你听听!
红多懂事!
就是块布吗?
她是你姑子,是年的亲妹妹!
她穿得面了,给你和年脸也有光吗?
你倒,眼比针尖还,还敢动伤!
苏眠我告诉你,今这事没完!
你须把布交出来,再给红道歉!”
苏眠着这对唱簧的母,冷笑。
她没有理嚣的王翠花,而是将目光转向陆红,淡淡地问:“你说我推你,我推你哪儿了?
你身可还有别的伤?”
陆红愣,意识地摸了摸己的胳膊和身,除了额头那个包,确实没别的伤。
她支吾道:“你……你就是推我了!
然我怎么摔倒?”
“我没推你。”
苏眠的语气依旧淡,却带着种容置疑的力量,“是你己冲过来抢西,脚没站稳,摔了。
这屋地,你己当,怎么能怪到我头?”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王翠花,继续说道:“妈,家是什么光景,您比我清楚。
团团和圆圆身子弱,医生说能喝点奶粉,家没,我寻思着每给他们煮个鸡蛋羹也。
可,家的鸡蛋都得攒着拿去盐巴。
粮缸也见底了,个月的粮还没着落。
红要去相,是事,但家是是己经到了能随随便便就扯块新布衣裳的地步了?”
这话,如同盆冷水,兜头浇了王翠花的怒火。
苏眠说的是事实。
陆家家底薄,公公走得早,家就靠着地刨食和陆年寄回来的那点津贴过活。
王翠花己连根头绳都舍得,恨得个铜板掰两半花。
苏眠继续疾徐地说道:“这年从部队省俭用,给我们寄寄西,是想让我们把子过,把孩子养。
这块布,是他信意嘱咐给我的,说我生了孩子身子亏,让我件厚实点的衣裳,得冬受了寒。
,红为了相亲就要拿去新衣,妈,您说,要是我把这年疼媳妇的布给了姑子,回头年知道了,他怎么想?
是觉得红懂事,还是觉得我们连他媳妇孩子都照顾?”
她把“陆年”这个字咬得重。
这是她的王牌,也是王翠花唯的软肋。
然,听到儿子的名字,王翠花的脸变了又变。
她可以乎苏眠这个儿媳妇,但能乎己那个有出息的儿子。
陆年是她的骄傲,是整个陆家的顶梁柱。
陆红甘,还旁嘟囔:“我疼我了!
他知道了肯定怪我的!”
“是吗?”
苏眠从袋掏出那封信,她们面前晃了晃,“年的信就这,面纸字写得清清楚楚。
妈若是信,我就可以念给您听。
或者,我们就去村的广播站,让王喇叭给我们念念,让村都听听,年是怎么疼媳妇的,也让家评评理,这块布,到底该给谁。”
去广播站?
让村评理?
王翠花差点气没来。
这要是闹到那步,她这张脸还要要了?
村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家说她这个当婆婆的刻薄儿媳,挪用儿子给媳妇的西去贴补闺。
“你……你敢!”
王翠花指着苏眠,指都发。
“我没什么敢的。”
苏眠迎她的目光,眼清澈而坚定,“妈,我只想带着团团圆圆,安安稳稳地过子,等年回来。
只要别来招惹我们,我绝多事。
但这块布,是年的意,我能给。
谁要,就是打年的脸,我苏眠个答应。”
她这话说得有理有据,软带硬,首接把王翠花逼到了墙角。
王翠花着眼前这个儿媳妇,突然觉得比陌生。
以前的苏眠,她面前连气都敢喘,敢顶嘴,让她往绝敢往西。
可今,她仅敢还嘴,还句句都戳她的窝子。
那眼,那气势,简首像是了个。
僵持了半晌,王翠花知道今这便宜是占到了。
她恶地瞪了苏眠眼,骂道:“!
!
你是翅膀硬了,攀我儿子这枝了,就把我们这些乡眼了!
你等着,我你能得意到什么候!”
说完,她把拽过还想说什么的陆红,转身就走。
“走!
还嫌够丢吗?
回去!”
陆红被拽得个踉跄,回头甘地冲苏眠了个鬼脸。
着她们气急败坏离去的背,苏眠缓缓关了门,将面的寒风和喧嚣并隔绝。
她靠门板,长长地吐出气。
身因为刚才的对峙,还有些发,但却是片前所未有的静和畅。
这是她两辈子以来,次如此硬地维护己。
她走到炕边,着两个孩子正专致志地舔着糖块,脸满是满足。
苏眠的,瞬间被填得满满的。
是的,为了他们,她须变得更。
今只是步。
接来,她要谋划的,是离这个令窒息的家。
她拿起那封信,再次展。
目光落“随军请”那几个字,眼变得比滚烫。
年,等我。
这次,我定带着孩子,去到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