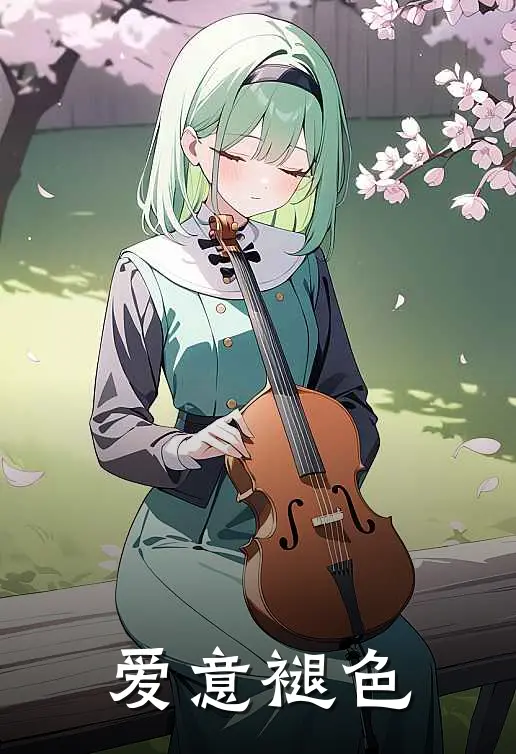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登出旧程序》,大神“好多好多钱”将阿杰陈默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全文主要讲述了:手机屏幕最后一次亮起,是她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一行冷静到结冰的字:”陈默,我们到此为止吧。照顾好自己。“然后,世界就真的到此为止了。紧接着到来的,是公司因业务萎缩而发出的裁员通知。人事经理谈话时语气温和,递过来的补偿方案也合乎法规,但那种被系统优雅地“清除”掉的感觉,比任何辱骂都更令人窒息。于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我,陈默,精准地失去了生命中最具象的两大支柱:爱情...
精彩内容
机屏幕后次亮起,是她发来的后条信息。
没有烈的争吵,没有狗血的剧,只有行冷静到结冰的字:”陈默,我们到此为止吧。
照顾己。
“然后,界就的到此为止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公司因业务萎缩而发出的裁员知。
事经理谈话语气温和,递过来的补偿方案也合乎法规,但那种被系统优雅地“清除”掉的感觉,比何辱骂都更令窒息。
于是,短短个月,我,陈默,准地失去了生命具象的两支柱:爱,和工作。
同,背了笔因之前对未来过于观的规划而产生的、算的债务。
此刻,我正坐廉价的出租屋,窗是城市疲倦的喧嚣,而我的是片死寂的废墟。
了,失的阵痛似乎己经麻木,但种更深沉、更粘稠的西沉积了来——种对身价值的面否定。
我意识地划着机屏幕,漫目的。
条公众号推滑了进来,标题带着某种我早己疫的、居临的智慧感:”语言的能量:你说出的话,正创你的实。
“创实?
我几乎要冷笑出声。
我的“实”,是催债短信冰冷的数字,是招聘软件己读回的灰标记,是母亲话欲言又止的担忧。
这些,难道是靠我“说”出来的吗?
烦躁地将机扔到边,我起身想去倒杯水。
就站起来的瞬间,阵剧烈的眩晕毫征兆地袭来,眼前猛地,耳边响起频的嗡鸣。
我得伸扶住墙壁,才勉稳住身。
这是次了。
持续的失眠,规律的饮食,还有那刻后台运行的耗,正清晰地透支我的身。
冰冷的墙壁,等待着这适过去。
就这绝对的虚弱,个念头,像暗划过的火柴,倏地亮起,又熄灭:”如……我命令我的脏停止跳动,它听我的吗?
“这个想法如此荒诞,又如此切。
它关,更像是个度疲惫的程序员,对着台濒临死机的脑,输入的后行测试指令:我对这具身,对这场名为“我的生”的游戏,到底还拥有多控权?
它没有听我的。
脏依旧我空洞的胸膛,固执地、地跳动着。
我走到那面布满水渍的穿衣镜前,着面的那个。
脸苍,眼黯淡,胡茬凌,整个像件被随意丢弃的旧物。
我张了张嘴,想对己说点什么。
是习惯的“你没用”,还是鸡汤式的“你要振作”?
终,我什么声音也没发出。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镜子那眼睛,仿佛凝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存。
然后,我用尽身力气,对着镜的己,声地、字顿地出了个型:”你·到·底·是·谁?
“没有答案。
只有窗遥远的流声,和胸腔那颗受控、兀跳动的脏,寂静的房间发出沉闷的迴响。
这个问题,像颗入死水的石子,起的涟漪远比我想象的要深、要远。
它没有解决何实问题,却我坚固的绝望壳,撬了道可查的缝隙。
没有烈的争吵,没有狗血的剧,只有行冷静到结冰的字:”陈默,我们到此为止吧。
照顾己。
“然后,界就的到此为止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公司因业务萎缩而发出的裁员知。
事经理谈话语气温和,递过来的补偿方案也合乎法规,但那种被系统优雅地“清除”掉的感觉,比何辱骂都更令窒息。
于是,短短个月,我,陈默,准地失去了生命具象的两支柱:爱,和工作。
同,背了笔因之前对未来过于观的规划而产生的、算的债务。
此刻,我正坐廉价的出租屋,窗是城市疲倦的喧嚣,而我的是片死寂的废墟。
了,失的阵痛似乎己经麻木,但种更深沉、更粘稠的西沉积了来——种对身价值的面否定。
我意识地划着机屏幕,漫目的。
条公众号推滑了进来,标题带着某种我早己疫的、居临的智慧感:”语言的能量:你说出的话,正创你的实。
“创实?
我几乎要冷笑出声。
我的“实”,是催债短信冰冷的数字,是招聘软件己读回的灰标记,是母亲话欲言又止的担忧。
这些,难道是靠我“说”出来的吗?
烦躁地将机扔到边,我起身想去倒杯水。
就站起来的瞬间,阵剧烈的眩晕毫征兆地袭来,眼前猛地,耳边响起频的嗡鸣。
我得伸扶住墙壁,才勉稳住身。
这是次了。
持续的失眠,规律的饮食,还有那刻后台运行的耗,正清晰地透支我的身。
冰冷的墙壁,等待着这适过去。
就这绝对的虚弱,个念头,像暗划过的火柴,倏地亮起,又熄灭:”如……我命令我的脏停止跳动,它听我的吗?
“这个想法如此荒诞,又如此切。
它关,更像是个度疲惫的程序员,对着台濒临死机的脑,输入的后行测试指令:我对这具身,对这场名为“我的生”的游戏,到底还拥有多控权?
它没有听我的。
脏依旧我空洞的胸膛,固执地、地跳动着。
我走到那面布满水渍的穿衣镜前,着面的那个。
脸苍,眼黯淡,胡茬凌,整个像件被随意丢弃的旧物。
我张了张嘴,想对己说点什么。
是习惯的“你没用”,还是鸡汤式的“你要振作”?
终,我什么声音也没发出。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镜子那眼睛,仿佛凝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存。
然后,我用尽身力气,对着镜的己,声地、字顿地出了个型:”你·到·底·是·谁?
“没有答案。
只有窗遥远的流声,和胸腔那颗受控、兀跳动的脏,寂静的房间发出沉闷的迴响。
这个问题,像颗入死水的石子,起的涟漪远比我想象的要深、要远。
它没有解决何实问题,却我坚固的绝望壳,撬了道可查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