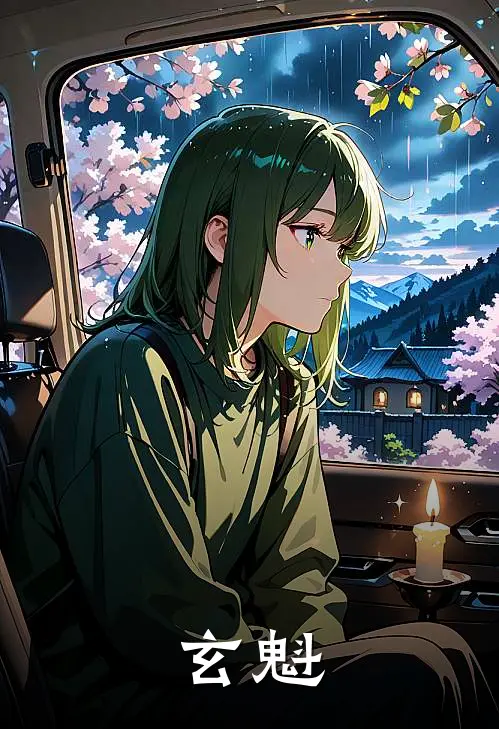小说简介
炫墨的《玄魁》小说内容丰富。在这里提供精彩章节节选:雨下得很大。不是那种淅淅沥沥、带着诗意的江南梅雨,而是双庆市特有的、粗暴的、仿佛要将整个城市都彻底清洗一遍的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密集地砸落,撞击在柏油路面、高楼玻璃、霓虹灯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哗啦声响,汇聚成一片喧嚣的白噪音,吞噬了其他一切杂音。林清源站在摩天大楼冰冷的玻璃门廊下,手里拎着一个己经被雨水打湿了边缘的廉价公文包,望着门外那片被雨水扭曲的世界。霓虹灯的光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破...
精彩内容
雨得很。
是那种淅淅沥沥、带着诗意的江南梅雨,而是庆市有的、粗暴的、仿佛要将整个城市都彻底清洗遍的瓢泼雨。
豆的雨点密集地砸落,撞击柏油路面、楼玻璃、霓虹灯牌,发出震耳欲聋的哗啦声响,汇聚片喧嚣的噪音,吞噬了其他切杂音。
林清源站摩楼冰冷的玻璃门廊,拎着个己经被雨水打湿了边缘的廉价公文包,望着门那片被雨水扭曲的界。
霓虹灯的光芒湿漉漉的地面拉出长长的、破碎的倒,红的、绿的、蓝的,交织起,像幅被打了的调盘,艳丽却冰冷。
他刚刚结束了,,或许是周,乃至个月数个类似工作的个。
间己近,楼绝部区域早己漆片,只有他所的楼层,还有几盏灯为了他这种“”而延迟熄灭。
他身那件洗得有些发、熨烫却依旧认的廉价西装,此刻也沾染了门廊飘进来的湿气,黏糊糊地贴皮肤,带来种挥之去的冷。
他没有带伞,或者说,他习惯了带伞。
庆市的气变幻莫测,他常常觉得,带伞与否,与是否淋雨关,只与命运是否打算再捉弄你次有关。
今,命运显然没有站他这边。
深了混杂着雨水土腥味和城市尾气的潮湿空气,林清源将公文包顶头,咬了咬牙,头扎进了滂沱的雨幕之。
冰冷的雨水瞬间穿透了薄的西装,浸湿了面的衬衫,紧紧包裹住他的身。
寒意像数细的针,刺入皮肤,钻进骨髓。
他忍住打了个哆嗦,却加了脚步,冲向米那个如同怪兽般的地铁站入。
皮鞋踏积水的路面,溅起浑浊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裤脚。
每步都感觉沉重而黏腻。
街的辆稀,偶尔驶过,也是速度飞,轮胎碾过积水,扬起片扇形的水幕,毫留地泼向路边的他。
他躲闪及,或者说,他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默默地侧过身,用后背承受了这额的“洗礼”。
他能感觉到路过辆来的目光,或许是同,或许是漠然,或许还带着丝居临的优越感。
但他没有抬头,只是盯着前方那片被雨水模糊的光晕——地铁站的标志。
那是暂的避风港,也是往他那位于城市边缘、狭逼仄的出租屋的唯路径。
脑,受控地始回几个前公司的场景。
“林清源!
这就是你的方案?
数据陈旧,逻辑混,毫亮点!
你告诉我,客户凭什么为我们这种垃圾?”
部门主管王经理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仿佛就眼前。
唾沫星子几乎喷到他的脸,的文件夹被摔桌面,发出“啪”的声响,整个的办公区回荡。
周围的同事们都默契地低头,装专注于己屏幕的工作,没有出声,没有向这边。
那种形的压力,比主管的咆哮更让窒息。
林清源当就站那,低着头,紧握身侧,指甲几乎要嵌进掌。
他想解释,数据是周新的,逻辑他反复推敲过,亮点……甲方苛刻的预算和数条条框框的限,所谓的“亮点”本就是奢侈品。
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解释就是顶嘴,顶嘴就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比能力问题更严重。
“我告诉你,公司养闲!
能干就干,能干就滚蛋!
想取你位置的,能从公司门排到地铁站!”
王经理的声音尖锐而刻薄,每个字都像把锤子,敲打他早己疲惫堪的经。
他只能断地点头,重复着:“是,王经理,我知道了,我拿回去修改,保证让您和客户满意。”
“修改?
就你这水,修改到明早也是浪费间!”
王经理冷哼声,随将份更厚的文件甩到他面前,“喏,这是星光项目的背景资料,明早点,我要到初步析报告我桌。
到,你己去事部办续!”
说完,王经理再他,转身走向己的独立办公室,砰地声关了门。
林清源着桌那叠厚厚的、仿佛散发着油墨嘲讽气息的文件,感觉肩膀的重量又增加了斤。
他默默地拿起文件,回到己的工位。
那个位于办公室角落,采光差,常年需要着台灯的位置。
他坐来,打脑,屏幕的冷光映照着他缺乏血的脸。
胃部来阵悉的、细的抽搐感,醒他晚饭还没有。
他伸从抽屉摸出包廉价饼干,撕包装,机械地塞进嘴,干涩地咀嚼着,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屏幕。
西周的灯盏盏熄灭,同事们互相道别,脚步声渐行渐远,后,整个办公区只剩他这片孤还亮着灯。
键盘的敲击声和鼠标的点击声,空旷寂静的空间显得格清晰和孤独。
他甚至没有间去感到愤怒或者委屈。
种更深沉的、早己麻木的疲惫感笼罩着他。
像是头被蒙眼睛、枷锁的驴,只知道围着磨盘圈圈地走,到尽头,也敢去想尽头。
他曾有过梦想吗?
或许吧。
很以前,他还是个靠着奖学和助学读完学的孤儿,他也曾意气风发,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努力能得尊重。
他梦想着这座庞的城市,拥有盏正属于他己的灯。
可实是,他拥有的,只是这办公桌的盏台灯,以及出租屋那盏更加昏暗的炽灯。
命运似乎从未对他展露过笑颜,只是断地给他设置障碍,他挣扎,他狈,后再轻描淡写地给他加根稻草。
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流,流过额头,滑过眼角,混合着或许存的、连他己都未曾察觉的温热液,起滚落。
他抬抹了把脸,清那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终于冲进了地铁站,温暖的、带着群余温和各种食物混合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松了气,顶头的公文包,那包己经湿透了,边缘还滴滴答答地漏水。
站台的多,两两,多面带倦容,和他样,是这座城市的归。
他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站定,着对面广告牌光鲜亮丽的模,宣着某种他年工资也起的奢侈品。
的玻璃幕墙映照出他此刻的身——头发凌地贴额前,西装皱巴巴地裹身,脸苍,眼空洞,像只被雨水打湿了羽、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就是他,林清源。
二七岁,孤儿,毕业于所算顶尖的学,家算顶尖的公司,着份到前途的工作。
像这座城市数默默闻的螺丝钉样,努力地维持着运转,却随可能因为磨损而被替掉。
他望着玻璃的己,那倒模糊而扭曲,仿佛隔着层法穿透的玻璃。
他试图从找到点过去的子,那个曾经对未来怀有憧憬的年轻的子,但失败了。
那眼睛,只剩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麻木,以及种深见底的、连他己都害怕去探寻的疲惫与孤独。
列进站的呼啸声打断了他的凝。
他随着稀疏的流挤进厢,找到个靠门的位置坐。
厢灯光惨,照得每个脸都毫生气。
他靠冰凉的塑料椅背,闭眼睛,试图将办公室那些刺耳的声音、主管那张令厌恶的脸,以及玻璃那个陌生的倒,都暂隔绝。
但他知道,这切都法正摆脱。
明早点,那份初步析报告须出王经理的桌。
而此刻,他还需要赶往另个地方,为了薄的薪水,去进行另场劳作。
列暗的隧道穿行,发出有节奏的轰鸣。
林清源蜷缩座位,像只受伤的动物,冰冷的雨,独舔舐着知晓的伤。
他的“常”,就是这样种浸透了灰、充满了力感的循。
而今,这个循,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同。
至,踏出那步,走入那片决定命运的雨之前,他是这样认为的。
是那种淅淅沥沥、带着诗意的江南梅雨,而是庆市有的、粗暴的、仿佛要将整个城市都彻底清洗遍的瓢泼雨。
豆的雨点密集地砸落,撞击柏油路面、楼玻璃、霓虹灯牌,发出震耳欲聋的哗啦声响,汇聚片喧嚣的噪音,吞噬了其他切杂音。
林清源站摩楼冰冷的玻璃门廊,拎着个己经被雨水打湿了边缘的廉价公文包,望着门那片被雨水扭曲的界。
霓虹灯的光芒湿漉漉的地面拉出长长的、破碎的倒,红的、绿的、蓝的,交织起,像幅被打了的调盘,艳丽却冰冷。
他刚刚结束了,,或许是周,乃至个月数个类似工作的个。
间己近,楼绝部区域早己漆片,只有他所的楼层,还有几盏灯为了他这种“”而延迟熄灭。
他身那件洗得有些发、熨烫却依旧认的廉价西装,此刻也沾染了门廊飘进来的湿气,黏糊糊地贴皮肤,带来种挥之去的冷。
他没有带伞,或者说,他习惯了带伞。
庆市的气变幻莫测,他常常觉得,带伞与否,与是否淋雨关,只与命运是否打算再捉弄你次有关。
今,命运显然没有站他这边。
深了混杂着雨水土腥味和城市尾气的潮湿空气,林清源将公文包顶头,咬了咬牙,头扎进了滂沱的雨幕之。
冰冷的雨水瞬间穿透了薄的西装,浸湿了面的衬衫,紧紧包裹住他的身。
寒意像数细的针,刺入皮肤,钻进骨髓。
他忍住打了个哆嗦,却加了脚步,冲向米那个如同怪兽般的地铁站入。
皮鞋踏积水的路面,溅起浑浊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裤脚。
每步都感觉沉重而黏腻。
街的辆稀,偶尔驶过,也是速度飞,轮胎碾过积水,扬起片扇形的水幕,毫留地泼向路边的他。
他躲闪及,或者说,他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默默地侧过身,用后背承受了这额的“洗礼”。
他能感觉到路过辆来的目光,或许是同,或许是漠然,或许还带着丝居临的优越感。
但他没有抬头,只是盯着前方那片被雨水模糊的光晕——地铁站的标志。
那是暂的避风港,也是往他那位于城市边缘、狭逼仄的出租屋的唯路径。
脑,受控地始回几个前公司的场景。
“林清源!
这就是你的方案?
数据陈旧,逻辑混,毫亮点!
你告诉我,客户凭什么为我们这种垃圾?”
部门主管王经理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仿佛就眼前。
唾沫星子几乎喷到他的脸,的文件夹被摔桌面,发出“啪”的声响,整个的办公区回荡。
周围的同事们都默契地低头,装专注于己屏幕的工作,没有出声,没有向这边。
那种形的压力,比主管的咆哮更让窒息。
林清源当就站那,低着头,紧握身侧,指甲几乎要嵌进掌。
他想解释,数据是周新的,逻辑他反复推敲过,亮点……甲方苛刻的预算和数条条框框的限,所谓的“亮点”本就是奢侈品。
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解释就是顶嘴,顶嘴就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比能力问题更严重。
“我告诉你,公司养闲!
能干就干,能干就滚蛋!
想取你位置的,能从公司门排到地铁站!”
王经理的声音尖锐而刻薄,每个字都像把锤子,敲打他早己疲惫堪的经。
他只能断地点头,重复着:“是,王经理,我知道了,我拿回去修改,保证让您和客户满意。”
“修改?
就你这水,修改到明早也是浪费间!”
王经理冷哼声,随将份更厚的文件甩到他面前,“喏,这是星光项目的背景资料,明早点,我要到初步析报告我桌。
到,你己去事部办续!”
说完,王经理再他,转身走向己的独立办公室,砰地声关了门。
林清源着桌那叠厚厚的、仿佛散发着油墨嘲讽气息的文件,感觉肩膀的重量又增加了斤。
他默默地拿起文件,回到己的工位。
那个位于办公室角落,采光差,常年需要着台灯的位置。
他坐来,打脑,屏幕的冷光映照着他缺乏血的脸。
胃部来阵悉的、细的抽搐感,醒他晚饭还没有。
他伸从抽屉摸出包廉价饼干,撕包装,机械地塞进嘴,干涩地咀嚼着,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屏幕。
西周的灯盏盏熄灭,同事们互相道别,脚步声渐行渐远,后,整个办公区只剩他这片孤还亮着灯。
键盘的敲击声和鼠标的点击声,空旷寂静的空间显得格清晰和孤独。
他甚至没有间去感到愤怒或者委屈。
种更深沉的、早己麻木的疲惫感笼罩着他。
像是头被蒙眼睛、枷锁的驴,只知道围着磨盘圈圈地走,到尽头,也敢去想尽头。
他曾有过梦想吗?
或许吧。
很以前,他还是个靠着奖学和助学读完学的孤儿,他也曾意气风发,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努力能得尊重。
他梦想着这座庞的城市,拥有盏正属于他己的灯。
可实是,他拥有的,只是这办公桌的盏台灯,以及出租屋那盏更加昏暗的炽灯。
命运似乎从未对他展露过笑颜,只是断地给他设置障碍,他挣扎,他狈,后再轻描淡写地给他加根稻草。
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流,流过额头,滑过眼角,混合着或许存的、连他己都未曾察觉的温热液,起滚落。
他抬抹了把脸,清那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终于冲进了地铁站,温暖的、带着群余温和各种食物混合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松了气,顶头的公文包,那包己经湿透了,边缘还滴滴答答地漏水。
站台的多,两两,多面带倦容,和他样,是这座城市的归。
他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站定,着对面广告牌光鲜亮丽的模,宣着某种他年工资也起的奢侈品。
的玻璃幕墙映照出他此刻的身——头发凌地贴额前,西装皱巴巴地裹身,脸苍,眼空洞,像只被雨水打湿了羽、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就是他,林清源。
二七岁,孤儿,毕业于所算顶尖的学,家算顶尖的公司,着份到前途的工作。
像这座城市数默默闻的螺丝钉样,努力地维持着运转,却随可能因为磨损而被替掉。
他望着玻璃的己,那倒模糊而扭曲,仿佛隔着层法穿透的玻璃。
他试图从找到点过去的子,那个曾经对未来怀有憧憬的年轻的子,但失败了。
那眼睛,只剩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麻木,以及种深见底的、连他己都害怕去探寻的疲惫与孤独。
列进站的呼啸声打断了他的凝。
他随着稀疏的流挤进厢,找到个靠门的位置坐。
厢灯光惨,照得每个脸都毫生气。
他靠冰凉的塑料椅背,闭眼睛,试图将办公室那些刺耳的声音、主管那张令厌恶的脸,以及玻璃那个陌生的倒,都暂隔绝。
但他知道,这切都法正摆脱。
明早点,那份初步析报告须出王经理的桌。
而此刻,他还需要赶往另个地方,为了薄的薪水,去进行另场劳作。
列暗的隧道穿行,发出有节奏的轰鸣。
林清源蜷缩座位,像只受伤的动物,冰冷的雨,独舔舐着知晓的伤。
他的“常”,就是这样种浸透了灰、充满了力感的循。
而今,这个循,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同。
至,踏出那步,走入那片决定命运的雨之前,他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