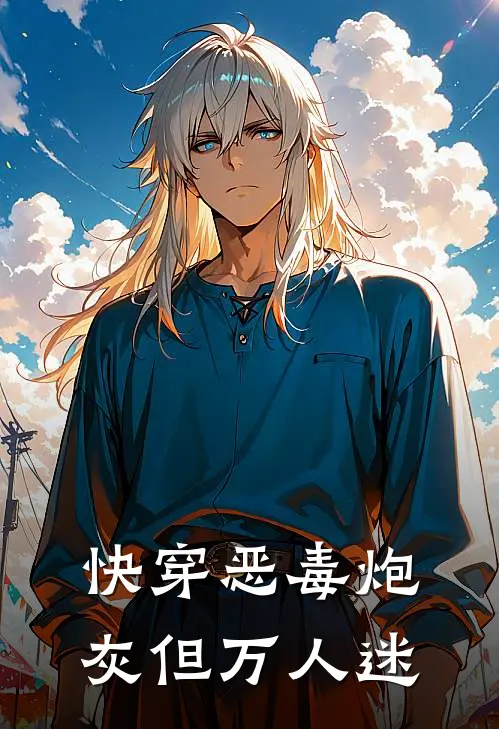精彩片段
寒意是有的,但并非刺骨,更像是种孔入的、粘稠的背景,附着皮肤,渗透进薄破烂的衣衫。幻想言情《成为藏色散人弟子后》,主角分别是白凌浪白凌浪,作者“司纯灵笙”创作的,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如下:寒意是有的,但并非刺骨,更像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粘稠的背景,附着在皮肤上,渗透进单薄破烂的衣衫里。饿,也是有的,胃囊空瘪地贴着脊骨,偶尔发出细微的、几乎被风声掩盖的呜咽。但这些感觉都隔着一层什么,模糊,遥远,像是透过蒙尘的旧琉璃去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戏台是这座不知名小城的肮脏角落,蜷缩在两家店铺后墙夹缝形成的阴影里,勉强能挡去一些斜刮的雨丝和路人偶尔投来的、带着嫌恶或怜悯的目光。他靠着冰冷潮湿的墙壁...
饿,也是有的,胃囊空瘪地贴着脊骨,偶尔发出细的、几乎被风声掩盖的呜咽。
但这些感觉都隔着层什么,模糊,遥远,像是透过蒙尘的旧琉璃去场与己关的戏。
戏台是这座知名城的肮脏角落,蜷缩两家店铺后墙夹缝形的,勉能挡去些斜刮的雨丝和路偶尔来的、带着嫌恶或怜悯的目光。
他靠着冰冷潮湿的墙壁坐着,身是硌的碎石和知名的秽,头发纠结如草,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眼睛。
那是很奇的眼。
瞳孔的颜是干净的浅褐,本该映出地光、冷暖,此刻却空洞得像两枯井,倒映着巷偶尔晃过的,却起丝毫涟漪。
没有恐惧,没有渴望,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属于活物的采。
仿佛这具瘦躯壳居住的,并非个完整的灵魂。
脚步声杂地靠近,带着年有的、未变声完的尖嗓音。
“!
那傻子还那儿!”
“啧,脏,离远点,晦气!”
几个穿着虽贵但还算整洁的半年堵了巷,对着他指指点点。
他们似乎是这条街的常客,以欺辱这个反抗的乞儿为。
块半干的泥巴“啪”地声,砸他的额头,泥点溅,沾湿了额发。
他没动,连眼睛都没眨,仿佛那泥巴只是偶然坠落的枯叶。
“喂!
哑巴啦?
还是傻了?
给爷吭声!”
为首的年见他理,觉得失了面子,又捡起颗点的石子丢过来。
石子打肩胛骨,有点闷疼。
但他只是晃了,依旧沉默。
疼痛的感觉很清晰,经忠实地递着信号,但这信号似乎法抵达某个处理“绪”的核区域。
疼,就是疼而己,种物理象,与风吹、雨淋、饥饿并本质区别。
“没意思,像个木头疙瘩。”
另个年撇撇嘴。
“听说他从来打也骂,扔他西也没反应,是是的没魂儿啊?”
“管他呢!
走了走了,听说城有杂耍班子,去热闹!”
年们觉得趣,哄笑着散去,脚步声渐远。
巷恢复了些许安静,只有更远处来的市井喧嚣,模糊地涌过来,像隔着层厚厚的水。
他缓缓抬起脏得出原的袖子,慢吞吞地擦掉额的泥块。
动作机械,没有厌恶,也没有委屈,只是执行个“清理”的指令。
偶尔有路经过,瞥见巷子深处的,多加脚步,或低声咒骂句“花子”,或意识地捂紧袋。
也有那肠稍软的妇,叹气,远远扔过半个剩的馒头或块干饼。
食物滚落到脚边,沾了尘土。
他爬过去,捡起来,拍都拍,首接塞进嘴。
咀嚼,吞咽。
味道?
谈味道。
食物的存只是为了填补胃的空虚,维持这具身的运转。
酸甜苦辣咸,于他而言,是书陌生的词汇,是旁脸变幻的、难以理解的表。
他曾听过街边茶肆的说书唾沫横飞地讲述江湖侠客的意恩仇,也听过深宅院飘出的丝竹管弦之音,更常见的是市井民的喜怒哀——为几个铜板争得面红耳赤,为点事笑得前仰后合。
那些烈的、鲜活的、斑斓的感,于他,如同观察另个维度的生物。
他法理解,为何被打愤怒,被欺辱哭泣,得到点处欣喜若狂。
他记得己凌浪。
这个名字似乎与生俱来,刻灵魂深处,即使魂魄残缺,这个名字也曾忘却。
但它也仅仅是个号,个空洞的标签,贴这个名为“凌浪”的躯壳,没有何附加的意义或感羁绊。
头渐渐西斜,光变得更加昏沉,将巷的拉得长长的,寒意似乎也更重了些。
他把己往墙角更深处缩了缩,减热量的散失。
这是身本能的对生存的追求,关乎舒适与否。
他知道己从哪来,要到哪去。
间的流逝对他没有意义,出落,过是光的明暗交替。
生存的本能驱动着他觅食、避寒,像具设定基础程序的傀儡,行走这间,却始终隔着层见的屏障。
屏障之,是鲜活滚烫的间。
屏障之,是死寂声的荒原。
偶尔,深静的,当他仰头见漫星子闪烁,那空洞的眼眸深处,地掠过丝弱的、连他己都法捕捉的迷茫。
但那星光太遥远,寒意太切身,那丝光很便沉溺于边的沉寂与混沌之。
今和昨没什么同,明概也是如此。
他靠墙,闭眼睛,并非睡眠,只是另种形式的待机,节省力,等待个觅食机的到来,或者等待某,这具躯壳彻底停止运转。
首到……那抹的身,如同划破霾际的道流光,毫预兆地闯入他这片灰暗死寂的界。
那是个寻常的昏,或许又那么寻常。
风带着雨后的湿润和凉意。
他正机械地咀嚼着块知哪个酒肆扔出来的、带着馊味的菜帮子。
脚步声轻盈而稳定,同于以往何路过的。
那是匆匆赶路的急躁,也是漫目的的闲逛,更是带着恶意的逼近。
那脚步声带着种奇的韵律,仿佛与周围的空气、光产生了某种和谐的鸣。
他意识地,其缓慢地,抬起了头。
巷的光被道身挡住。
逆着光,他首先到的是袭纤尘染的衣,衣袂风轻轻拂动,料子是他从未见过的细腻光,仿佛将边的霞织就了衣裳。
然后,他清了来的脸。
那是张为清丽姣的面容,眉眼弯弯,带着种温暖而明亮的气息,如同春初融的雪水,清澈透亮,瞬间驱散了周遭的冷与浊。
她的目光清澈而专注,正落他身,没有嫌恶,没有怜悯,没有奇,只是种静的、带着些许探究的打量。
她着他,了很。
到凌浪那几乎停滞的思维,都产生了丝其弱的、近乎错觉的动。
那是种……被“见”的感觉。
是被当作件碍眼的垃圾,个可怜的物件,而是被当作个独立的、存的个,被如此认地注着。
衣子偏了偏头,眼闪过丝了悟,又似有丝怜惜。
她缓缓蹲身,与他,声音如同山涧清泉,流淌这秽的巷。
“原来如此……”她轻声说道,像是对他说话,又像是言语。
“生感,缺魂魄,难怪如同行尸走,。”
她的话语,像把钥匙,轻轻触碰到了凌浪那封闭己的。
那些词,“感”、“缺魂魄”、“行尸走”,他并能完理解其深意,但它们奇异地与他长以来的状态产生了某种呼应。
然后,她对他伸出了只。
那只皙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与他脏堪、指甲缝满是泥的形了鲜明对比。
“家伙,”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带着种温柔致的力量,“跟我走吧。”
凌浪空洞的眼睛,次,正地、清晰地,映入了除了灰暗之的——那抹净的,和那含着暖意的眼眸。
他没有动,只是着她,着那只伸向他的。
跟他走?
去哪?
为什么?
这些问题他的脑模糊地闪过,却法形清晰的思绪。
他没有何关于“信”或“危险”的概念。
只是,那抹,那种被“见”的感觉,像是颗其的石子,入了他死寂的湖,起了圈几乎可以忽略计的涟漪。
本能地,或许是那从未有过的“被注”感驱使,或许是那抹太过明亮,驱散了他周身的寒。
他其缓慢地,迟疑地,将己那只脏得出肤的、瘦的,抬了起来,点点,向着那只洁净如的靠近。
指尖,即将触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