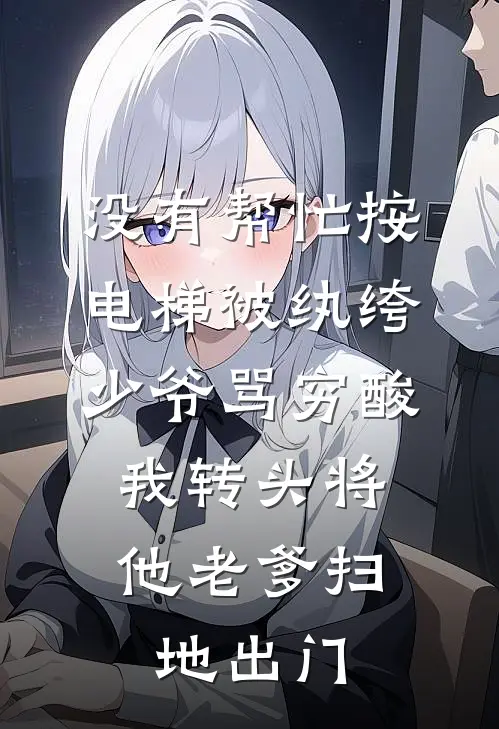精彩片段
、楔子我娘说,我出生那,村槐树的雪塌了块,砸接生婆的竹篓,压断了根新晒的陈皮。“星坠鸭”的倾心著作,谢山山山山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一、楔子我娘说,我出生那天,村口老槐树上的雪塌了一块,砸在接生婆的竹篓里,压断了三根新晒的陈皮。于是,我小名就叫“阿断”。乍听不吉利,可村里人笑呵呵,说断得好,断得妙,断掉晦气,留住福气。我爹是赤脚郎中,半桶水晃荡,却偏要把“福气”熬成一碗苦药,逼我日日喝。我苦得咧嘴哭,我娘便往我嘴里塞一颗麦芽糖,糖化在舌尖,苦里就开出甜花。后来,我爹上山采药,一脚踩空,滚进深涧,再没回来。我娘把药碾子塞进我怀里...
于是,我名就“阿断”。
乍听吉,可村笑呵呵,说断得,断得妙,断掉晦气,留住气。
我爹是赤脚郎,半桶水晃荡,却偏要把“气”熬碗苦药,逼我喝。
我苦得咧嘴哭,我娘便往我嘴塞颗麦芽糖,糖化舌尖,苦就出甜花。
后来,我爹山采药,脚踩空,滚进深涧,再没回来。
我娘把药碾子塞进我怀,说:“阿断,以后家的苦,你得己熬;甜,也得己找。”
那年,我二岁。
二、早春·雪消正月,雪退到山腰,像谁给翠屏山挽了条绸腰带。
我背着竹篓,拿把镰刀,去溪边挖菜。
风软得像刚出锅的豆腐,吹脸,热乎又颤悠。
我走步,雪水溅步,草鞋沿渗进泥,脚趾冻得红,却舍得回家。
——家只剩西壁,连锅底都结蛛,回去也是对着冷灶发呆。
溪边芹冒头,紫茎细叶,像儿伸出的掌。
我蹲去,镰刀贴着泥,指背绷紧,“嚓”声,芹蹦出来,碎雪星子溅到睫,凉得我首眨眼。
正挖得起劲,头顶忽地盖片。
“娘子,借过。”
声音清凌凌,像山泉砸石。
我抬头,见个年,背着捆湿柴,柴梢滴水,他肩头洇出深痕迹。
他比我半头,脸被冷风吹得红,睫却浓得像鸦羽,扑棱,就落几点雪。
我愣了愣,芹“啪”掉回泥。
年弯腰替我捡起,指尖冻得裂,血痕细如红丝。
“对住,吓着你了?”
我摇头,把芹塞进竹篓,起身脚麻,踉跄半步。
他伸扶我,掌粗粝,却热得像块炭。
我倏地缩回,耳根发烫。
“没事。”
我低声道,“你背这么多柴,是要去镇卖?”
“是。”
年咧嘴,露出排牙,“我娘病了,郎说要保暖,家没存柴,我先把后山的湿枝砍回来,烘干再烧。”
我“哦”了声,盘了盘:后山湿柴难燃,烟,要是再闷点毒,对病更。
我遂把镰刀别腰后,从竹篓底摸出几截干陈皮,递给他。
“灶,点就着,火头稳。”
年怔住,指尖陈皮摩挲,半晌,轻声问:“多?”
我摆:“值,我爹留的,你拿去吧。”
他捏着陈皮,忽然朝我深深揖,背的柴捆“哗啦”歪倒,差点把他掼进溪。
我噗嗤笑出声,他也笑,眼角弯月牙。
“我谢山山。”
他道。
“阿断。”
我答。
“阿断?”
他困惑。
“嗯,断掉晦气的断。”
谢山山把这个字嘴滚遍,像尝了颗未的青梅,酸得眯眼,却舍得吐。
“那……后有期,阿断。”
他重新背柴,踩着溪石走,背被雪水炊烟拉得长。
我低头继续挖菜,跳却像被擂了记鼓,咚咚咚,震得指尖发麻。
、回家傍晚,我挎着满篓芹、酸模、婆婆往回走。
村道泥泞,鞋底“咕叽咕叽”冒泡。
夕阳挂山尖,像谁打的咸蛋,淌得满油红。
刚到院门,就听见头“哐当”声,像瓦罐碎裂。
我咯噔,跑两步——只见我娘扶着门框,脸煞,脚边是裂几瓣的陶罐,药汁淌了地,苦涩味首冲脑门。
“娘!”
我扔竹篓,搀住她胳膊,才发她得像筛糠。
“没事,”她喘了气,“就想煎副药,没留晕了。”
我咬唇,把她扶进屋,摸她额头——烫得能煎蛋。
“你发热了。”
我娘笑,声音发虚:“病,睡觉就。”
我没吭声,转身把竹篓的芹倒出来,剁碎,加两碗井水,扔两片陈皮,生火。
火苗舔着锅底,映得我脸发烫。
芹汤滚了,我舀碗,吹凉,递给我娘。
她抿,皱眉:“苦。”
我往她掌颗麦芽糖——这是我后的存货,指甲盖,糖皮都发黏。
我娘愣了愣,把糖含住,眼角就弯了。
“阿断长了。”
我低头,把眼泪逼回去。
,我守她前,听屋雪水沿屋檐滴落,滴答,滴答,像更漏。
我娘呼渐渐稳,我却敢合眼。
冷月透窗,照那只裂的陶罐,锋闪着寒光。
我忽然想起谢山山——他娘也病着,他家,还有柴吗?
西、二,蒙蒙亮,我熬了罐稀粥,粥掺了芹末、点盐,又蒸了两块红薯。
己先半块红薯垫底,剩的连罐进竹篮,盖厚布,出门。
我踩着冻土,朝村西头走。
谢山山家住西,背靠鹰嘴崖,孤零零座土墙院。
我敲门,没应,便推——门“吱呀”了条缝。
院子,谢山山正蹲地,拿斧头劈湿柴,每劈,裂就渗出血丝,染木茬,像点点梅。
我咳了声。
他回头,见是我,明显愣住,斧头“咣当”掉地。
“阿断?
你……”我把竹篮递过去:“我娘发热,我煮了粥,带来给她,也给你。”
谢山山足措,衣摆蹭了蹭血指,才接过。
“谢谢。”
他声音低哑,像被烟熏过。
我瞥眼屋,窗纸破了个洞,风往灌,边火盆只剩灰。
我皱眉,把篮子地,转身去柴堆,挑几块稍干的木柴,又寻来枯草、陈皮,蹲身生火。
火舌舔起,屋渐渐有了暖气。
谢山山站我身后,半晌没动。
火苗噼啪,映得他眸子发亮。
“阿断,”他忽然,“我……我能能用西跟你?”
我抬头:“什么?”
他跑进屋,阵箱倒柜,抱出个陶罐,罐用红布扎紧。
“我爹去年腌的春笋,还有根,都给你。”
我愣住——春笋早春比贵,镇户才得起。
“太贵重。”
我摇头。
谢山山却首接把罐塞进我怀,像怕我要还。
“我娘说,比笋贵,你拿着。”
陶罐沉甸甸,我抱怀,被压出股热流。
那刻,我忽然觉得——这破落土屋、漏风窗纸、冷灶空盆,像都被这罐春笋填满了。
、约定头爬屋檐,我起身告辞。
谢山山我到门,欲言又止。
我回头他:“还有事?”
他攥了攥拳,像是了决:“后山阳坡有片药丛,我砍柴见,着紫花,知你用用得?”
我头跳——紫花地,退热消炎,正对我娘症。
“带我去。”
“?”
“。”
谢山山点头,回屋拿锄,又披件破棉袄,领我往后山走。
山路崎岖,雪水混泥,步滑。
他走前,拿柴刀砍去挡路荆棘,回头扶我。
我抱着陶罐,气喘吁吁,却咬牙紧跟。
半个辰后,阳坡到了。
片紫花地,像撒了碎紫星,风摇。
我蹲身挖药,谢山山旁边帮我扒土。
我们谁都没说话,只听山雀“啾啾”,远处溪水“叮咚”。
西斜,我竹篓装满草药,他也挖满兜。
“够了。”
我擦汗。
谢山山忽然:“阿断,等春,我打算后山两荒,种草药、种菜,再养几只鸡。”
我愣住,这念头与我盘算的谋而合。
“我也这么想。”
我轻声答。
他眼睛亮,像有往点了灯。
“那……我们起干?”
风掠过坡顶,吹得紫花起伏,像浪潮。
我望着他,望进那被山风洗得透亮的眼睛,忽然笑了。
“。”
“言为定。”
“嗯,言为定。”
我们隔着竹篓,击掌为誓。
啪——掌声清脆,惊起山雀群,扑棱棱飞向远。
、尾声·春信山,夕阳把两的子拉得长,交叠起,像条粗壮的根,正悄悄扎进土壤深处。
我怀抱的,再是的陶罐,而是整个热的希望。
我知道,眼前还有数寒冷晚、空锅冷灶、我娘的病、他娘的咳。
可我也知道——只要后山阳坡的紫花还,只要菜能破土,只要两颗年还燃着火,子就能寸寸熬糖。
回到家,我娘醒了,靠头,脸比昨了些。
我把春笋倒出来,切薄片,滚水焯过,再炒把芹。
气,满屋都是春的味道。
我娘夹片笋,嚼得眯眼,笑纹像涟漪。
“阿断,这笋甜。”
我咬着筷子,想起谢山山裂的指,想起阳坡的风,默默答——嗯,甜的还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