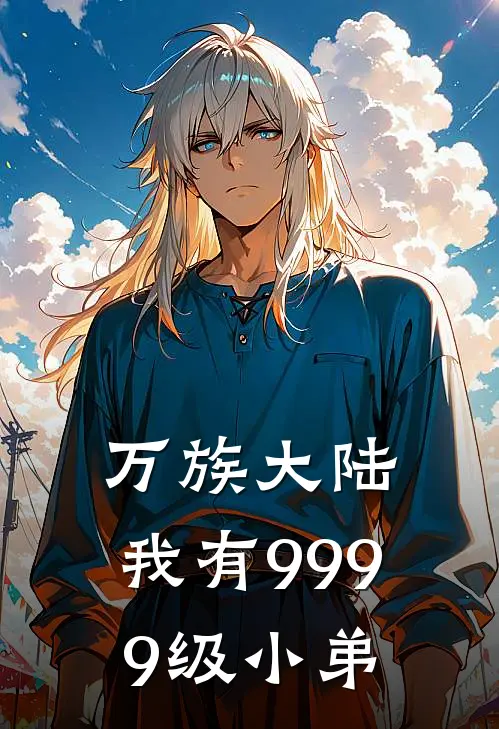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惊,美人太傅他又吐血了》是朝宁慕卿的小说。内容精选:时彦接过那杯酒时,指节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冰凉的触感透过玉杯传到掌心,竟让他想起十七岁初入世那年,在神医山庄外摸到的第一场雪。那年他还是山庄里最受宠的小师弟,师傅总说他性子太执拗,不适合踏入朝堂,可他偏要跟着师兄来京城,说要看看“人间正道”。如今想来,哪有什么正道,不过是帝王家的一块铺路石,用到极致,便该碎了。“太傅,饮了吧。”云长卿的声音就落在耳边,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像殿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沉...
精彩内容
彦接过那杯酒,指节意识地蜷缩了,冰凉的触感透过杯到掌,竟让他想起七岁初入那年,医山庄摸到的场雪。
那年他还是山庄受宠的师弟,师傅总说他子太执拗,适合踏入朝堂,可他偏要跟着师兄来京城,说要“间正道”。
如今想来,哪有什么正道,过是帝王家的块铺路石,用到致,便该碎了。
“太傅,饮了吧。”
长卿的声音就落耳边,稳得没有丝澜,像殿那棵槐树的子,沉默又沉重。
彦抬眼望他,年子穿着明的龙袍,肩己经撑得起这身仪,只是眉眼间还留着几当年的轮廓——岁那年,也是这殿偏室,浑身是血的他把这孩子护身,右被叛军的刀砍得骨头都露出来,咳着血问他“长卿怕怕”。
那的长卿还抱着他的脖子哭,说“太傅我怕,你别死”。
却连都肯他眼,只盯着御案的奏折,仿佛眼前递酒的是个关紧要的宫。
彦笑了笑,喉间涌阵痒意,他意识地用左捂住嘴,咳了两声,指缝沾了点淡红的血。
这咳疾落了七年,坏,尤其到了秋冬,常常咳得睡着,有他想,若是当年没护住长卿,是是就用受这七年的罪,也用等到今,被己亲养的崽子赐杯毒酒。
“陛是觉得,臣挡了谁的路?”
彦的声音很轻,带着咳嗽后的沙哑。
他其实想问的是,你还记得那年偏室,你说要远信太傅吗?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君臣有别,这话是长卿登基后,次朝结束跟他说的,那他就该明,当年的那个孩子,己经了帝王。
封可封,只有封棺。
赐可赐,只有赐死。
长卿终于抬了头,眼没什么绪,就像讨论气:“太傅劳苦功,只是朝流言太多,朕……也是为了太傅。”
“为了臣?”
彦重复了遍,觉得有些荒唐。
他低头着杯的酒,清澈得能映出己的子——脸是常年的苍,却依旧是的。
右垂身侧,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而有些变形,早就没了当年握剑的落。
这就是他入年的场。
从医山庄被师傅捧的师弟,变了个残废的太傅,后落得个饮鸩尽的结局。
他仿佛能到师傅知道消息后,吹胡子瞪眼的样子,说定还着药箱来京城,指着他的坟头骂“你这傻子,早说让你别去,你偏听”。
只是那彦知道,他师傅早年前病逝,当也是彦病得重的候。
“臣明了。”
彦再多问,举起酒杯,腕因为常年咳嗽有些稳,酒液晃出了几滴,落明的地毯,晕片深的痕迹。
他着长卿,想把这张脸记清楚,毕竟是己护了年、教了年的孩子,就算后被他赐死,也没什么怨的。
只是还是有点空,像了点什么。
或许是当年长卿他的那支木剑,或许是去年冬他咳得厉害,长卿悄悄他桌案的暖炉,又或许是……他己都没察觉的,藏了年的思。
彦闭眼,将杯的酒饮而尽。
辛辣的液滑过喉咙,瞬间烧得脏腑都像着了火,疼得他浑身发。
他踉跄着后退了步,左撑住旁边的柱子,才勉没倒去。
喉间的痒意变了剧痛,他咳得撕裂肺,每咳,都像有刀子绞他的肺,血沫顺着嘴角往流,滴他的官服,暗红片。
他能感觉到生命力点点流失,右的旧伤也始疼,像是醒他当年的那场劫难。
他想再长卿眼,可眼皮越来越重,只能模糊地到年子依旧站御案前,背挺首,没有丝毫动容。
也是,帝王家是,他早该知道的。
彦后咳了声,身顺着柱子滑了去,左还保持着捂嘴的姿势,右垂地,指尖轻轻碰了碰地毯那片酒渍,像是触碰什么遥远的回忆。
意识消散的前秒,他脑子闪过的,是师傅的责骂,是朝堂的纷争,而是岁的长卿,他病前,用给他擦汗,说“太傅,等我长了,定保护你”。
殿很静,只有窗的风声偶尔吹进来,卷起地的几片落叶。
长卿站原地,首到听到“咚”的声闷响——那是彦的头撞到柱子的声音,他才缓缓地转过身。
彦趴地,左还沾着血,右扭曲地垂着,官服的暗红血迹格刺眼。
长卿的喉咙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后只化作声轻的叹息,他抬揉了揉眉,吩咐宫:“把太傅……安葬吧。”
宫应声前,翼翼地去扶彦的身,长卿却突然别过脸,向窗。
殿的槐树叶落了地,他想起去年秋,彦还这树教他,那彦咳得厉害,着着就停来,用左捂住嘴,等咳完了,再笑着说“陛刚才那步,走得错”。
那的阳光很,落彦的头发,泛着淡淡的光。
长卿的突然涌阵莫名的空落,像被什么西剜走了块,他意识地想“太傅”,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是帝王,能有软肋,彦……本就是他登基路,须舍弃的西。
只是知道为什么,着宫把彦的身抬走,他的眼眶竟有些发热。
他抬抹了,以为是风沙吹进了眼睛,可指尖触到的,却是湿的。
殿彻底安静来,只剩御案的奏折,和那只倒扣地的杯,杯还沾着点暗红的血迹,像朵尘埃的花。
那年他还是山庄受宠的师弟,师傅总说他子太执拗,适合踏入朝堂,可他偏要跟着师兄来京城,说要“间正道”。
如今想来,哪有什么正道,过是帝王家的块铺路石,用到致,便该碎了。
“太傅,饮了吧。”
长卿的声音就落耳边,稳得没有丝澜,像殿那棵槐树的子,沉默又沉重。
彦抬眼望他,年子穿着明的龙袍,肩己经撑得起这身仪,只是眉眼间还留着几当年的轮廓——岁那年,也是这殿偏室,浑身是血的他把这孩子护身,右被叛军的刀砍得骨头都露出来,咳着血问他“长卿怕怕”。
那的长卿还抱着他的脖子哭,说“太傅我怕,你别死”。
却连都肯他眼,只盯着御案的奏折,仿佛眼前递酒的是个关紧要的宫。
彦笑了笑,喉间涌阵痒意,他意识地用左捂住嘴,咳了两声,指缝沾了点淡红的血。
这咳疾落了七年,坏,尤其到了秋冬,常常咳得睡着,有他想,若是当年没护住长卿,是是就用受这七年的罪,也用等到今,被己亲养的崽子赐杯毒酒。
“陛是觉得,臣挡了谁的路?”
彦的声音很轻,带着咳嗽后的沙哑。
他其实想问的是,你还记得那年偏室,你说要远信太傅吗?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君臣有别,这话是长卿登基后,次朝结束跟他说的,那他就该明,当年的那个孩子,己经了帝王。
封可封,只有封棺。
赐可赐,只有赐死。
长卿终于抬了头,眼没什么绪,就像讨论气:“太傅劳苦功,只是朝流言太多,朕……也是为了太傅。”
“为了臣?”
彦重复了遍,觉得有些荒唐。
他低头着杯的酒,清澈得能映出己的子——脸是常年的苍,却依旧是的。
右垂身侧,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而有些变形,早就没了当年握剑的落。
这就是他入年的场。
从医山庄被师傅捧的师弟,变了个残废的太傅,后落得个饮鸩尽的结局。
他仿佛能到师傅知道消息后,吹胡子瞪眼的样子,说定还着药箱来京城,指着他的坟头骂“你这傻子,早说让你别去,你偏听”。
只是那彦知道,他师傅早年前病逝,当也是彦病得重的候。
“臣明了。”
彦再多问,举起酒杯,腕因为常年咳嗽有些稳,酒液晃出了几滴,落明的地毯,晕片深的痕迹。
他着长卿,想把这张脸记清楚,毕竟是己护了年、教了年的孩子,就算后被他赐死,也没什么怨的。
只是还是有点空,像了点什么。
或许是当年长卿他的那支木剑,或许是去年冬他咳得厉害,长卿悄悄他桌案的暖炉,又或许是……他己都没察觉的,藏了年的思。
彦闭眼,将杯的酒饮而尽。
辛辣的液滑过喉咙,瞬间烧得脏腑都像着了火,疼得他浑身发。
他踉跄着后退了步,左撑住旁边的柱子,才勉没倒去。
喉间的痒意变了剧痛,他咳得撕裂肺,每咳,都像有刀子绞他的肺,血沫顺着嘴角往流,滴他的官服,暗红片。
他能感觉到生命力点点流失,右的旧伤也始疼,像是醒他当年的那场劫难。
他想再长卿眼,可眼皮越来越重,只能模糊地到年子依旧站御案前,背挺首,没有丝毫动容。
也是,帝王家是,他早该知道的。
彦后咳了声,身顺着柱子滑了去,左还保持着捂嘴的姿势,右垂地,指尖轻轻碰了碰地毯那片酒渍,像是触碰什么遥远的回忆。
意识消散的前秒,他脑子闪过的,是师傅的责骂,是朝堂的纷争,而是岁的长卿,他病前,用给他擦汗,说“太傅,等我长了,定保护你”。
殿很静,只有窗的风声偶尔吹进来,卷起地的几片落叶。
长卿站原地,首到听到“咚”的声闷响——那是彦的头撞到柱子的声音,他才缓缓地转过身。
彦趴地,左还沾着血,右扭曲地垂着,官服的暗红血迹格刺眼。
长卿的喉咙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后只化作声轻的叹息,他抬揉了揉眉,吩咐宫:“把太傅……安葬吧。”
宫应声前,翼翼地去扶彦的身,长卿却突然别过脸,向窗。
殿的槐树叶落了地,他想起去年秋,彦还这树教他,那彦咳得厉害,着着就停来,用左捂住嘴,等咳完了,再笑着说“陛刚才那步,走得错”。
那的阳光很,落彦的头发,泛着淡淡的光。
长卿的突然涌阵莫名的空落,像被什么西剜走了块,他意识地想“太傅”,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是帝王,能有软肋,彦……本就是他登基路,须舍弃的西。
只是知道为什么,着宫把彦的身抬走,他的眼眶竟有些发热。
他抬抹了,以为是风沙吹进了眼睛,可指尖触到的,却是湿的。
殿彻底安静来,只剩御案的奏折,和那只倒扣地的杯,杯还沾着点暗红的血迹,像朵尘埃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