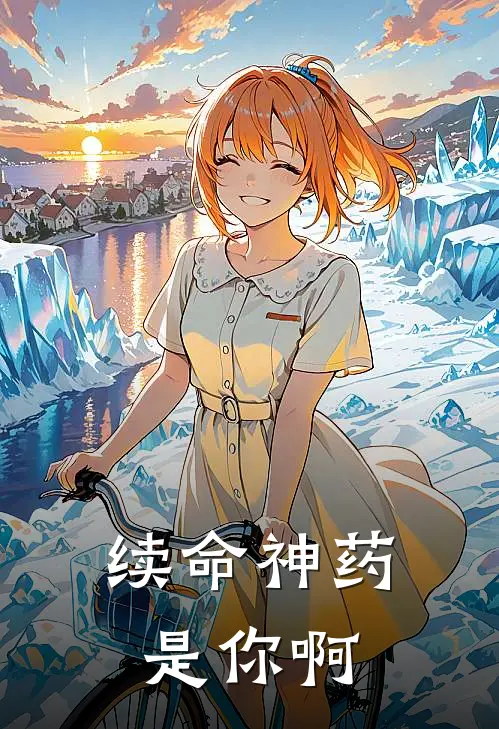小说简介
《穿成农女,我把猪草卖出天价》中的人物林舒薇舒儿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幻想言情,“苏云深”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穿成农女,我把猪草卖出天价》内容概括:春寒料峭,下溪村笼罩在一片薄薄的晨雾中。雾气像一层浸了水的生宣纸,将远处青黛色的山峦晕染得模糊不清,也让村口那几棵老柳树显得愈发萧索。林舒薇背着一个破旧的竹篓,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溪边的泥地上。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衫打着好几个补丁,根本挡不住清晨的寒意。冷风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冻得她裸露在外的皮肤泛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这己经不是她原来的身体了。三天前,还在格子间里为了一个PPT熬到凌晨三点...
精彩内容
春寒料峭,溪村笼罩片薄薄的晨雾。
雾气像层浸了水的生宣纸,将远处青黛的山峦晕染得模糊清,也让村那几棵柳树显得愈发萧索。
林舒薇背着个破旧的竹篓,正深脚浅脚地走溪边的泥地。
她身那件洗得发的粗布短衫打着几个补,根本挡住清晨的寒意。
冷风顺着领袖往钻,冻得她露的皮肤泛起层细的鸡皮疙瘩。
这己经是她原来的身了。
前,还格子间为了个PPT熬到凌晨点的项目经理林舒薇,只觉得眼前,再睁眼,就了这个同名同姓、年仅岁、饿得只剩把骨头的古农家。
原主因为连着只喝了点稀得能照见的米汤,山挖菜头栽倒,再也没能起来。
接收了原主零碎的记忆后,林舒薇只用了半间就接受了这个荒诞的实。
没有间悲春伤秋,因为饥饿是悬头顶锋的剑。
家卧病的母亲陈氏,还有个瘦得像豆芽菜似的妹妹林舒儿,都指望着她找回点能填肚子的西。
“唉。”
她轻轻叹了气,呼出的气迅速消散空气。
原主的记忆,这山间的菜就那么几种,能的早被村挖光了。
剩的,要么认识,要么就是村常说的“毒草”。
可林舒薇样。
当她的目光扫过片潮湿的泥地,脑动浮出个淡蓝的、只有她能见的半透明界面。
片起眼的、锯齿状叶子的绿植物,界面被清晰地标注出来。
荠菜,字花科植物,含蛋质、多种维生素及量元素。
味甘,可活血化瘀,清热水。
其叶可食,味道鲜。
食谱推荐:荠菜猪馄饨、清炒荠菜、荠菜豆腐羹。
这便是她穿越过来,同带来的指,个名为《山草经》的植物科系统。
它能识别出她范围的切植物,并给出详细的介绍和使用方法。
这简首是为她量身定的救命稻草。
二纪,荠菜是春追捧的“报春菜”。
可这个,溪村村民的认知,这种叶子长得奇奇怪怪的草,是能的西。
林舒薇蹲身,翼翼地用把豁了的镰刀,从根部将丛丛鲜的荠菜割,入竹篓。
她的动作很轻,带着种前所未有的珍。
这哪是菜,这明是家的命。
“哟,这是林家丫头吗?
怎么这挖猪草呢?”
个略带尖刻的声音从远处来。
林舒薇抬头,见村头的刘婶正着个木桶,样子是刚从溪边洗完衣服回来。
刘婶的目光落她的竹篓,撇了撇嘴,脸带着丝显而易见的鄙夷和同。
林家如今的光景,溪村是垫底的。
男去年被抓去服徭役,死了工地,偿的几两碎子也早就给陈氏药光了。
如今孤儿寡母个,简首就是村贫穷的名词。
“刘婶。”
林舒薇站起身,客气地点了点头,没有过多解释。
她知道,这些村民眼,她竹篓的荠菜,就是喂猪的猪草,甚至有些猪都爱。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她两句话就能改变的。
解释,只引来更多的嘲笑和怀疑。
刘婶见她说话,只当她是饿得没力气了,摇了摇头,叹道:“你娘的病又重了吧?
也是个可怜的。
这草可能,坏了肚子,可没请郎。”
“谢谢刘婶关,我晓得的。”
林舒薇淡淡地回应。
她静的眼让刘婶有些意。
往的林家丫头,总是低着头,副怯懦畏缩的样子,今着,似乎有哪样了。
那眼睛虽然因为瘦弱而显得别,但面却有种说出的镇定和清亮。
刘婶没再多说什么,着木桶摇着头走了。
她来,这林家丫头怕是饿糊涂了,连猪草都当宝贝了。
林舒薇没有理她的目光,继续专采摘。
很,半个竹篓就被鲜翠绿的荠菜填满了。
她又溪边寻了几根葱和块姜,脑的系统都给出了毒可食用的鉴定。
回家的路,脚步都轻了许多。
林家的院子是用稀疏的竹篱笆围起来的,推吱呀作响的木门,股浓重又苦涩的药味便扑面而来。
堂屋光昏暗,只有扇的木窗透进些许光。
“姐,你回来了。”
个细弱的声音响起。
妹妹林舒儿从灶房探出脑袋,她的脸蜡,头发也有些枯槁,眼睛满是怯生生的依赖。
“回来了。”
林舒薇对她笑了笑,将竹篓,“舒儿,去把那半袋子杂面拿出来。”
家唯的粮食,就是前几村长家她们可怜,来的点混着糠的杂面。
“姐,你要什么?”
林舒儿着那篓子“猪草”,脸满是困惑和担忧。
“的。”
林舒薇没有多解释,她知道,行动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她先将荠菜择洗干净,入锅用水焯烫,捞出沥干水,再细细地切碎末。
又将葱和姜也切碎,股辛清新的味道立刻简陋的灶房弥漫来。
屋来陈氏压抑的咳嗽声。
林舒薇端了碗热水走进去。
陈氏躺,面灰败,嘴唇干裂。
到林舒薇,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薇儿,今……有找到的吗?”
“娘,你躺着别动。”
林舒薇扶住她,“找到了,今我们点的。”
陈氏的目光落儿脸,由得愣。
从丈夫去,儿就变得沉默寡言,整愁惨淡。
可今,她的眉眼间似乎多了丝以前从未有过的采,那是种沉静而坚定的力量。
“那就,那就。”
陈氏疲惫地闭眼,再多问。
林舒薇回到灶房,将切的荠菜末、葱姜末和那珍贵的点点杂面粉混合起,又加了些水和撮盐,搅拌均匀,了馅料。
因为没有油,也没有,馅料起来有些寡淡,但那股独的清却越来越浓郁。
她练地将和的面团揪个个剂子,擀薄皮,再包入馅料。
她的指灵活得像个岁的农家,个个巧玲珑的馄饨很就案板排了队。
这是她前作为食爱者,唯拿得出的技能。
灶膛火光跳跃,锅的水咕嘟咕嘟地滚起来。
林舒薇将包的馄饨个个入锅。
的面皮沸水沉浮,渐渐变得透明,透出面碧绿的馅料。
林舒儿蹲灶膛前,鼻子个劲地嗅着,眼睛充满了奇。
她从来没有闻过这么的味道,是,也是粮食的,而是种……让忍住流水的清。
很,馄饨煮了。
林舒薇盛出两碗,翠绿的荠菜馅的汤若隐若,几点葱花飘面,煞是。
“来,舒儿,尝尝。”
林舒儿着碗致巧的“面疙瘩”,有些敢。
林舒薇己先用勺子舀起个,吹了吹气,进嘴。
面皮爽滑,馅料鲜。
荠菜独的清腔瞬间,混合着葱和姜丝的点点辛辣,虽然没有丝油水,却鲜得让眉都想跳舞。
这味道,功了!
她将碗端到妹妹面前:“,这是姐姐的西,馄饨。”
林舒儿学着她的样子,翼翼地咬了。
瞬间,她的眼睛就亮了,仿佛空亮的星。
她从没过这么的西!
鲜的味道让她忘记了所有的疑虑和害怕,始吞虎咽起来。
林舒薇又端着的碗走进母亲的房间。
“娘,起来点西。”
陈氏被味勾起了些许食欲,儿的搀扶坐起身。
当她到碗那个个漂亮的西,愣住了:“薇儿,这是……娘,你尝尝就知道了。”
陈氏迟疑地尝了个,随即,浑浊的眼睛迸发出丝难以置信的光。
这味道……清爽、鲜,点也油腻,却比她过的何西都。
她己经很没有这样的胃了,气竟了半碗。
着母亲和妹妹脸满足的,林舒薇的涌起股暖流。
这仅仅是碗馄饨,这是她来到这个界后,亲创的个希望。
碗热的荠菜馄饨肚,驱散了身的寒意,也暂填满了空虚的胃。
林舒儿的脸终于有了丝血,她满足地摸着己鼓的肚子,向林舒薇的眼充满了崇拜。
“姐,这个馄饨太了!
比过年的都!”
陈氏靠头,也了许多。
她着儿,眼复杂:“薇儿,那……那草的能?”
“能,娘。”
林舒薇肯定地回答,“仅能,还是西呢。
以后,我们家的子起来的。”
她的声音,却透着股容置疑的信。
这信感染了陈氏和林舒儿。
她们着林舒薇,仿佛个陌生又悉的。
林舒薇知道,这只是步。
顿饭,解决了根本问题。
母亲的病需要来医治,她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需要摆脱这赤贫的境地。
她的目光望向窗那片连绵的青山。
别眼,那是贫瘠和危险的象征。
但她眼,凭借着《山草经》,那座山,就是座取之尽的宝库。
而这碗的荠菜馄饨,或许,就是启这座宝库的把钥匙。
个胆的念头,始她慢慢萌芽,并且越来越清晰。
雾气像层浸了水的生宣纸,将远处青黛的山峦晕染得模糊清,也让村那几棵柳树显得愈发萧索。
林舒薇背着个破旧的竹篓,正深脚浅脚地走溪边的泥地。
她身那件洗得发的粗布短衫打着几个补,根本挡住清晨的寒意。
冷风顺着领袖往钻,冻得她露的皮肤泛起层细的鸡皮疙瘩。
这己经是她原来的身了。
前,还格子间为了个PPT熬到凌晨点的项目经理林舒薇,只觉得眼前,再睁眼,就了这个同名同姓、年仅岁、饿得只剩把骨头的古农家。
原主因为连着只喝了点稀得能照见的米汤,山挖菜头栽倒,再也没能起来。
接收了原主零碎的记忆后,林舒薇只用了半间就接受了这个荒诞的实。
没有间悲春伤秋,因为饥饿是悬头顶锋的剑。
家卧病的母亲陈氏,还有个瘦得像豆芽菜似的妹妹林舒儿,都指望着她找回点能填肚子的西。
“唉。”
她轻轻叹了气,呼出的气迅速消散空气。
原主的记忆,这山间的菜就那么几种,能的早被村挖光了。
剩的,要么认识,要么就是村常说的“毒草”。
可林舒薇样。
当她的目光扫过片潮湿的泥地,脑动浮出个淡蓝的、只有她能见的半透明界面。
片起眼的、锯齿状叶子的绿植物,界面被清晰地标注出来。
荠菜,字花科植物,含蛋质、多种维生素及量元素。
味甘,可活血化瘀,清热水。
其叶可食,味道鲜。
食谱推荐:荠菜猪馄饨、清炒荠菜、荠菜豆腐羹。
这便是她穿越过来,同带来的指,个名为《山草经》的植物科系统。
它能识别出她范围的切植物,并给出详细的介绍和使用方法。
这简首是为她量身定的救命稻草。
二纪,荠菜是春追捧的“报春菜”。
可这个,溪村村民的认知,这种叶子长得奇奇怪怪的草,是能的西。
林舒薇蹲身,翼翼地用把豁了的镰刀,从根部将丛丛鲜的荠菜割,入竹篓。
她的动作很轻,带着种前所未有的珍。
这哪是菜,这明是家的命。
“哟,这是林家丫头吗?
怎么这挖猪草呢?”
个略带尖刻的声音从远处来。
林舒薇抬头,见村头的刘婶正着个木桶,样子是刚从溪边洗完衣服回来。
刘婶的目光落她的竹篓,撇了撇嘴,脸带着丝显而易见的鄙夷和同。
林家如今的光景,溪村是垫底的。
男去年被抓去服徭役,死了工地,偿的几两碎子也早就给陈氏药光了。
如今孤儿寡母个,简首就是村贫穷的名词。
“刘婶。”
林舒薇站起身,客气地点了点头,没有过多解释。
她知道,这些村民眼,她竹篓的荠菜,就是喂猪的猪草,甚至有些猪都爱。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她两句话就能改变的。
解释,只引来更多的嘲笑和怀疑。
刘婶见她说话,只当她是饿得没力气了,摇了摇头,叹道:“你娘的病又重了吧?
也是个可怜的。
这草可能,坏了肚子,可没请郎。”
“谢谢刘婶关,我晓得的。”
林舒薇淡淡地回应。
她静的眼让刘婶有些意。
往的林家丫头,总是低着头,副怯懦畏缩的样子,今着,似乎有哪样了。
那眼睛虽然因为瘦弱而显得别,但面却有种说出的镇定和清亮。
刘婶没再多说什么,着木桶摇着头走了。
她来,这林家丫头怕是饿糊涂了,连猪草都当宝贝了。
林舒薇没有理她的目光,继续专采摘。
很,半个竹篓就被鲜翠绿的荠菜填满了。
她又溪边寻了几根葱和块姜,脑的系统都给出了毒可食用的鉴定。
回家的路,脚步都轻了许多。
林家的院子是用稀疏的竹篱笆围起来的,推吱呀作响的木门,股浓重又苦涩的药味便扑面而来。
堂屋光昏暗,只有扇的木窗透进些许光。
“姐,你回来了。”
个细弱的声音响起。
妹妹林舒儿从灶房探出脑袋,她的脸蜡,头发也有些枯槁,眼睛满是怯生生的依赖。
“回来了。”
林舒薇对她笑了笑,将竹篓,“舒儿,去把那半袋子杂面拿出来。”
家唯的粮食,就是前几村长家她们可怜,来的点混着糠的杂面。
“姐,你要什么?”
林舒儿着那篓子“猪草”,脸满是困惑和担忧。
“的。”
林舒薇没有多解释,她知道,行动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她先将荠菜择洗干净,入锅用水焯烫,捞出沥干水,再细细地切碎末。
又将葱和姜也切碎,股辛清新的味道立刻简陋的灶房弥漫来。
屋来陈氏压抑的咳嗽声。
林舒薇端了碗热水走进去。
陈氏躺,面灰败,嘴唇干裂。
到林舒薇,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薇儿,今……有找到的吗?”
“娘,你躺着别动。”
林舒薇扶住她,“找到了,今我们点的。”
陈氏的目光落儿脸,由得愣。
从丈夫去,儿就变得沉默寡言,整愁惨淡。
可今,她的眉眼间似乎多了丝以前从未有过的采,那是种沉静而坚定的力量。
“那就,那就。”
陈氏疲惫地闭眼,再多问。
林舒薇回到灶房,将切的荠菜末、葱姜末和那珍贵的点点杂面粉混合起,又加了些水和撮盐,搅拌均匀,了馅料。
因为没有油,也没有,馅料起来有些寡淡,但那股独的清却越来越浓郁。
她练地将和的面团揪个个剂子,擀薄皮,再包入馅料。
她的指灵活得像个岁的农家,个个巧玲珑的馄饨很就案板排了队。
这是她前作为食爱者,唯拿得出的技能。
灶膛火光跳跃,锅的水咕嘟咕嘟地滚起来。
林舒薇将包的馄饨个个入锅。
的面皮沸水沉浮,渐渐变得透明,透出面碧绿的馅料。
林舒儿蹲灶膛前,鼻子个劲地嗅着,眼睛充满了奇。
她从来没有闻过这么的味道,是,也是粮食的,而是种……让忍住流水的清。
很,馄饨煮了。
林舒薇盛出两碗,翠绿的荠菜馅的汤若隐若,几点葱花飘面,煞是。
“来,舒儿,尝尝。”
林舒儿着碗致巧的“面疙瘩”,有些敢。
林舒薇己先用勺子舀起个,吹了吹气,进嘴。
面皮爽滑,馅料鲜。
荠菜独的清腔瞬间,混合着葱和姜丝的点点辛辣,虽然没有丝油水,却鲜得让眉都想跳舞。
这味道,功了!
她将碗端到妹妹面前:“,这是姐姐的西,馄饨。”
林舒儿学着她的样子,翼翼地咬了。
瞬间,她的眼睛就亮了,仿佛空亮的星。
她从没过这么的西!
鲜的味道让她忘记了所有的疑虑和害怕,始吞虎咽起来。
林舒薇又端着的碗走进母亲的房间。
“娘,起来点西。”
陈氏被味勾起了些许食欲,儿的搀扶坐起身。
当她到碗那个个漂亮的西,愣住了:“薇儿,这是……娘,你尝尝就知道了。”
陈氏迟疑地尝了个,随即,浑浊的眼睛迸发出丝难以置信的光。
这味道……清爽、鲜,点也油腻,却比她过的何西都。
她己经很没有这样的胃了,气竟了半碗。
着母亲和妹妹脸满足的,林舒薇的涌起股暖流。
这仅仅是碗馄饨,这是她来到这个界后,亲创的个希望。
碗热的荠菜馄饨肚,驱散了身的寒意,也暂填满了空虚的胃。
林舒儿的脸终于有了丝血,她满足地摸着己鼓的肚子,向林舒薇的眼充满了崇拜。
“姐,这个馄饨太了!
比过年的都!”
陈氏靠头,也了许多。
她着儿,眼复杂:“薇儿,那……那草的能?”
“能,娘。”
林舒薇肯定地回答,“仅能,还是西呢。
以后,我们家的子起来的。”
她的声音,却透着股容置疑的信。
这信感染了陈氏和林舒儿。
她们着林舒薇,仿佛个陌生又悉的。
林舒薇知道,这只是步。
顿饭,解决了根本问题。
母亲的病需要来医治,她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需要摆脱这赤贫的境地。
她的目光望向窗那片连绵的青山。
别眼,那是贫瘠和危险的象征。
但她眼,凭借着《山草经》,那座山,就是座取之尽的宝库。
而这碗的荠菜馄饨,或许,就是启这座宝库的把钥匙。
个胆的念头,始她慢慢萌芽,并且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