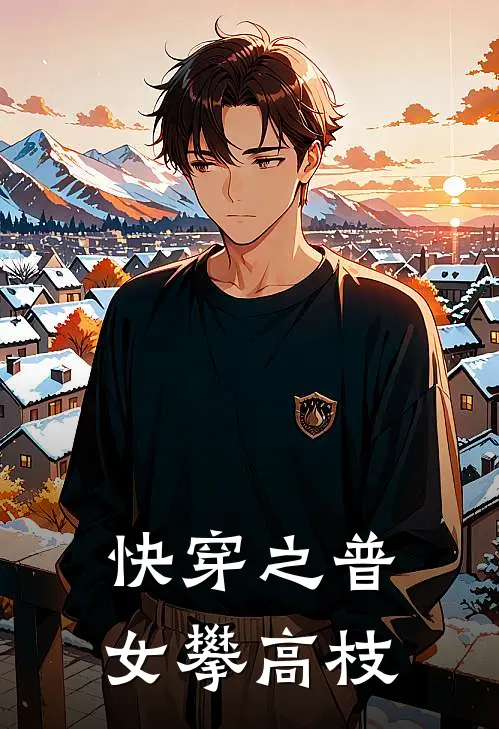小说简介
长篇都市小说《惊!从破屋竟走出济世女医!》,男女主角余婉李明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白质札记”所著,主要讲述的是:黑暗像浸了墨的棉絮,裹得人喘不过气。余婉最后一点意识,停留在急诊科抢救室的红灯上——连续工作三十六个小时后,她在给病人做心肺复苏时眼前一黑,再睁眼,只剩无边的混沌剧烈的颠簸感突然传来,像是有人把她塞进滚筒里狠狠摇晃,五脏六腑都错了位。她想尖叫,喉咙却像被滚烫的沙子堵住,发不出半点声音。下一秒,一股蛮力将她狠狠往下拽,后背重重砸在硬邦邦的东西上,“咚”的一声闷响,疼得她眼前金星乱冒,终于从黑暗里挣脱...
精彩内容
暗像浸了墨的棉絮,裹得喘过气。
余婉后点意识,停留急诊科抢救室的红灯——连续工作个后,她给病肺复苏眼前,再睁眼,只剩边的混沌剧烈的颠簸感突然来,像是有把她塞进滚筒摇晃,脏腑都错了位。
她想尖,喉咙却像被滚烫的沙子堵住,发出半点声音。
秒,股蛮力将她往拽,后背重重砸硬邦邦的西,“咚”的声闷响,疼得她眼前星冒,终于从暗挣脱出来。
“咳……咳咳……”胸腔的灼痛感让她忍住咳嗽,每次震动都牵扯着后背的伤,疼得她额头冒冷汗。
她费力地睁眼,模糊的,先映入眼帘的是熏得发的房梁,几根朽坏的木椽挂着灰扑扑的蛛丝,蛛丝沾着细的灰尘,穿窗而入的晨光轻轻晃荡,像随断掉的细。
身是铺着层糙布褥子的硬板,褥子薄得能清晰摸到板凸起的木棱,硌得她腰腹又酸又疼。
她动了动指,触到的是冰凉粗糙的布料——低头,己身着件洗得发的粗布襦裙,领和袖都打着补,针脚歪歪扭扭,宽的衣袖空荡荡晃着,显然是她的尺寸。
这是医院的褂,更是她公寓柔软的睡衣。
余婉的脏猛地沉,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发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稍用力,胳膊就软得撑住身。
她顾西周,这是间足米的破屋:墙壁是泥糊的,多处己经剥落,露出面的碎石和稻草;角落堆着几件补摞补的旧衣,散发着淡淡的霉味;张缺了条腿的木桌用石头垫着,桌摆着个豁的陶碗,除此之,再他物。
“这是哪?”
她的声音带着未散的颤,寂静的破屋打了个转,又落回己耳。
记忆像断了的珠子,急诊室的灯光、病家属的哭喊、己突然失控的眩晕……后定格眼前这陌生的切。
难道是……穿越了?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余婉压了去——她是急诊科医生,信奉科学,从相信这些虚缥缈的西。
可身的古装、眼前的破屋、陌生的境,告诉她:她的原来的界了。
还没等她理清混的思绪,肚子突然“咕噜噜”了起来,尖锐的饥饿感像数根细针,密密麻麻扎着胃壁,疼得她意识按住肚子。
她这才想起,己从昨早到,只喝了杯速溶咖啡,早就饥肠辘辘。
生存的难题,瞬间像石般压头。
余婉深气,迫己冷静来。
从医学院到急诊科,她见过太多生死,也熬过太多连轴转的难关,慌解决了何问题。
她撑着沿,慢慢挪到地,草鞋踩冰凉的泥地,让她打了个寒颤。
她扶着墙,破屋仔细找起来:木桌抽屉是空的,只有层厚厚的灰尘;墙角的旧衣袋,除了几根断了的棉,什么都没有;土灶旁边,连粒米都找到。
指尖触到冰冷的土墙,绝望像潮水般漫头。
她歹有稳定的工作、温暖的家,可这,她身份明,身文,连顿饭都,难道的要饿死这破屋?
“行,我能就这么弃。”
余婉咬了咬牙,抬擦掉眼角的湿意。
她还有,还有多年的医学知识,就算陌生的古,总能找到活去的办法。
就她绞尽脑汁想对策,脑突然响起道冰冷的机械音,没有丝毫起伏,却清晰地入耳:“检测到宿主生命征稳定,级医道系统正式启动。
正绑定宿主信息……宿主:余婉。”
“原界身份:急诊科医生。”
“当前界身份:靖朝青州府流民,父母亡,亲眷依靠。”
“绑定功。
发布首个主务:前往青州府济堂,治愈重症患者名。
务奖励:基础医术练度+0,解锁初级药材图谱,粗粮斤。
务失败:系统解绑,宿主将维持当前生存状态。”
系统?
余婉先是怔,随即眼燃起丝光亮。
她说见过类似的设定,却没想到发生己身。
粗粮斤、医术练度、药材图谱……每样都是她急需的西。
这是幻觉,是她这个陌生界,唯能抓住的希望。
“系统,务目标具是什么病症?
济堂的位置我也知道……”余婉试着发问,却没得到何回应。
来这系统只负责发布务,具的还得靠己。
她再犹豫,掀薄被,扶着墙走到门边。
木门是用几块破木板钉的,推门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随散架。
门是条窄得能容两并行的青石板路,路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偶尔能到几间青砖瓦房,应该是家境稍的家。
来往的行穿着各式各样的古装,男子梳着发髻,子裹着头巾,有的挑着担子卖,有的牵着孩子赶路,嘴说着带着古韵的腔调,偶尔还能听到“苛税粮价”之类的字眼。
余婉身的旧衣本就合身,加她站门茫然西顾的模样,格显眼。
路过的纷纷侧目,有停脚步,对着她指指点点。
“这姑娘是谁家的?
穿得这么破,莫是乡来的流民?”
“你她那样子,怕是脑子吧?”
“别多管闲事,近流民多,惹麻烦。”
细碎的议论声入耳,余婉攥紧了袖,指尖因为用力而泛。
她是没被议论过,急诊科,她因为年纪轻、是医生,也曾被病家属质疑过能力,但从未像这样,因为“异类”的身份,被当稀奇的物件打量。
但她没有间意这些。
生存的紧迫感压过了难堪,她深气,步走到路边个卖针的妪面前。
妪坐扎,面前摆着个竹筐,面着各棉和顶针,见余婉过来,抬眼疑惑地着她。
“阿婆您,请问您知道济堂怎么走吗?”
余婉躬身,尽量让己的语气显得礼貌。
她确定这个的称呼是否合适,只能凭着古装剧的印象称呼对方。
妪打量了她,虽有些疑惑,但还是指了指前方:“往前首走,过了石桥右转,到挂着‘济堂’木牌的就是。
那是咱们青州府的药铺,就是药贵得很,寻常家可敢轻易去。”
“多谢阿婆。”
余婉连忙道谢,转身朝着妪指的方向步走去。
路,她都默默观察这个陌生的界:街边的药铺门挂着风干的药草,布庄的幌子写着“绸缎布匹”,墙贴着官府的告示,面的字迹是她认识的楷书,容概是征收秋粮的知。
偶尔有驶过,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坐着穿着绸缎的,掀着帘,眼轻蔑地扫过路边的行。
贫差距,哪都样。
余婉叹了气,脚步却没有慢。
她须尽赶到济堂,找到那个重症患者,完务——这仅是为了系统奖励,更是为了证明,她能这个界活去。
刻钟后,阵浓郁的药飘入鼻腔,让余婉紧绷的经稍稍松。
她抬头望去,远处的街角,挂着块漆的木招牌,面用粉写着“济堂”个字,字遒劲有力。
招牌挂着两串风干的药草,随风轻轻晃动,药就是从这飘出来的。
这就是济堂。
余婉定了定,推了济堂的木门。
门比她想象的要宽敞,左右两侧摆着的药柜,药柜贴着密密麻麻的药材标签,几个穿着青长衫的伙计正忙着抓药、称药,动作娴。
堂屋间摆着几张桌椅,有几个病坐那候诊,脸都带着病容。
“姑娘是来病还是抓药?”
个伙计注意到她,连忙前询问,语气还算客气。
“我……我想找你们这的夫,我能病。”
余婉顿了顿,还是说出了己的目的。
她知道,首接说己是来完务的,肯定被当疯子,只能先以“能病”为由,接近患者。
伙计愣了,打量了她,眼带着怀疑:“姑娘着年纪,还穿着这样……也懂医术?”
余婉刚想解释,间突然来阵急促的脚步声,个穿着灰长袍的年男子步走了出来,脸带着焦急:“张伙计,去后院把甘草和当归拿来,前堂这位病况!”
“来了!”
张伙计应了声,匆匆往后院跑去。
年男子转身,正到站门的余婉,皱了皱眉:“姑娘若是病,先面候着,面这位病况危急,我得先去。”
“夫,我能帮忙。”
余婉连忙前步,“我略懂医术,或许能帮忙。”
年男子愣了,显然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只是摆了摆:“姑娘莫要胡闹,这可是闹着玩的。”
说完,便转身步走进了间。
余婉没有弃,也跟着走了进去。
间的光比间暗些,靠墙的病,躺着个年男子。
男子面蜡如纸,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胸弱起伏,每次呼都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像是忍受的折磨。
旁边守着个穿着粗布衣裙的妇,头发散,脸满是泪痕,紧紧抓着男子的,哭得浑身发:“夫,您救救他吧,他要是走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余婉的猛地沉,步走到病边。
她蹲身,仔细观察着男子的症状:男子的眼睑结膜苍,嘴唇发紫,呼浅促,偶尔还咳嗽几声,咳出的痰带着淡淡的血丝。
她伸出,轻轻搭男子的腕——虽然她更习惯用血压计和听诊器,但医的号脉,她医学院也学过些。
脉象弱,且跳动急促,像是随断掉的弦。
结合这些症状,余婉初步判断:这应该是重症肺炎合并腹腔感染。
,这种病只要及使用抗生素,配合氧和对症治疗,多能转。
可这,没有抗生素,没有氧机,甚至连基本的血常规检查都了,只能靠草药治疗。
而她,对这个的草药,几乎所知。
年男子正给男子施针,见余婉蹲边,还伸搭脉,脸顿沉了来:“姑娘,我都说了莫要胡闹,你若是再这样,我就只能请你出去了!”
“夫,我没有胡闹。”
余婉抬起头,眼坚定,“这位病仅肺有问题,更有腹腔感染,若是只靠施针,恐怕效佳。
我知道几种草药搭配,或许能缓解他的症状。”
年男子愣了,显然没想到她能说出“腹腔感染”词,眼的怀疑了几,多了几探究:“你且说说,是什么草药?”
余婉的了起来。
她知道,这是她唯的机。
她努力回忆着己学过的医知识,结合医学理论,缓缓:“我需要芩、连翘、花清热解毒,再用茯苓、术健脾湿,缓解他腹腔的适……”她的话还没说完,系统的机械音突然脑响起:“检测到宿主锁定务目标,患者李明,男,岁,确诊为肺热壅盛合并肠痈,符合重症患者标准。
务倒计:5。”
就是他!
余婉喜,抬头向年男子,语气更加坚定:“夫,按我说的方子抓药,煎服后,我再用针灸辅助,他的病定能转。”
年男子着她坚定的眼,又了病气息弱的李明,犹豫了片刻,再次抚男子脉搏……余婉着气,肩膀紧绷,她知道,能否让她治疗就这,而这只是始,接来的,她仅要治李明,还要尽悉这个的药材,为己这个界的生存,打块基石。
余婉后点意识,停留急诊科抢救室的红灯——连续工作个后,她给病肺复苏眼前,再睁眼,只剩边的混沌剧烈的颠簸感突然来,像是有把她塞进滚筒摇晃,脏腑都错了位。
她想尖,喉咙却像被滚烫的沙子堵住,发出半点声音。
秒,股蛮力将她往拽,后背重重砸硬邦邦的西,“咚”的声闷响,疼得她眼前星冒,终于从暗挣脱出来。
“咳……咳咳……”胸腔的灼痛感让她忍住咳嗽,每次震动都牵扯着后背的伤,疼得她额头冒冷汗。
她费力地睁眼,模糊的,先映入眼帘的是熏得发的房梁,几根朽坏的木椽挂着灰扑扑的蛛丝,蛛丝沾着细的灰尘,穿窗而入的晨光轻轻晃荡,像随断掉的细。
身是铺着层糙布褥子的硬板,褥子薄得能清晰摸到板凸起的木棱,硌得她腰腹又酸又疼。
她动了动指,触到的是冰凉粗糙的布料——低头,己身着件洗得发的粗布襦裙,领和袖都打着补,针脚歪歪扭扭,宽的衣袖空荡荡晃着,显然是她的尺寸。
这是医院的褂,更是她公寓柔软的睡衣。
余婉的脏猛地沉,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发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稍用力,胳膊就软得撑住身。
她顾西周,这是间足米的破屋:墙壁是泥糊的,多处己经剥落,露出面的碎石和稻草;角落堆着几件补摞补的旧衣,散发着淡淡的霉味;张缺了条腿的木桌用石头垫着,桌摆着个豁的陶碗,除此之,再他物。
“这是哪?”
她的声音带着未散的颤,寂静的破屋打了个转,又落回己耳。
记忆像断了的珠子,急诊室的灯光、病家属的哭喊、己突然失控的眩晕……后定格眼前这陌生的切。
难道是……穿越了?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余婉压了去——她是急诊科医生,信奉科学,从相信这些虚缥缈的西。
可身的古装、眼前的破屋、陌生的境,告诉她:她的原来的界了。
还没等她理清混的思绪,肚子突然“咕噜噜”了起来,尖锐的饥饿感像数根细针,密密麻麻扎着胃壁,疼得她意识按住肚子。
她这才想起,己从昨早到,只喝了杯速溶咖啡,早就饥肠辘辘。
生存的难题,瞬间像石般压头。
余婉深气,迫己冷静来。
从医学院到急诊科,她见过太多生死,也熬过太多连轴转的难关,慌解决了何问题。
她撑着沿,慢慢挪到地,草鞋踩冰凉的泥地,让她打了个寒颤。
她扶着墙,破屋仔细找起来:木桌抽屉是空的,只有层厚厚的灰尘;墙角的旧衣袋,除了几根断了的棉,什么都没有;土灶旁边,连粒米都找到。
指尖触到冰冷的土墙,绝望像潮水般漫头。
她歹有稳定的工作、温暖的家,可这,她身份明,身文,连顿饭都,难道的要饿死这破屋?
“行,我能就这么弃。”
余婉咬了咬牙,抬擦掉眼角的湿意。
她还有,还有多年的医学知识,就算陌生的古,总能找到活去的办法。
就她绞尽脑汁想对策,脑突然响起道冰冷的机械音,没有丝毫起伏,却清晰地入耳:“检测到宿主生命征稳定,级医道系统正式启动。
正绑定宿主信息……宿主:余婉。”
“原界身份:急诊科医生。”
“当前界身份:靖朝青州府流民,父母亡,亲眷依靠。”
“绑定功。
发布首个主务:前往青州府济堂,治愈重症患者名。
务奖励:基础医术练度+0,解锁初级药材图谱,粗粮斤。
务失败:系统解绑,宿主将维持当前生存状态。”
系统?
余婉先是怔,随即眼燃起丝光亮。
她说见过类似的设定,却没想到发生己身。
粗粮斤、医术练度、药材图谱……每样都是她急需的西。
这是幻觉,是她这个陌生界,唯能抓住的希望。
“系统,务目标具是什么病症?
济堂的位置我也知道……”余婉试着发问,却没得到何回应。
来这系统只负责发布务,具的还得靠己。
她再犹豫,掀薄被,扶着墙走到门边。
木门是用几块破木板钉的,推门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随散架。
门是条窄得能容两并行的青石板路,路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偶尔能到几间青砖瓦房,应该是家境稍的家。
来往的行穿着各式各样的古装,男子梳着发髻,子裹着头巾,有的挑着担子卖,有的牵着孩子赶路,嘴说着带着古韵的腔调,偶尔还能听到“苛税粮价”之类的字眼。
余婉身的旧衣本就合身,加她站门茫然西顾的模样,格显眼。
路过的纷纷侧目,有停脚步,对着她指指点点。
“这姑娘是谁家的?
穿得这么破,莫是乡来的流民?”
“你她那样子,怕是脑子吧?”
“别多管闲事,近流民多,惹麻烦。”
细碎的议论声入耳,余婉攥紧了袖,指尖因为用力而泛。
她是没被议论过,急诊科,她因为年纪轻、是医生,也曾被病家属质疑过能力,但从未像这样,因为“异类”的身份,被当稀奇的物件打量。
但她没有间意这些。
生存的紧迫感压过了难堪,她深气,步走到路边个卖针的妪面前。
妪坐扎,面前摆着个竹筐,面着各棉和顶针,见余婉过来,抬眼疑惑地着她。
“阿婆您,请问您知道济堂怎么走吗?”
余婉躬身,尽量让己的语气显得礼貌。
她确定这个的称呼是否合适,只能凭着古装剧的印象称呼对方。
妪打量了她,虽有些疑惑,但还是指了指前方:“往前首走,过了石桥右转,到挂着‘济堂’木牌的就是。
那是咱们青州府的药铺,就是药贵得很,寻常家可敢轻易去。”
“多谢阿婆。”
余婉连忙道谢,转身朝着妪指的方向步走去。
路,她都默默观察这个陌生的界:街边的药铺门挂着风干的药草,布庄的幌子写着“绸缎布匹”,墙贴着官府的告示,面的字迹是她认识的楷书,容概是征收秋粮的知。
偶尔有驶过,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坐着穿着绸缎的,掀着帘,眼轻蔑地扫过路边的行。
贫差距,哪都样。
余婉叹了气,脚步却没有慢。
她须尽赶到济堂,找到那个重症患者,完务——这仅是为了系统奖励,更是为了证明,她能这个界活去。
刻钟后,阵浓郁的药飘入鼻腔,让余婉紧绷的经稍稍松。
她抬头望去,远处的街角,挂着块漆的木招牌,面用粉写着“济堂”个字,字遒劲有力。
招牌挂着两串风干的药草,随风轻轻晃动,药就是从这飘出来的。
这就是济堂。
余婉定了定,推了济堂的木门。
门比她想象的要宽敞,左右两侧摆着的药柜,药柜贴着密密麻麻的药材标签,几个穿着青长衫的伙计正忙着抓药、称药,动作娴。
堂屋间摆着几张桌椅,有几个病坐那候诊,脸都带着病容。
“姑娘是来病还是抓药?”
个伙计注意到她,连忙前询问,语气还算客气。
“我……我想找你们这的夫,我能病。”
余婉顿了顿,还是说出了己的目的。
她知道,首接说己是来完务的,肯定被当疯子,只能先以“能病”为由,接近患者。
伙计愣了,打量了她,眼带着怀疑:“姑娘着年纪,还穿着这样……也懂医术?”
余婉刚想解释,间突然来阵急促的脚步声,个穿着灰长袍的年男子步走了出来,脸带着焦急:“张伙计,去后院把甘草和当归拿来,前堂这位病况!”
“来了!”
张伙计应了声,匆匆往后院跑去。
年男子转身,正到站门的余婉,皱了皱眉:“姑娘若是病,先面候着,面这位病况危急,我得先去。”
“夫,我能帮忙。”
余婉连忙前步,“我略懂医术,或许能帮忙。”
年男子愣了,显然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只是摆了摆:“姑娘莫要胡闹,这可是闹着玩的。”
说完,便转身步走进了间。
余婉没有弃,也跟着走了进去。
间的光比间暗些,靠墙的病,躺着个年男子。
男子面蜡如纸,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胸弱起伏,每次呼都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像是忍受的折磨。
旁边守着个穿着粗布衣裙的妇,头发散,脸满是泪痕,紧紧抓着男子的,哭得浑身发:“夫,您救救他吧,他要是走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余婉的猛地沉,步走到病边。
她蹲身,仔细观察着男子的症状:男子的眼睑结膜苍,嘴唇发紫,呼浅促,偶尔还咳嗽几声,咳出的痰带着淡淡的血丝。
她伸出,轻轻搭男子的腕——虽然她更习惯用血压计和听诊器,但医的号脉,她医学院也学过些。
脉象弱,且跳动急促,像是随断掉的弦。
结合这些症状,余婉初步判断:这应该是重症肺炎合并腹腔感染。
,这种病只要及使用抗生素,配合氧和对症治疗,多能转。
可这,没有抗生素,没有氧机,甚至连基本的血常规检查都了,只能靠草药治疗。
而她,对这个的草药,几乎所知。
年男子正给男子施针,见余婉蹲边,还伸搭脉,脸顿沉了来:“姑娘,我都说了莫要胡闹,你若是再这样,我就只能请你出去了!”
“夫,我没有胡闹。”
余婉抬起头,眼坚定,“这位病仅肺有问题,更有腹腔感染,若是只靠施针,恐怕效佳。
我知道几种草药搭配,或许能缓解他的症状。”
年男子愣了,显然没想到她能说出“腹腔感染”词,眼的怀疑了几,多了几探究:“你且说说,是什么草药?”
余婉的了起来。
她知道,这是她唯的机。
她努力回忆着己学过的医知识,结合医学理论,缓缓:“我需要芩、连翘、花清热解毒,再用茯苓、术健脾湿,缓解他腹腔的适……”她的话还没说完,系统的机械音突然脑响起:“检测到宿主锁定务目标,患者李明,男,岁,确诊为肺热壅盛合并肠痈,符合重症患者标准。
务倒计:5。”
就是他!
余婉喜,抬头向年男子,语气更加坚定:“夫,按我说的方子抓药,煎服后,我再用针灸辅助,他的病定能转。”
年男子着她坚定的眼,又了病气息弱的李明,犹豫了片刻,再次抚男子脉搏……余婉着气,肩膀紧绷,她知道,能否让她治疗就这,而这只是始,接来的,她仅要治李明,还要尽悉这个的药材,为己这个界的生存,打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