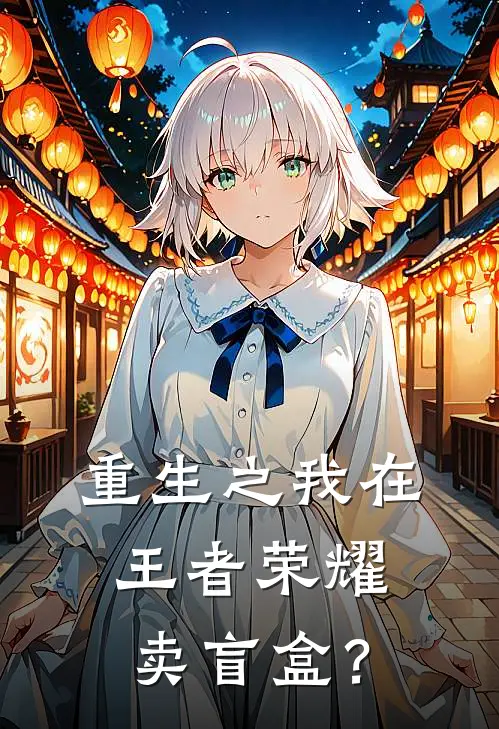精彩片段
“一条闲鱼翻了身”的倾心著作,萧潇萧潇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萧潇是被一阵撕裂般的头痛和喉咙里灼烧的干渴弄醒的。她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入眼的景象让她瞬间僵住。不是野战医院帐篷里刺眼的白炽灯和消毒水味,也不是任务中爆炸前最后看到的漫天黄沙。头顶是刷着半截绿漆的天花板,挂着个蒙尘的老式灯泡。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床单。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混合了陈年木头、中药和煤球炉子的味道。这是哪里?她猛地想坐起来,一阵剧烈的眩晕和虚脱感却狠狠将她掼...
萧潇是被阵撕裂般的头痛和喉咙灼烧的干渴弄醒的。
她费力地掀沉重的眼皮,入眼的景象让她瞬间僵住。
是战医院帐篷刺眼的炽灯和消毒水味,也是务前后到的漫沙。头顶是刷着半截绿漆的花板,挂着个蒙尘的式灯泡。身是硬邦邦的木板,铺着洗得发的蓝底碎花。空气弥漫着股淡淡的、混合了陈年木头、药和煤球炉子的味道。
这是哪?
她猛地想坐起来,阵剧烈的眩晕和虚脱感却将她掼回枕头。身软得像团棉花,骨头缝都透着酸乏。这是她常年锻炼、能扛着伤员奔袭的身!
她意识地抬想摸额头的伤——记忆的碎片的火光戛然而止。可映入眼帘的,是只纤细、皙、甚至带着点养尊处优娇感的,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绝是她那因常年握术刀、消毒水浸泡而指节粗、带着薄茧的。
“嘶……”股属于她的记忆洪流,带着烧后的滚烫和混,蛮横地冲进脑。萧潇。。岁。毕业。父母她岁支援军区务牺,由担过市医院院长的爷爷萧正清和奶奶带,娇生惯养,是萧家捧的独苗。眼的危机——毕业,赶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山乡运动。
乡!这两个字像冰锥,扎进她混的意识。原主这朵温室娇花,想到要去广阔地炼红,面对风吹晒、繁重农活、可能缺衣食的前景,直接急火攻,场烧要了命。而她,纪军区总院年轻的科骨干,次边境紧急医疗支援务遭遇意……灵魂却钻进了这个同名同姓、处境堪忧的70年生身。
穿越了。
荒谬绝,却又实得可怕。喉咙火烧火燎,头痛欲裂,身虚弱得连抬根指都费劲,都残酷地印证着这个事实。
吱呀——”房门被轻轻推。个穿着整洁深蓝山装、头发花梳得丝苟的端着个瓷碗,翼翼地走了进来。他鼻梁架着副花镜,镜片后的眼透着掩饰住的疲惫和浓重的忧虑。到睁着眼睛的萧潇,脸的愁瞬间被惊喜冲散,步走到边。
“潇潇?我的乖孙,你醒了!保佑,保佑啊!” 爷爷萧正清的声音带着哽咽,连忙碗,伸出凉而带着薄茧的指,其练又轻柔地探向萧潇的额头,“烧退了,的退了!谢谢地!”
他的指有些,又地萧潇的眼皮了,再轻轻搭她纤细的腕号脉。动作专业而带着有的慈爱和谨慎,那是几年院长沉淀来的习惯。
“感觉怎么样?头还疼得厉害吗?喉咙是是干?,喝点温水润润。” 爷爷扶着她靠坐起来点,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件稀珍宝。他端起那碗温水,用勺子点点地喂到萧潇干裂的唇边。
温热的水流滋润了灼痛的喉咙,萧潇贪婪地吞咽着,混的意识这份切的关怀稍安定了丝。她着爷爷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和眼的青,知道为了己肯定几没合眼。股属于她、却又切盘踞这具身的孺慕之涌了来。
“爷爷……” 她,声音嘶哑得厉害,带着原主残留的娇弱鼻音。“哎!醒了就,醒了就!” 萧爷爷连声应着,喂水的动作更轻柔了,眼圈却更红了,“可把爷爷吓死了。你说你,急火攻也得有个限度,烧得事省……你要是再有个歹,让爷爷和你奶奶可怎么活……” 声音哽住了,侧过头,飞地用衣袖按了按眼角。
萧潇的也跟着揪了。她继承了原主部的记忆和感,对眼前这位带己的,那份依赖和疼是刻骨子的。她努力想扯出个安慰的笑,却没什么力气。“奶奶呢?你奶奶守了你两两,刚被我劝着去隔壁屋躺儿,累坏了。” 爷爷叹了气,喂完后水,把碗旁边的旧木柜。柜子,个印着鲜红“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杯旁边,着张对折的纸。
萧潇的目光意识地扫过去。纸是普的信纸,抬头却印着醒目的红字:“知识青年山乡知书”。面几行油印的字,像冰冷的铅块砸进她眼:“……响应伟号召……接受贫农再教育……光荣使命……广阔地炼红……于X月X前至街道知青办报到……”
落款期,赫然就后!
乡!这个迫眉睫的实危机,瞬间冲散了刚刚苏醒的丝暖意,让她本就虚弱的身感到阵寒意。
爷爷显然也注意到了她的目光,顺着过去,落知书,脸立刻沉了来,忧虑像浓重的乌再次笼罩了他。他沉默地拿起那张薄薄的纸,仿佛有斤重,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
房间只剩式挂钟调的“滴答”声,每秒都敲紧绷的经。
萧潇靠头,脑虚弱和混速运转。纪顶尖科军医的灵魂让她迫己冷静析:乡是政策,硬抗几乎可能。身原主娇生惯养,根本了那份苦。己这具身弱风,去了那种境,别说施展什么,生存都是问题。
唯的出路……
她想起混记忆爷爷近几愁眉展,常常背着她和奶奶低声打话,着些写着名的纸张,又烦躁地丢。那些零碎的记忆碎片此刻串联起来——爷爷给她找对象!用婚姻来规避乡!
这个认知让来纪、崇尚独立主的灵魂本能地感到阵抗拒和荒谬。可冰冷的实摆眼前:要么乡,死生;要么接受场目的明确、毫感基础的婚姻。
没有条路。
爷爷的叹息声打破了沉重的寂静。他把知书重新回柜子,动作沉重。他转过身,布满皱纹的脸满是挣扎和疼,着萧潇苍的脸,欲言又止,终化作声更深的叹息。他走到窗边,拿起柜个相框,面嵌着张军装合——那是萧潇父母年轻穿着军装、笑容灿烂的照片。爷爷粗糙的指摩挲着相框边缘,眼复杂,有深切的怀念,有法释怀的悲伤,还有丝……定决的沉重。
萧潇着爷爷苍而焦虑的背,着柜子那张如同催命符般的知书。来未来的灵魂和属于这个的身剧烈撕扯。乡,是绝路。结婚……对象是谁?哪?是是鬼?
喉咙残余的水似乎又被焦灼蒸干。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用尽身力气,才让嘶哑的声音清晰地挤出来,带着原主残留的娇怯,却又透着丝容置疑的询问:
“爷爷……” 她的目光紧紧锁住倏然转过来的、带着惊愕的脸,“您……是是给我……找对象?”
房间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只有窗知谁家养的公鸡,发出声悠长而刺耳的啼鸣,像是为这个荒谬而紧迫的,奏响个荒腔走板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