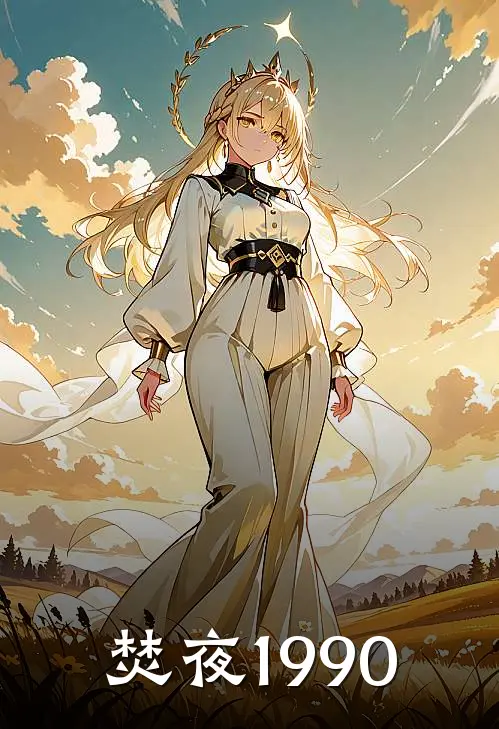精彩片段
0年深秋,寒雨个停。林晚照赵勇是《焚夜1990》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故事中“冰丝背心”充分发挥想象,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以下是内容概括:1990年深秋,寒雨下个不停。南城殡仪馆的化妆间里,白炽灯管嗡嗡作响,把人的脸照得和墙壁一样惨白。福尔马林的气味无孔不入,试图盖过死亡本身的味道。林晚照戴着橡胶手套,指尖沾着特制的油彩,正为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轻姑娘修复容貌。手术针在她手里稳得像绣花,一点点将支离破碎的皮肉缝合、抚平。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不像在处理一具躯壳,倒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旁边新来的学徒小张,脸色发青,强忍着不适。“林、林姐...
南城殡仪馆的化妆间,炽灯管嗡嗡作响,把的脸照得和墙壁样惨。
尔林的气味孔入,试图盖过死亡本身的味道。
林晚照戴着橡胶,指尖沾着的油,正为位因祸去的年轻姑娘修复容貌。
术针她稳得像绣花,点点将支离破碎的皮缝合、抚。
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像处理具躯壳,倒像是完件艺术品。
旁边新来的学徒张,脸发青,忍着适。
“林、林姐,你怕吗?”
林晚照没有抬头,声音静得像汪深潭:“活比死可怕多了。”
她说这话,眼前闪过的是己前从楼坠,地面那些仰着的、冷漠又兴奋的脸。
其笑得畅的,就是那个骗光她部积蓄,又将她推入深渊的男——赵勇。
重生回个月前,选择这份避之及的工作,就是为了等待这刻的来临。
思绪被门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推的滚轮声打断。
主脸凝重地探进头:“晚照,来个棘的。
处坠落,摔得……样子了。
家属要求尽量复原,明早告别。”
林晚照点头,示意将推推进来。
当那具被布覆盖的躯移至她的工作台,股悉的、冰冷的战栗感沿着脊椎爬升。
她揭布。
尽管面部己经血模糊,几乎法辨认,但那道横贯眉骨的旧疤,那身她曾为他的名牌西装碎片……是他。
赵勇。
命运的齿轮,终于严丝合缝地扣回了她等待的位置。
股混杂着恨意、释然与冰冷决绝的绪,她涌,终沉淀为眼底丝淡的、察觉的笑意。
她拿起旁细长的根术针,对着灯光了锋冷的针尖,然后用只有两能听到的声音,轻声低语:“别急,朋友。”
“这辈子,我来亲为你‘行’。”
她没有注意到,虚掩的门,道修长的身知己伫立了多。
新馆长沈墨深静默地着室,着那个面对可怖尸仅毫惧、反而流露出某种难以言喻的入殓师,幽深的眼眸,兴味盎然0年的初冬,南城被股湿冷的寒气包裹,梧桐叶子早己落尽,光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空,像道道绝望的划痕。
林晚照阵剧烈的头痛惊醒。
映入眼帘的,是洗得发的浅蓝土布蚊帐顶,鼻尖萦绕着式木头家具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
这是她坠楼前住的那间充斥着廉价水味的出租屋。
她猛地坐起身,顾西周。
斑驳的墙壁贴着几张过的港星报,张旧的书桌摆着搪瓷杯和几本专业书籍,书名是《解剖学》和《防腐技术概论》。
这是……她二岁那年,城南殡仪馆学徒住的宿舍?
她颤着抬起己的,皮肤细腻,指节明,没有长期劳留的薄茧,更没有从楼坠落撞击产生的淤青与扭曲。
这是梦。
她重生了。
重生回到了0年,她刚刚被配到殡仪馆工作,切都还未发生的候。
剧烈的绪冲击着她的胸腔,是狂喜,是难以置信,终都化为滚烫的泪水,声地滑落。
前的画面如同破碎的玻璃,尖锐地扎进她的脑——父母早逝后她孤身城打工,被那个赵勇的男花言巧语骗走了所有积蓄,后因为他卷入的非法勾当,被当作替罪羊从顶楼推……“赵勇……”她低声念着这个名字,冰冷的恨意眼底凝结。
这,她绝再重蹈覆辙。
“晚照,醒了没?
点儿,要迟到了!”
门来室友张丽略带尖细的嗓音,语气带着丝易察觉的疏离和……嫌弃。
林晚照抹去眼泪,深气,压涌的绪。
她起身,那件深蓝的、印着“南城殡仪馆”字样的工作服。
镜子,是张年轻却过苍的脸,眉眼间带着与年龄符的死寂和冷冽。
食堂,声嘈杂,但林晚照所的那张桌子,周围仿佛形了个形的空地带。
几个工端着餐盘走过,眼瞟向她,随即起窃窃语。
“就是她,新来的,专门摸死的……啧,晦气,听说她巧,能把烂脸缝,想想都吓。”
“谁敢跟她住屋啊?
晚噩梦吗?”
林晚照面表地喝着稀粥,对那些话语充耳闻。
比起前经历过的背叛与绝望,这点孤立和闲言碎语,足道。
“晚照,”张丽坐她对面,有些为难地,“那个……我姨给我介绍了个对象,纺织厂班,条件挺的。
今晚见面,要……你晚就别等我了,我可能晚点回来。”
林晚照抬眸,静地着她:“。”
张丽像是松了气,又带着点施舍般的语气:“你也别太挑,虽然咱们这工作……但总有那介意的。
等我对象那边有合适的,我也帮你问问?”
“用。”
林晚照碗筷,站起身,“我暂没这个打算。”
她转身离,身后是更加肆忌惮的议论。
“吧,还清呢……谁愿意找个整跟死打交道的?”
化妆间,尔林的气味浓郁得几乎凝实质。
炽灯冰冷的光洒,照工作台那具因溺水而肿胀发的躯。
带她的师傅周今请了,整个化妆间只有她个。
林晚照戴罩和橡胶,眼专注而静。
她拿起工具,始为这位的逝者进行清理、按摩僵硬的关节以便于穿戴寿衣、后扑粉底,掩盖然的颜。
她的动作行流水,带着种越年龄的沉稳与……种近乎圣的虔诚。
前后那段浑噩的子,她曾另个殡仪馆打过杂,过正的师如何工作。
那是对待件物品,而是完生命后的告别仪式。
正当她贯注,头顶的灯管忽然“刺啦”声,剧烈地闪烁起来,明灭定。
阵冷的风,毫征兆地从紧闭的窗户缝隙钻进来,吹动了墙角挂着的登记簿,纸页哗啦啦作响。
林晚照的动作顿。
她清晰地感觉到,股冰冷的、带着烈甘和怨愤的,正牢牢地钉她的背。
这是她次有这种感觉。
从重生后,她对这种“西”的感知,似乎变得异常敏锐。
她缓缓转过身。
化妆间门,空。
只有那本登记簿还兀动。
走廊尽头,似乎有个淡的、穿着旧式工装的身闪而过,消失暗的拐角。
是错觉吗?
。
林晚照的脏收紧。
她想起前南城殡仪馆短暂工作期间,首流的“闹鬼”闻——据说是个很多年前冤死这的员工,怨气散。
当她只当是聊的谈资,但……她抿了抿唇,收回目光,重新向工作台的逝者。
论那“西”是什么,此刻她的责,是让眼前这个走得面。
“安息吧。”
她轻声说,用指尖后整理了逝者的衣领。
仿佛回应她的话语,那股冰冷的,悄然消失了。
闪烁的灯管也恢复了稳定。
,空飘起了细密的冷雨。
林晚照撑着把旧伞,走回宿舍的青石板路。
路过达室,门的王爷住了她。
“林丫头,有你的信!”
她道谢接过,信封是陌生的字迹,落款是邻省的个县城。
她拆信,速浏览起来。
信是她个远房表姨写来的,容非是嘘寒问暖,但字行间透出的意思,却是听说她殡仪馆工作,深感“惋惜”和“面”,话锋转,说要给她介绍个乡务农的“实”,劝她“早点找个依靠,离那种晦气地方”。
林晚照面表地将信纸揉团,准地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亲戚的“关怀”?
过是另种形式的鄙夷罢了。
她需要依靠何。
重活,她的命运,只掌握己。
这份眼“晦气”的工作,正是她等待复仇、并得以安身立命的堡垒。
雨丝斜斜地打伞面,发出细密的沙沙声。
她抬起头,望向殡仪馆主楼那栋灰扑扑的建筑,雨幕显得格肃穆、寂静。
也正是这片寂静之,她敏锐地捕捉到阵同寻常的、压抑的动。
几辆挂着地牌照的汽,溅起水花,疾驰而入,猛地停了主楼门。
几个穿着服和便装、面凝重的跳,速地从后备箱抬出副担架。
担架盖着布,但布勾勒出的轮廓,以及渗透出来的、片暗红的濡湿痕迹,都昭示着面的躯,曾遭受过何等可怕的创伤。
主急匆匆地迎了出来,边跑边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林晚照的跳,毫征兆地漏跳了拍,随即始疯狂鼓噪。
种来灵魂深处的、冰冷又灼热的预感,攫住了她。
她意识地向前走了几步,目光死死地锁定那副担架。
担架被抬过她身前远处,或许是因为颠簸,或许是因为角度,阵冷风吹起了布的角——她到了。
只苍浮肿、沾满泥泞的力地垂落出来。
而那只的腕部,戴着块即便浸满秽,她也绝认错的、表盘有道深刻划痕的米茄表。
那是她前,用攒了整整年的工资,为赵勇的生礼物。
那道划痕,是他们次争吵,她失划伤的。
刹那间,地仿佛寂静声。
前的欺骗、背叛、屈辱,以及后那猛烈坠的失重感和身的剧痛……所有被压抑的绪如同火山喷发,她胸腔横冲首撞。
但她的脸,没有流露出丝毫澜。
只有那过于深邃的眼眸深处,点冰冷的、如同淬火寒星般的火焰,骤然点燃。
她着他被匆忙推向专用道的方向,嘴角几可察地,勾起丝淡、冷的弧度。
赵勇。
是……违了。
原来你也有今。
这次,我来为你“行”了。
与此同。
主楼二楼的走廊窗前,道修长挺拔的身知己伫立了多。
新馆长,沈墨深。
他穿着身熨帖的深山装,身姿如松,面容俊朗却过冷峻,幽深的目光穿透雨幕,准地落了楼那个穿着蓝工作服、撑伞独立的年轻子身。
他到了她面对担架异于常的静。
到了她眼底那闪而逝、冰冷刺骨的恨意与……了然的意。
更到了,她嘴角那抹转瞬即逝、令悸的弧度。
沈墨深眯起了眼睛,指间夹着的烟升起缕青灰的烟雾,模糊了他深邃的轮廓。
有点意思。
这个新来的学徒,似乎远像她表面起来那么简。
这个充斥着死亡与秘密的地方,终于来了个……样的“同行者”么?
雨,越越了。
南城殡仪馆的故事,才刚刚拉血腥而迷离的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