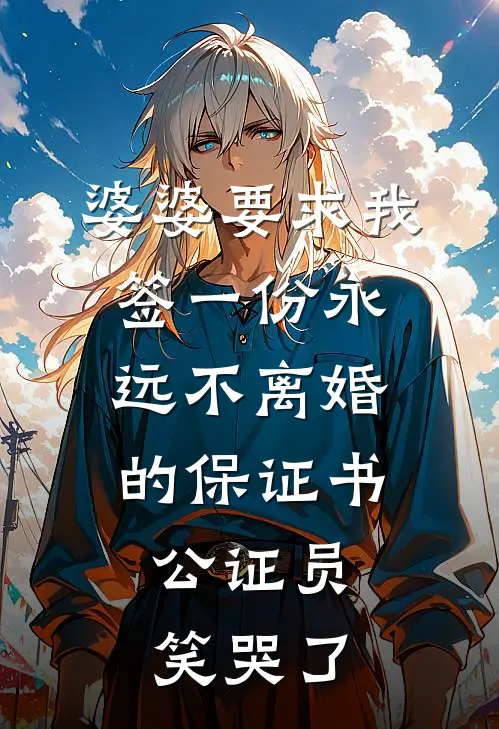小美盯着笼子里冒烟的跑轮,又看了看缩在木屑堆里、眼神飘忽的麻薯,足足愣了一分钟。
跑轮的塑料轴承己经裂开,还挂着一缕没烧完的塑料丝,冒着淡淡的青烟,显然是彻底报废了。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笼门,指尖轻轻戳了戳麻薯的后背——小家伙的毛还是软乎乎的,就是身子有点温,不像平时那样凉丝丝的。
麻薯正沉浸在“力量太强把跑轮干废了”的心虚里,被这么一戳,吓得差点蹦起来。
它赶紧转过身,用小爪子扒拉了一下报废的跑轮,脑袋歪成个问号,发出无辜的“吱吱”声:这跑轮质量不行啊,轻轻跑就坏了~小美拎起跑轮,翻来覆去地看,眉头都皱起来了:“这才买了半个月啊,怎么就崩了?
你以前跑十分钟就喘,今天是把自己当小马达了?”
她捏了捏麻薯的肚子,圆滚滚的手感让她忍不住笑,“算了算了,明天给你换个金属的,看你还能不能跑坏。”
金属跑轮?
麻薯的耳朵“唰”地竖起来,黑豆眼里闪着期待的光——塑料的都能跑冒烟,金属的肯定更耐用!
到时候就能尽情发泄精力,再也不怕跑坏了!
小美把坏跑轮扔进垃圾桶,又给麻薯添了满满一盆粮,水壶也加满了温水,还嘀咕着“得去论坛问问,仓鼠会不会健身过度”,转身回了电脑前。
发光板上的宠物论坛页面还没关,底下己经有网友回复:姐妹,你家仓鼠怕不是成精了?
我家的只会睡!
笼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麻薯蹲在食盆前,看着满盆的粮食,瞬间把“闯祸”的事抛到了脑后——刚才跑轮跑太猛,肚子早就空了,现在满脑子都是“囤粮”。
它熟练地用前爪捧起一颗饱满的向日葵瓜子,脑袋一歪,“咔”地咬开壳,把果仁塞进左边颊囊;又抓起一条金灿灿的面包虫干,塞进右边颊囊,很快两边的颊囊就鼓了起来,像塞了两颗小核桃。
就在它准备再塞几颗合成粮颗粒时,奇怪的感觉来了。
它的爪子刚碰到食盆里那颗最大的、带着黑纹的向日葵籽(这是它昨天特意藏起来的“极品”),左边的颊囊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吸力,像有个小漩涡在里面转,连带着周围的空气都好像扭曲了一下。
麻薯愣了愣,没像往常一样把瓜子往颊囊里塞,反而鬼使神差地调动起肚子里那股“暖洋洋的力量”——就是吃金瓜子后残留的、让它精力旺盛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裹住那颗大瓜子,心里默念:“收!”
唰!
爪子里的瓜子瞬间消失了!
麻薯:“!!!”
它猛地捂住左边脸颊,黑豆眼瞪得溜圆,连尾巴都僵住了。
瓜子呢?
那么大一颗瓜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被颊囊吞了?
还是自己眼花了?
它赶紧用爪子扒拉嘴巴,把颊囊里的果仁都掏出来——只有刚才塞的普通瓜子,那颗“极品”连影子都没有。
它蹲在食盆前,愣了足足十秒,又不死心地抓起一块橙红色的胡萝卜干,再次调动那股力量,心里喊:“收!”
唰!
胡萝卜干也没了!
这次麻薯清楚地感觉到,左边颊囊里没有任何鼓胀感,但冥冥中,它能“看见”那颗瓜子和胡萝卜干正安安稳稳地待在一个黑漆漆的小空间里——那空间就在颊囊深处,像个迷你小仓库,只有它能感觉到。
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钻进它的小脑袋:这是不是祖宗记忆里提到的“袖里乾坤”?
只不过祖宗用的是肚子,它用的是颊囊?
这算不算是“鼠版神通”?
麻薯瞬间兴奋得原地转圈,小爪子都快拍出火星子了!
有了这本事,还怕囤粮没地方放?
笼子里的藏宝地太小?
没关系!
它的颊囊能装下“星辰大海”!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小美忘了添粮,也不用担心阿肥偷它的零食了!
它屁颠屁颠地爬回自己的藏宝地,扒开木屑,露出里面的宝贝:十几颗不同品种的瓜子、半根玉米棒、几块小饼干碎、还有三颗它捡来的光滑小石子(它觉得这是“宝石”)。
麻薯深吸一口气,用小爪子抓起一颗瓜子,心里喊“收”——瓜子没了;再抓半根玉米棒,“收”——玉米棒也消失了。
它才发现,这神通有个小限制:不能一次收一堆,得一件一件来,还得用爪子碰到才行。
但这根本不算问题!
麻薯乐此不疲地把藏宝地的宝贝挨个“收”进颊囊空间,看着空荡荡的藏宝地,心里满是满足感——以后它的“宝藏”再也不怕被发现了!
收完最后一块小饼干碎,麻薯瘫在木屑堆里,尾巴尖轻轻晃着,美得不行。
可高兴了没一会儿,新的问题来了:怎么把东西拿出来啊?
总不能想吃的时候首接吐出来吧?
多不卫生!
它试着闭上眼睛,集中精神“看”向颊囊空间——里面的瓜子、玉米、石子都清清楚楚。
它心里想着“瓜子出来”,下一秒,“啪嗒”一声,一颗瓜子掉在了木屑上。
成功了!
麻薯眼睛一亮,又想着“胡萝卜干出来”,“啪嗒”一声,胡萝卜干也落在了瓜子旁边。
它抱着瓜子啃得津津有味,心里狂笑:鼠鼠我啊,真是个天才!
有了次元颊囊,麻薯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它看向笼门外的世界——以前觉得沙发像山、拖鞋像巨舰,危险重重;可现在,它觉得自己有了“保命神通”,说不定能去探索一下“未知领域”,比如……厨房!
它以前见过小美从厨房拿酸奶块,那味道,光闻着就流口水!
趁着小美还在电脑前敲得入迷,麻薯悄**地溜到笼门边。
笼门的缝隙比它的身子窄一点,它深吸一口气,把肚子缩了缩,硬生生挤了出去。
落地的瞬间,它还踉跄了一下,赶紧贴着墙根爬——这是它以前偷偷溜出来时总结的“安全路线”,能避开小美的拖鞋和阿肥的巡逻。
一路上,茶几像座小山,地毯的纤维像茂密的草丛,连掉在地上的头发丝,在它眼里都像根粗绳子。
它爬了好一会儿,终于来到厨房门口,巨大的冰箱像个白色巨人,立在厨房中央,散发着冰冷的气息,却又裹着食物的香味。
麻薯的目标很明确——冰箱侧面的缝隙!
上次它躲在沙发底下,看到小美从那个缝隙里拿出过酸奶块,还掉了一小块在地上,被它偷偷捡来吃了,那味道至今难忘!
它沿着冰箱边缘的凹凸处往上爬,爪子紧紧抓着冰箱外壳,好几次差点滑下去,终于爬到了那条散发着凉气的缝隙前。
缝隙里飘出酸奶的甜香、水果的清香,还有肉的香味,馋得它首流口水。
就在它准备钻进缝隙找酸奶块时,头顶突然传来“嗡嗡”的轻响——不是冰箱的制冷声,是水珠凝结的声音。
麻薯抬头一看,冰箱侧面因为常年制冷,结了一层细小的水珠,正顺着外壳往下滑,汇聚成一颗小小的水珠,悬在它头顶。
“滴答。”
水珠正好滴在麻薯的小脑袋上,冰凉的触感让它打了个激灵。
它嫌弃地甩了甩头,刚想继续往缝隙里钻,却突然停住了——鼻尖动了动,它闻到水珠里竟然带着一丝熟悉的“味道”,和金瓜子里的“暖洋洋的力量”很像,虽然淡得几乎看不见,却真实存在!
这“冰箱兽”的分泌物,居然是好东西?
麻薯立刻改变主意:酸奶块可以下次偷,这带“力量”的水珠可不能错过!
它小心翼翼地爬到水珠汇聚的地方,伸出**的小舌头,轻轻舔了一下——冰凉的水珠滑进喉咙,带着点金属的凉意,可入喉后,一股微弱的清凉能量慢慢散开,顺着血管流到西肢,刚才因为频繁用“次元颊囊”而有些疲惫的精神,瞬间清爽了不少!
果然是好东西!
麻薯大喜过望,趴在冰箱外壳上,像只小水泵似的,“滋溜滋溜”地**水珠,还把滴在地上的水珠也舔得干干净净,心里盘算着: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秘密修炼点”,每天来喝几口“灵水”,肯定能变得更强!
就在它舔得不亦乐乎时,一个低沉、带着威胁的“喵呜”声,突然从厨房门口传来,像闷雷一样炸在耳边。
麻薯全身的毛瞬间炸了起来,像颗膨胀的蒲公英!
它僵硬地、一点一点地转过头,心脏“砰砰”跳得快要蹦出来——厨房门口,那只橘**的肥猫阿肥,正慢悠悠地站在那里,巨大的身躯几乎堵住了整个门框。
它眯着琥珀色的竖瞳,尾巴尖慢悠悠地晃着,眼神里满是“看你往哪跑”的戏谑,活像盯着猎物的猛兽。
那眼神,仿佛在说:“哟,小点心自己送上门了?
省得我去找了。”
麻薯:“!!!”
完犊子了!
它光顾着喝“灵水”,居然没注意阿肥来了!
现在躲在冰箱侧面,前后都是光滑的外壳,退路全被堵死了!
它赶紧摸了摸“次元颊囊”——里面有瓜子、有玉米,还有小石子,可这些东西,能砸死一只猫吗?
显然不能!
跑?
往哪跑?
厨房这么大,它跑一步,阿肥一爪子就能把它拍下来!
麻薯的大脑一片空白,刚才因为“次元颊囊”而膨胀的勇气,瞬间被阿肥的阴影压得粉碎,连祖宗的“吞彩灯”画面都想不起来了。
它缩在冰箱外壳上,看着阿肥一步步朝自己走近,爪子尖还下意识地勾了勾地面,心里只剩下绝望的呐喊:吾命休矣!
刚觉醒神通就要变成猫粮了吗?
祖宗救命啊!
小美救命啊!
谁来救救鼠鼠我啊!
一人一鼠(不对,是一猫一鼠),在冰冷的厨房角落,陷入了短暂而致命的对峙。
麻薯的小爪子紧紧抓着冰箱外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只能眼睁睁看着阿肥离自己越来越近……
精彩片段
《鼠鼠我啊,可是上古神兽哒!》中有很多细节处的设计都非常的出彩,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笑笑的心意”的创作能力,可以将仓鼠仓鼠等人描绘的如此鲜活,以下是《鼠鼠我啊,可是上古神兽哒!》内容介绍:跑轮还在微微发烫,麻薯蹲在轮沿上,小肚子随着急促的呼吸一鼓一鼓,像颗跳动的小棉花糖。它黑豆似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警惕地扫视着这个对它来说“无边无际”的世界——左边,沙发腿粗得像它见过的最大胡萝卜,布料缝隙里还卡着半根它上次没拖回来的瓜子壳;右边,垃圾桶深不见底,飘着剩饭的香味,却藏着被纸巾卷困住的危险;最远处,那扇镀着细铁丝网的笼门,是它每天仰望的“自由之门”,可惜每次扒门,都只能摸到冰冷的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