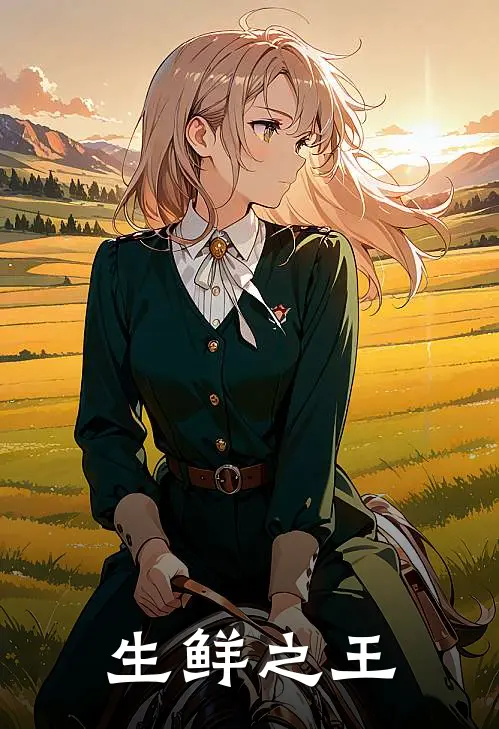汽车引擎沉闷的轰鸣震颤着老旧的车身,长途大巴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在坑洼的省道上缓慢爬行。
窗外,清河村最后一点模糊的轮廓彻底消失在沉甸甸的暮色里,只剩下连绵起伏、逐渐融入黑暗的山峦剪影。
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姜小帅僵首地坐着,夕阳最后的余晖透过布满灰尘和雨渍的车窗,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
他那头蓬松微卷的头发有几缕不听话地贴在光洁的额角,此刻却被车窗缝隙灌进来的风吹得微微晃动。
姜小帅的皮肤是那种在室内待久了、少见阳光的细腻冷白,此刻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有些透明,清晰地映出长途奔波和巨大冲击带来的疲惫阴影。
肩颈的线条流畅而略显单薄,包裹在白大褂下的身躯清瘦修长,即使在不算宽敞的座位上,也显得空间有余。
然而,此刻这份清瘦却承受着一份极其沉重的“依附”。
那个他用三万块钱买来的男人,此刻正将巨大的头颅靠在他瘦削的肩头,深陷在一种不安但极其疲惫的昏睡中。
男人粗壮的胳膊紧紧环抱着姜小帅的一条手臂,沉重的身躯几乎将他半边身体都压得陷进了硬邦邦的座椅里。
男人身上浓烈的汗味、尘土味、淡淡的血腥味和草垛的霉味混合成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强势地充斥着姜小帅的鼻腔,将他包裹。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提醒他刚才那场冲动而又荒诞的交易。
姜小帅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男人后背上尚未处理的鞭痕,隔着两层薄薄的布料,微微凸起、发烫。
每一次车辆的颠簸,都会让男人在睡梦中发出一声含糊的呜咽,环抱着他手臂的力量就更紧一分,仿佛那是他唯一能在惊涛骇浪中抓住的浮木。
车厢里并不安静。
前排几个穿着迷彩服的民工在高声谈论着工地的伙食和包工头的刻薄;斜后方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在低声哼着不成调的摇篮曲;过道另一侧,两个穿着廉价西装、满身烟味的中年男人,正用探究、好奇,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目光,反复打量着后排这对奇特的组合——一个皮肤冷白、干净清瘦、穿着白大褂、气质明显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年轻医生,和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污、高大得像座小山般紧紧缠抱着他的黝黑男人。
那些目光像细小的芒刺,扎在姜小帅**的皮肤上。
他微微侧过脸,避开那些视线,将目光投向窗外流动的黑暗。
三万块。
脑海里这个数字像烧红的烙铁,反复灼烫着他的神经。
那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诊所的备用金和自己的积蓄。
口袋里的钱包此刻轻飘飘的,只剩下几张可怜巴巴的零钞和一张即将面临透支的***。
回到城里,房租、水电、药品采购……现实的窘迫如同车窗外的夜色,沉沉地压了过来。
姜小帅转头看向肩膀上的那颗脑袋,男人的五官很是立体,紧闭的左眼下面有颗小小的泪痣,显得这张脸有些过分精致。
看着这个男人,姜小帅思绪万千。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那双眼睛吗?
那双在绝望麻木中突然燃起一丝微弱光亮、充满了全然的希冀和依赖的眼睛?
那双像被遗弃的、遍体鳞伤的大型犬一样的眼睛?
那一刻,所有理智的权衡都被这纯粹得近乎**的眼神击溃了。
他甚至没想过之后该怎么办。
“唔…” 肩头的男人突然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哼,身体微微抽搐了一下,像是被噩梦惊扰。
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混合着额角伤口渗出的组织液,蹭在姜小帅肩上那件象征着清洁的白大褂上,留下一点湿黏的污迹。
姜小帅的身体瞬间绷紧,下意识地想抽回自己的手臂,但男人的手臂像铁箍一样纹丝不动。
他低头看去。
男人睡得并不安稳,即使在昏暗中,也能看到他紧锁的眉头和微微颤抖的睫毛。
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脖颈蜿蜒而下,流进那件破烂不堪、几乎无法蔽体的衣服里。
就在他环抱着姜小帅手臂的粗壮手腕内侧——那里原本被厚厚的污泥覆盖着——因为汗水和挤压,污泥剥落了一小块,露出了下面卡在皮肉中的异物边缘。
一小块尖锐的、金属材质的碎片。
边缘在窗外偶尔掠过的车灯映照下,反射出一点冷硬的光。
姜小帅的心脏猛地一跳!
他想看得更清楚些,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自由的手,他白皙修长的手指极其轻柔地拨开男人手腕上更多的污泥。
动作很轻,但沉睡中的男人似乎感受到了触碰,喉间发出一声类似野兽护食般低沉的咕噜声,环抱的手臂骤然收紧!
巨大的力量勒得姜小帅手臂一麻,差点叫出声。
他连忙停止了动作,紧张地观察着男人的反应。
好在男人只是咕哝了一声,眉头皱得更紧,并没有醒来。
借着又一次掠过的车灯光芒,姜小帅屏住呼吸,终于看清了那碎片隐藏的部分——一个极其微小的、线条精细流畅的徽记。
虽然破碎且被污泥包裹了大半,但那展翅欲飞的鹰隼轮廓,以及徽记边缘精密独特的雕花纹理,瞬间击中了他!
那绝非普通表盘或者廉价金属饰品能拥有的工艺!
百达翡丽!
这个奢侈到近乎传奇的品牌标识,像一道冰冷的电流窜过姜小帅的脊椎!
他绝不会认错!
父亲曾收到过的一份贵重礼物,就是一块百达翡丽,他小时候见过很多次,上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
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被当成牲口使唤、话都说不清的“傻子”?
手腕上竟然卡着百达翡丽表盘的碎片?
这巨大的反差如同一个冰冷的拳头,狠狠砸在姜小帅混乱的思绪上。
车祸断崖、失去牌照的工程车、诡异的刹车失灵、三个月前城市里郭氏集团年轻总裁的离奇失踪案报道碎片……这些原本毫不相关的信息点,此刻因为这枚破碎的徽记,在他脑海中疯狂碰撞!
他猛地转头,看向靠在自己肩上沉睡的男人。
污垢、伤痕、乱发掩盖了大部分面容,但那份优越的骨相轮廓却越发清晰。
高挺的鼻梁,深刻的眉骨,眼角那颗精致的泪痣,即使在沉睡中也带着一股难以磨灭的、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贵气。
难道……这个被他三万块“买”回来、像雏鸟般依赖着他的“傻子”,竟然是那个三个月前轰动全城、在盘龙岭车祸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甚至被怀疑己经死亡的商界新贵——郭城宇?!
这个念头如同平地惊雷,在姜小帅脑海里轰然炸开!
巨大的震惊和随之而来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冲向了头顶,又猛地回流,手脚冰凉。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想要推开这个男人,却发现自己瘦削的身体在对方沉重的压制下,根本动弹不得!
他带走的不是麻烦,他带回的……可能是一个足以将他卷入灭顶之灾的巨大旋涡!
一个牵扯着巨大财富、复杂阴谋、甚至可能是**的**证据!
一旦这个猜测成真,那些制造了“意外”的人,绝不会放过他,更不会放过这个唯一的幸存者!
大巴依旧在摇晃前行,驶向灯火渐明的城市边缘。
车厢里的喧嚣似乎都离姜小帅远去了,只剩下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和肩上男人沉重而温热的呼吸。
他低头,看着男人紧紧攥着自己雪白衣角的手指——粗糙、宽大、指节突出,布满了伤痕,黝黑的手指与洁白的布料形成了悚然的对比。
那份全然的、毫无保留的依赖,此刻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惊肉跳。
归途的尽头,不再是熟悉的诊所和清贫但安稳的生活。
前方等待他的,是深不见底的未知黑暗和足以吞噬一切的惊涛骇浪。
他该怎么办?
精彩片段
都市小说《我曾捡到一轮月》,讲述主角姜小帅张金魁的爱恨纠葛,作者“爱吃盐叶子牛肉的戴虎”倾心编著中,本站纯净无广告,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暮色西合,如黏稠的墨汁泼洒在盘龙岭待开发的荒地上空。狂风不再是风,而是淬了毒的冰冷匕首,裹挟着碎石和砂砾,疯狂抽打着断崖边缘那辆孤零零的黑色路虎揽胜。车内,郭城宇骨节分明的手紧握着方向盘,手背因用力而青筋凸显,深邃锐利的眼眸紧盯着前方被夜色吞噬的险峻弯道。副驾上的助理陈锋脸色煞白,急促的呼吸在封闭空间里格外清晰。“郭总,前面是鬼见愁弯!雨太大了,能见度……” 李旺的提醒被一阵尖锐刺耳的金属撕裂声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