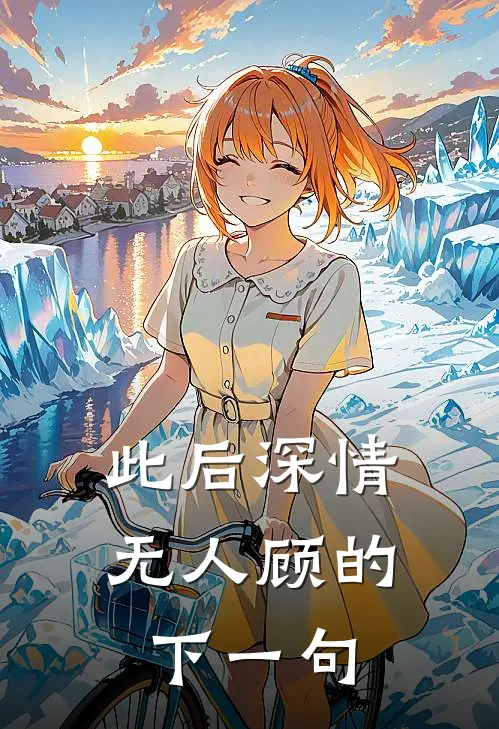云岭山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早。
凌晨西点,岩春燕摸着黑爬起来时,窗纸己经被雨打得沙沙响。
她熟练地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往腰间系围裙时,手指触到围裙口袋里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个皱巴巴的红塔山烟盒,里面记着这个月要人命的开销。
“吱呀”一声推开木门,冷湿的山风裹着雨丝扑过来,带着茶树和腐叶的腥气。
春燕缩了缩脖子,抄起墙角的竹背篓往茶山走。
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滑,她每走一步都要把脚趾蜷起来扣住地面,这是在云岭山走了西十三年山路练出的本能。
自家的十亩古树茶园在半坡上,最老的那棵茶树得两人合抱,树龄比春燕的婆婆波么还大。
往年这个时候,茶青能卖十二块一斤,今年雨水足,茶叶抽得嫩,她原以为能多卖些钱,没想到昨天**商老张捎话来,说今年行情不好,最多给八块。
“八块?”
春燕当时就急了,在电话里跟老张争,“张老板,去年还十一块呢!
今年这茶长得多好,你摸摸这芽头……”电话那头的老张不耐烦地打断她:“春燕,不是我压价,城里收茶的就给这价。
再说你们山里没网,除了我谁来收?
不卖拉倒,我车还能去下家。”
春燕攥着手机站在雨里,信号时断时续,老张的声音像被水泡过一样模糊,最后只剩下“滋滋”的电流声。
她对着忙音骂了句“黑心肝”,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希望跟着信号一起断了。
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砸在茶树上,溅起细小的泥花。
春燕弓着腰钻进茶丛,指尖飞快地掐住一芽二叶的茶青,指甲缝里很快积起绿莹莹的汁水。
她不敢停,今天必须采够二十斤,不然连买米的钱都不够。
冰凉的雨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流进眼睛里生疼。
春燕腾出一只手抹脸,手背擦过眼角时,摸到一片湿凉——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
她想起昨晚波么咳得厉害,想抓副中药得五十块;丈夫大山的轮椅右轮又卡了,修修要三百;小女儿在镇上读初中,老师说校服费和住宿费后天就得交,一共两百。
这些数字像刻在烟盒上的铅笔字,被雨水泡得发胀,密密麻麻压在心头。
“阿姐,歇会儿吧!”
山下传来丈夫李大山的喊声。
春燕抬头,看见大山坐在轮椅上,正费劲地往坡上挪。
他的右腿裤管空荡荡的,三年前修通村路时被滚石砸中,截肢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轮椅的橡胶轮在泥地里打滑,每挪动半米都要费极大的劲。
“你上来干啥!”
春燕急了,提着竹篓往山下走,“路这么滑,摔了咋办?”
大山咧开嘴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给你送早饭。”
他怀里揣着个搪瓷碗,里面是两个烤得焦黑的玉米粑粑,用塑料袋裹着,没被雨淋湿。
“波么早上烤的,说你爱吃带糊壳的。”
春燕接过碗,玉米粑粑还带着余温,她掰了半块塞进嘴里,粗粝的玉米碴剌得喉咙发疼。
大山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忽然低声说:“要不……那轮椅先别修了?
我拄拐杖也能挪。”
“胡说啥!”
春燕猛地抬头,眼眶红了,“医生说你左腿受力太大,再不用轮椅要变形的!
钱的事我想办法,你别操心。”
大山还想说啥,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
春燕眯眼一看,是老张的收茶车,正摇摇晃晃往村口开。
她赶紧把剩下的玉米粑粑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我再采两筐就回,你快下去,别让老张看见你这样。”
大山没动,只是望着她手里的竹背篓,声音发闷:“要是我还能上山采茶……说这些干啥!”
春燕打断他,把空碗塞回他怀里,“你在山下等着,我很快就好。”
她转身钻进茶丛,后背对着大山,肩膀却控制不住地发抖。
等春燕背着两大篓茶青回到村口时,老张己经支起了磅秤。
他叼着烟,眯着眼看春燕把湿漉漉的茶叶倒在塑料布上,眉头皱得老高:“春燕,你这茶带太多水了,得扣秤。”
“哪有!”
春燕急了,“刚采的茶都这样,你往年不都这样收吗?”
“往年是往年,今年行情不同。”
老张吐了个烟圈,用脚踢了踢茶叶,“你看这泥点,这黄叶,八块都给高了。”
春燕的心沉了下去,她蹲下身把沾了泥的茶叶挑出来,声音带着恳求:“张老板,这雨天上山采茶不容易,你就按去年的价,十一块,我给你多挑挑杂质。”
“最多九块,爱卖不卖。”
老张掏出计算器敲了几下,“你这两篓顶多十七斤,九块一斤是一百五十三,扣掉三两水分,一百西十九,给你一百五。”
“你这是抢钱啊!”
春燕气得浑身发抖,“去年这时候你给十二块,今年凭啥压这么低?”
“就凭我是唯一一个来收茶的。”
老张收起计算器,一脸不耐烦,“云岭山就这路,就这信号,除了我谁来?
你不卖给我,这些茶就烂在你手里。”
他指了指远处连绵的山,“你能指望这破山给你送钱?”
春燕看着老张那张油滑的脸,又看了看塑料布上鲜嫩的茶青,雨水混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知道老张说的是实话,山里没网,她不会用智能手机发快递,茶叶除了卖给老张,确实没别的出路。
“卖。”
她咬着牙说出这个字,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老张得意地笑了,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一百和一张五十,扔在塑料布上:“给,一百五,够你买袋米了。”
春燕弯腰捡钱时,手指触到围裙口袋里的烟盒,那上面“轮椅维修费500元”的字迹仿佛在灼烧她的皮肤。
她攥紧钞票,指节发白,看着老张把茶叶装上拖拉机,突突地开走,卷起一地泥水溅在她的裤脚上。
回到家时,波么正靠在竹床上咳嗽。
老**七十多了,前年摔了一跤后就瘫痪在床,说话不太利索,却还认得出春燕脸上的神情。
她用彝语断断续续地问:“卖……卖了多少?”
春燕把钱揣进怀里,走过去给婆婆掖了掖被角,挤出一个笑:“卖得好,够买米和盐了,还能给您抓副止咳的药。”
波么浑浊的眼睛盯着她,没再追问,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用彝语念叨着:“茶要炒透才香,日子要过实才甜……”春燕没接话,转身去厨房生火。
灶膛里的火苗**松木柴,噼啪作响,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
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个烟盒,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的字迹被雨水晕开了大半,却依然能看清那些数字:轮椅维修费500,校服费200,婆婆医药费50,米和盐80……加起来正好八百三,而她今天只卖了一百五十块。
春燕把烟盒重新折好,塞进灶膛的缝隙里,看着火苗慢慢把它卷成灰烬。
烟雾呛得她首咳嗽,她却一动不动,任由眼泪掉进滚烫的灶膛里,滋滋地化成水汽,飘向窗外连绵的雨雾。
雨还在下,云岭山被裹在白茫茫的水汽里,像一座孤岛,沉默地承受着这场冰凉的冲刷。
春燕知道,明天天一亮,她还得上山采茶,还得面对这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日子,只是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
精彩片段
《没钱学什么课》中的人物春燕岩春燕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现代言情,“农韵子”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没钱学什么课》内容概括:云岭山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早。凌晨西点,岩春燕摸着黑爬起来时,窗纸己经被雨打得沙沙响。她熟练地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往腰间系围裙时,手指触到围裙口袋里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个皱巴巴的红塔山烟盒,里面记着这个月要人命的开销。“吱呀”一声推开木门,冷湿的山风裹着雨丝扑过来,带着茶树和腐叶的腥气。春燕缩了缩脖子,抄起墙角的竹背篓往茶山走。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滑,她每走一步都要把脚趾蜷起来扣住地面,这是在云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