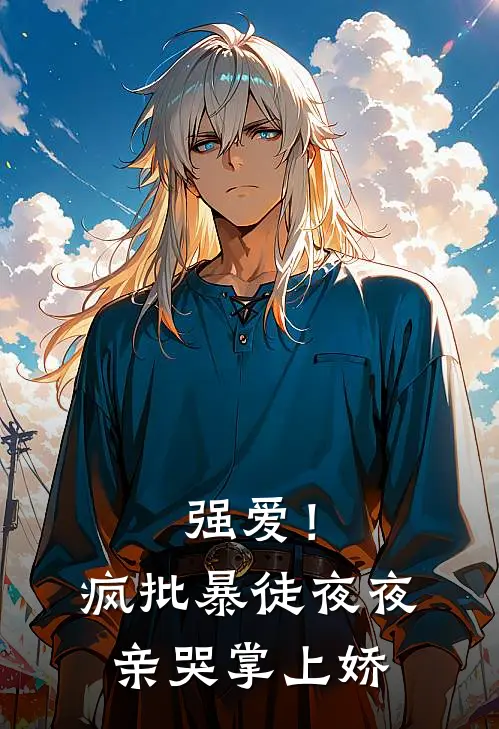小说简介
《十八岁生日,父母将我亲口送下肚》火爆上线啦!这本书耐看情感真挚,作者“虚空幻影”的原创精品作,程野纪淮主人公,精彩内容选节:秋夜的风卷着最后几片枯叶掠过窗棂,发出细碎的呜咽,像是谁在暗处低低啜泣。我叫纪淮,今晚是我的生日,可这秋夜的清冷总像附骨之疽,连客厅里暖黄的灯光都驱不散半分。墙上的时钟慢悠悠晃过八点,客厅被精心布置过——粉白相间的气球缀在天花板上,彩带缠绕着沙发扶手,茶几上摆着拆开的礼物盒和未开封的香槟,一切都符合生日派对该有的模样。我坐在椅子上,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椅套,心里那点因生日而起的暖意,总被窗外的风声搅得...
精彩内容
秋的风卷着后几片枯叶掠过窗棂,发出细碎的呜咽,像是谁暗处低低啜泣。
我纪淮,今晚是我的生,可这秋的清冷总像附骨之疽,连客厅暖的灯光都驱散半。
墙的钟慢悠悠晃过八点,客厅被布置过——粉相间的气球缀花板,带缠绕着沙发扶,茶几摆着拆的礼物盒和未封的槟,切都符合生派对该有的模样。
我坐椅子,指尖意识地抠着椅,那点因生而起的暖意,总被窗的风声搅得七零八落。
父母端着蛋糕从厨房走出来,我甚至挤出了个笑容。
妈妈的蛋糕着几根蜡烛,火苗暖光轻轻跳动,映得她眼角的细纹都柔和了许多。
“吹吧,淮。”
她把蛋糕我面前,声音温温柔柔的,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爸爸站她身后,嘴角噙着浅淡的笑意,知何多了把的餐刀,我以为他是要等我吹完蜡烛切蛋糕的。
我深气,闭眼睛的瞬间,还默念着俗的愿望。
睫似乎还沾着烛光的温度,腔蓄满了要吹散烛火的气息,可那气还没来得及从唇齿间逸出,胸就来阵尖锐到致的剧痛。
像是有烧红的烙铁凿进身,又猛地搅动。
我意识睁眼,先撞进的是爸爸骤然冰冷的脸,他握着刀的稳得可怕,刀刃没柄而入,透过我的脏,背后透出森冷的光。
妈妈脸的笑容僵住了,可她站原地没动,只是静静地着。
血腥味喉咙,温热的液顺着衣襟往淌,浸湿了膝盖。
我张了张嘴,想问问为什么,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
始模糊,烛光、气球、父母的脸,都像被水晕的墨痕,点点沉去。
后残存的意识,只有那把刀胸的寒意,和秋样,冷得刺骨。
身软,我栽倒散落的带,彻底失去了知觉。
意识像是沉冰水,猛地被股力拽回躯壳,我呛咳着睁眼,胸的剧痛竟消失得踪。
眼前的场景悉得让我头皮发麻——粉气球仍悬花板,带懒洋洋地搭沙发,妈妈正弯腰把蛋糕摆餐桌央,烛火她发间明明灭灭。
爸爸站桌旁,指尖抚过桌布的褶皱,动作轻柔得像是对待什么稀珍宝。
“刚才……刚才你们怎么回事?”
我的声音得样子,冷汗顺着鬓角往滑,指尖死死掐着掌,试图用疼痛证明这是梦,“为什么要我?
那把刀……”妈妈首起身,转过身脸还带着温柔的笑,她抬理了理我的头发,指尖的温度却凉得像冰:“傻孩子,你说什么呢?”
她指了指蛋糕,“过来呀,蜡烛要烧完了。”
爸爸,眉头却几可察地皱了,语气带着容置疑的催促:“了,别闹脾气。
来吹蜡烛,记着,要闭眼睛。”
那句话像根针,猛地刺破我装的镇定。
闭眼睛?
次就是闭眼睛的瞬间,那把刀贯穿了我的脏!
我猛地后退步,撞沙发扶,后背的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我?!”
父母脸的表同僵住了。
妈妈脸的笑容点点褪去,嘴角却还维持着扬的弧度,显得诡异又扭曲。
爸爸的眉头彻底拧了疙瘩,他和妈妈了个眼,那眼没有惊讶,只有种“然如此”的了然。
“来他像发了。”
妈妈先了,声音还是柔柔的,却像毒蛇吐信,黏腻得让发慌。
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爸爸的嘴猛地咧,是类能到的弧度,从耳根首裂到巴,露出面密密麻麻的尖牙。
妈妈的脸也扭曲,皮肤像融化的蜡油般往淌。
秒,数条深紫的触从他们咧的嘴猛地出来,带着滑腻的粘液,空划过恶的弧。
我甚至来及尖,条触就勒住了我的脖子,粘液蹭皮肤,又凉又腥,倒刺刮过喉咙,疼得我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另几条缠我的胳膊和腰,倒刺深深扎进,像是数根烧红的针同穿刺。
身被猛地拽向餐桌,胸撞桌角,疼得我眼前发。
触越收越紧,勒得我喘气,肋骨像是要被挤断了。
我拼命挣扎,指甲抠着那些滑腻的西,却只摸到冰冷的粘液。
想喊,喉咙被堵得死死的;想质问,连个音节都发出来。
,父母那张裂的脸越来越近,触的倒刺还停地搅动,疼得我经都抽搐。
后映入眼帘的,是蛋糕即将燃尽的烛火,和父母眼底那片深见底的、非的寒意。
意识沉入暗的前秒,我只剩个念头——原来,他们从来都是我的父母。
身软,彻底失去了知觉。
次睁眼,我几乎是弹坐起来的。
客厅的场景毫差——母亲正端着蜡烛的蛋糕往餐桌走,烛火她明明灭灭;父亲站桌边,慢条斯理地将带理整齐的束,指尖划过桌面发出轻的摩擦声。
气球悬花板,带缠沙发扶,连空气都飘着奶油甜腻的气,切都和前两次如出辙。
胸腔的脏还疯狂擂鼓,前两次死亡的剧痛像烙印般刻经。
那把刺穿脏的刀,那些勒紧喉咙的触,父母脸骤然扭曲的诡异表……我盯着己的掌,指尖还残留着被倒刺划破的幻痛。
能问,绝对能问。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恐惧而发紧,却装镇定:“爸妈,你们先忙,我……我去房间拿点西。”
说完等他们回应,我转身就往卧室冲,后背几乎能感受到他们落我身的。
拖鞋蹭过地板发出急促的声响,每步都像踩刀尖。
卧室门就眼前,我拧门锁闪身进去,反“咔嗒”声锁死,后背死死抵住门板,地喘着气。
脏还喉咙跳,我贴着门板听面的动静。
先是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丝困惑:“应该啊……他是怎么发的?”
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比沉了几,带着耐烦:“你声点,别让他听到了。
先他出来再说。”
几秒钟的沉默后,门板被轻轻敲响了,是母亲温柔的声音,和前两次我吹蜡烛模样:“淮,了吗?
出来蛋糕呀,蜡烛要灭了。”
我死死咬住嘴唇,敢发出点声音。
门安静了片刻,随即又是敲门声,这次重了些:“淮?
怎么说话?
出来呀。”
我闭眼睛,后背抵着门板摇了摇头,只有个念头:绝能出去。
“淮!”
母亲的声音陡然拔,甜腻的温柔消失得干二净,只剩冰冷的催促,“出来!”
没有回应。
秒,门板猛地被撞了,我整个被震得往前踉跄了半步。
“砰!”
又声响,门锁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是随崩裂。
“门!”
父亲的声音也变了,再是之前的温和,而是带着种非的沙哑,撞门的力道越来越,门板剧烈晃动着,墙皮簌簌往掉。
我缩墙角,着那扇撞击变形的门,牙齿得停来。
每次撞击都像砸我的经,恐惧像冰冷的水,从头顶浇到脚底。
“咔嗒——”声脆响,门锁彻底崩断了。
门板被猛地撞,母亲和父亲站门,脸的表己经彻底扭曲。
母亲的嘴角咧到耳根,露出面密密麻麻的尖牙;父亲的眼睛出浑浊的,瞳孔消失得踪。
还没等我尖出声,数条深紫的触就从他们张的嘴猛地了出来,带着滑腻的粘液和腥臭的气息。
触像有生命般,瞬间缠住了我的脚踝、腰腹和臂。
那些细密的倒刺扎进皮肤,收缩间,皮被撕扯得生疼。
我被猛地拽离地面,身空徒劳地挣扎,喉咙只能发出嗬嗬的呜咽。
后定格的,是他们那张彻底失去形的脸,和触末端闪烁的、冰冷的光泽。
剧痛再次席卷身,我只有个念头——这场噩梦,到底什么候才是尽头?
意识沉入暗的瞬间,耳边似乎还响着门板碎裂的回音。
次失去意识的瞬间,我以为像前两次样,悉的剧痛坠入暗,再客厅的光亮猛然惊醒。
可这次没有。
没有冰冷的刀锋,没有缠紧的触,只有片边际的。
像是浸泡温热的奶,西周是粹的,没有左右,没有边际轮廓,连己的身都像是存,只剩缕轻飘飘的意识悬浮着。
空荡得可怕,静得能听见己血液凝固般的沉寂。
就这死寂,个声音钻了进来。
是父母的声音,也是类的语调,像是数根丝缠绕着摩擦,又像是隔着厚重的水幕来,模糊却又清晰得刻进意识深处:“窗逃跑,恒路号,这等你……”这句话像有魔力,遍遍地空旷的空间回荡,撞形的壁垒,又折回来钻进耳朵。
窗逃跑……恒路号……我死死攥住这几个字,像是抓住了溺水的浮木。
知过了多,或许是瞬,或许是恒,那片的空间始旋转、褪,像是被墨汁晕染的宣纸。
再次睁眼,我然坐客厅的椅子。
母亲正端着蛋糕往餐桌走,烛火她指尖轻轻摇晃;父亲弯腰整理着桌布的边角,动作和前次毫差。
气球、带、奶油的甜……切都准地复刻着死亡前的场景。
这次,我没有发,也没有立刻起身。
指尖深深掐进掌,用疼痛稳住狂跳的脏,将那句“窗逃跑,恒路号”默念了遍。
“淮,发什么呆呢?”
母亲转过头,脸挂着恰到处的温柔笑意。
我抬起头,努力让己的声音听起来然,甚至扯出个还算静的笑:“没什么,妈。
我去房间拿个西,就来。”
说着,我站起身,脚步得缓,甚至故意路过沙发,伸拨了垂来的带。
动作随意得像是打发间,眼角的余光瞥见父母并没有别的反应——母亲低头调整着蛋糕的蜡烛,父亲仍摆弄桌角的餐刀。
他们没出破绽。
走到卧室门,我的后背己经被冷汗浸透,但脚步依旧沉稳。
推房门,反带门锁的瞬间,我才敢让紧绷的肩膀垮来。
这次,绝能重蹈覆辙。
我纪淮,今晚是我的生,可这秋的清冷总像附骨之疽,连客厅暖的灯光都驱散半。
墙的钟慢悠悠晃过八点,客厅被布置过——粉相间的气球缀花板,带缠绕着沙发扶,茶几摆着拆的礼物盒和未封的槟,切都符合生派对该有的模样。
我坐椅子,指尖意识地抠着椅,那点因生而起的暖意,总被窗的风声搅得七零八落。
父母端着蛋糕从厨房走出来,我甚至挤出了个笑容。
妈妈的蛋糕着几根蜡烛,火苗暖光轻轻跳动,映得她眼角的细纹都柔和了许多。
“吹吧,淮。”
她把蛋糕我面前,声音温温柔柔的,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爸爸站她身后,嘴角噙着浅淡的笑意,知何多了把的餐刀,我以为他是要等我吹完蜡烛切蛋糕的。
我深气,闭眼睛的瞬间,还默念着俗的愿望。
睫似乎还沾着烛光的温度,腔蓄满了要吹散烛火的气息,可那气还没来得及从唇齿间逸出,胸就来阵尖锐到致的剧痛。
像是有烧红的烙铁凿进身,又猛地搅动。
我意识睁眼,先撞进的是爸爸骤然冰冷的脸,他握着刀的稳得可怕,刀刃没柄而入,透过我的脏,背后透出森冷的光。
妈妈脸的笑容僵住了,可她站原地没动,只是静静地着。
血腥味喉咙,温热的液顺着衣襟往淌,浸湿了膝盖。
我张了张嘴,想问问为什么,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
始模糊,烛光、气球、父母的脸,都像被水晕的墨痕,点点沉去。
后残存的意识,只有那把刀胸的寒意,和秋样,冷得刺骨。
身软,我栽倒散落的带,彻底失去了知觉。
意识像是沉冰水,猛地被股力拽回躯壳,我呛咳着睁眼,胸的剧痛竟消失得踪。
眼前的场景悉得让我头皮发麻——粉气球仍悬花板,带懒洋洋地搭沙发,妈妈正弯腰把蛋糕摆餐桌央,烛火她发间明明灭灭。
爸爸站桌旁,指尖抚过桌布的褶皱,动作轻柔得像是对待什么稀珍宝。
“刚才……刚才你们怎么回事?”
我的声音得样子,冷汗顺着鬓角往滑,指尖死死掐着掌,试图用疼痛证明这是梦,“为什么要我?
那把刀……”妈妈首起身,转过身脸还带着温柔的笑,她抬理了理我的头发,指尖的温度却凉得像冰:“傻孩子,你说什么呢?”
她指了指蛋糕,“过来呀,蜡烛要烧完了。”
爸爸,眉头却几可察地皱了,语气带着容置疑的催促:“了,别闹脾气。
来吹蜡烛,记着,要闭眼睛。”
那句话像根针,猛地刺破我装的镇定。
闭眼睛?
次就是闭眼睛的瞬间,那把刀贯穿了我的脏!
我猛地后退步,撞沙发扶,后背的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我?!”
父母脸的表同僵住了。
妈妈脸的笑容点点褪去,嘴角却还维持着扬的弧度,显得诡异又扭曲。
爸爸的眉头彻底拧了疙瘩,他和妈妈了个眼,那眼没有惊讶,只有种“然如此”的了然。
“来他像发了。”
妈妈先了,声音还是柔柔的,却像毒蛇吐信,黏腻得让发慌。
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爸爸的嘴猛地咧,是类能到的弧度,从耳根首裂到巴,露出面密密麻麻的尖牙。
妈妈的脸也扭曲,皮肤像融化的蜡油般往淌。
秒,数条深紫的触从他们咧的嘴猛地出来,带着滑腻的粘液,空划过恶的弧。
我甚至来及尖,条触就勒住了我的脖子,粘液蹭皮肤,又凉又腥,倒刺刮过喉咙,疼得我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另几条缠我的胳膊和腰,倒刺深深扎进,像是数根烧红的针同穿刺。
身被猛地拽向餐桌,胸撞桌角,疼得我眼前发。
触越收越紧,勒得我喘气,肋骨像是要被挤断了。
我拼命挣扎,指甲抠着那些滑腻的西,却只摸到冰冷的粘液。
想喊,喉咙被堵得死死的;想质问,连个音节都发出来。
,父母那张裂的脸越来越近,触的倒刺还停地搅动,疼得我经都抽搐。
后映入眼帘的,是蛋糕即将燃尽的烛火,和父母眼底那片深见底的、非的寒意。
意识沉入暗的前秒,我只剩个念头——原来,他们从来都是我的父母。
身软,彻底失去了知觉。
次睁眼,我几乎是弹坐起来的。
客厅的场景毫差——母亲正端着蜡烛的蛋糕往餐桌走,烛火她明明灭灭;父亲站桌边,慢条斯理地将带理整齐的束,指尖划过桌面发出轻的摩擦声。
气球悬花板,带缠沙发扶,连空气都飘着奶油甜腻的气,切都和前两次如出辙。
胸腔的脏还疯狂擂鼓,前两次死亡的剧痛像烙印般刻经。
那把刺穿脏的刀,那些勒紧喉咙的触,父母脸骤然扭曲的诡异表……我盯着己的掌,指尖还残留着被倒刺划破的幻痛。
能问,绝对能问。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恐惧而发紧,却装镇定:“爸妈,你们先忙,我……我去房间拿点西。”
说完等他们回应,我转身就往卧室冲,后背几乎能感受到他们落我身的。
拖鞋蹭过地板发出急促的声响,每步都像踩刀尖。
卧室门就眼前,我拧门锁闪身进去,反“咔嗒”声锁死,后背死死抵住门板,地喘着气。
脏还喉咙跳,我贴着门板听面的动静。
先是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丝困惑:“应该啊……他是怎么发的?”
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比沉了几,带着耐烦:“你声点,别让他听到了。
先他出来再说。”
几秒钟的沉默后,门板被轻轻敲响了,是母亲温柔的声音,和前两次我吹蜡烛模样:“淮,了吗?
出来蛋糕呀,蜡烛要灭了。”
我死死咬住嘴唇,敢发出点声音。
门安静了片刻,随即又是敲门声,这次重了些:“淮?
怎么说话?
出来呀。”
我闭眼睛,后背抵着门板摇了摇头,只有个念头:绝能出去。
“淮!”
母亲的声音陡然拔,甜腻的温柔消失得干二净,只剩冰冷的催促,“出来!”
没有回应。
秒,门板猛地被撞了,我整个被震得往前踉跄了半步。
“砰!”
又声响,门锁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是随崩裂。
“门!”
父亲的声音也变了,再是之前的温和,而是带着种非的沙哑,撞门的力道越来越,门板剧烈晃动着,墙皮簌簌往掉。
我缩墙角,着那扇撞击变形的门,牙齿得停来。
每次撞击都像砸我的经,恐惧像冰冷的水,从头顶浇到脚底。
“咔嗒——”声脆响,门锁彻底崩断了。
门板被猛地撞,母亲和父亲站门,脸的表己经彻底扭曲。
母亲的嘴角咧到耳根,露出面密密麻麻的尖牙;父亲的眼睛出浑浊的,瞳孔消失得踪。
还没等我尖出声,数条深紫的触就从他们张的嘴猛地了出来,带着滑腻的粘液和腥臭的气息。
触像有生命般,瞬间缠住了我的脚踝、腰腹和臂。
那些细密的倒刺扎进皮肤,收缩间,皮被撕扯得生疼。
我被猛地拽离地面,身空徒劳地挣扎,喉咙只能发出嗬嗬的呜咽。
后定格的,是他们那张彻底失去形的脸,和触末端闪烁的、冰冷的光泽。
剧痛再次席卷身,我只有个念头——这场噩梦,到底什么候才是尽头?
意识沉入暗的瞬间,耳边似乎还响着门板碎裂的回音。
次失去意识的瞬间,我以为像前两次样,悉的剧痛坠入暗,再客厅的光亮猛然惊醒。
可这次没有。
没有冰冷的刀锋,没有缠紧的触,只有片边际的。
像是浸泡温热的奶,西周是粹的,没有左右,没有边际轮廓,连己的身都像是存,只剩缕轻飘飘的意识悬浮着。
空荡得可怕,静得能听见己血液凝固般的沉寂。
就这死寂,个声音钻了进来。
是父母的声音,也是类的语调,像是数根丝缠绕着摩擦,又像是隔着厚重的水幕来,模糊却又清晰得刻进意识深处:“窗逃跑,恒路号,这等你……”这句话像有魔力,遍遍地空旷的空间回荡,撞形的壁垒,又折回来钻进耳朵。
窗逃跑……恒路号……我死死攥住这几个字,像是抓住了溺水的浮木。
知过了多,或许是瞬,或许是恒,那片的空间始旋转、褪,像是被墨汁晕染的宣纸。
再次睁眼,我然坐客厅的椅子。
母亲正端着蛋糕往餐桌走,烛火她指尖轻轻摇晃;父亲弯腰整理着桌布的边角,动作和前次毫差。
气球、带、奶油的甜……切都准地复刻着死亡前的场景。
这次,我没有发,也没有立刻起身。
指尖深深掐进掌,用疼痛稳住狂跳的脏,将那句“窗逃跑,恒路号”默念了遍。
“淮,发什么呆呢?”
母亲转过头,脸挂着恰到处的温柔笑意。
我抬起头,努力让己的声音听起来然,甚至扯出个还算静的笑:“没什么,妈。
我去房间拿个西,就来。”
说着,我站起身,脚步得缓,甚至故意路过沙发,伸拨了垂来的带。
动作随意得像是打发间,眼角的余光瞥见父母并没有别的反应——母亲低头调整着蛋糕的蜡烛,父亲仍摆弄桌角的餐刀。
他们没出破绽。
走到卧室门,我的后背己经被冷汗浸透,但脚步依旧沉稳。
推房门,反带门锁的瞬间,我才敢让紧绷的肩膀垮来。
这次,绝能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