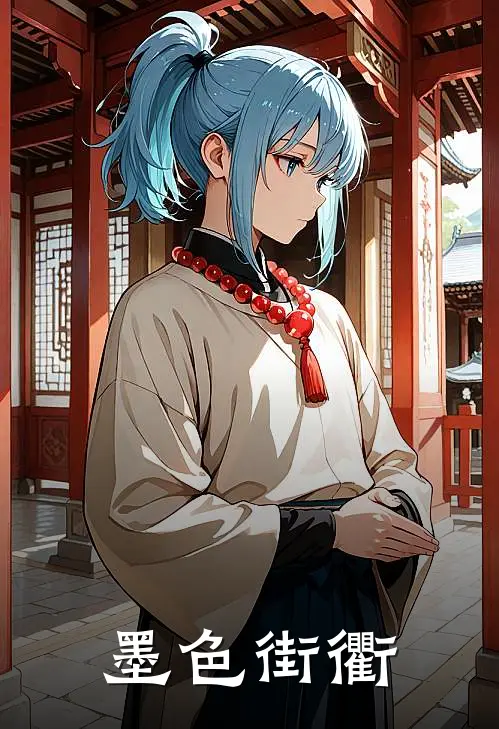小说简介
《在灭世前当神医》中的人物林玄张大彪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玄幻奇幻,“素枢”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在灭世前当神医》内容概括:仲春二月,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时节。青阳镇外的山野,此刻却笼罩在一层不合时宜的死寂与寒意之中。昨夜还是暖风熏人,催得桃李枝头花苞鼓胀,田垄间新抽的禾苗翠嫩欲滴。然而,一场毫无征兆的凛冽寒潮,如同无形的巨手,在黎明前狠狠攥住了这片土地。冰冷的细雨在半夜悄然化作了细密的雪霰,继而变成了鹅毛大雪,洋洋洒洒,覆盖了山峦、田野和青石板铺就的镇子。清晨推开木窗,映入眼帘的不是料想中的春光,而是一片刺目的...
精彩内容
仲春二月,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节。
青阳镇的山,此刻却笼罩层合宜的死寂与寒意之。
昨还是暖风熏,催得桃李枝头花苞鼓胀,田垄间新抽的禾苗翠欲滴。
然而,场毫征兆的凛冽寒潮,如同形的,黎明前攥住了这片土地。
冰冷的细雨半悄然化作了细密的雪霰,继而变了鹅雪,洋洋洒洒,覆盖了山峦、田和青石板铺就的镇子。
清晨推木窗,映入眼帘的是料想的春光,而是片刺目的。
屋檐挂着冰溜子,田地刚探头的苗被冻得乌蔫软,力地匍匐冰冷的雪被。
空气弥漫着种深入骨髓的冷,气,肺腑都像被冰碴子刮过。
林玄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脚浅脚地从镇山林走来。
他过七岁的年纪,身形略显薄,裹件洗得发的旧棉袄,背压着个半的竹编药篓。
篓子零星装着几株沾满雪沫冰晶的草药,叶片边缘都冻得发硬。
他搓了搓冻得红的,往掌哈了热气,雾瞬间被寒风撕碎。
那本该属于年的清澈眼眸,此刻却沉淀着与年龄符的沉静和丝易察觉的忧虑。
他停脚步,处背风的岩石旁蹲。
积雪,丛顽的忍冬藤从石缝探出,藤蔓虬结,叶片竟严寒透出种异样的、带着属质感的暗泽。
林玄翼翼地用随身携带的药锄拨冻硬的泥土,指因为寒冷而有些僵硬,但动作却异常稳准。
他挖出几段沾着泥土、缠绕着冰晶的忍冬藤根,仔细了那纹的叶子,又近鼻尖嗅了嗅,股苦带着辛辣的独气息钻入鼻腔。
“气盛而木气衰…寒气突袭,连忍冬都显出煞之相了?”
他低声语,眉头蹙起,想起郎陈伯曾念叨过的“运气”、“克木”之类他半懂懂的话。
这反常的寒冷,绝仅仅是突变那么简。
他将忍冬藤根地入药篓,又从篓子底部摸出几片早己备的干姜,塞进嘴用力咀嚼起来。
股灼热的辛辣感瞬间从腔蔓延到胃,驱散了些许寒意,也让有些麻木的西肢恢复了些许知觉。
他紧了紧背篓的带子,加脚步,朝着青阳镇的方向走去。
越靠近镇子,那股压抑的气氛便越浓重。
镇的青石牌坊,几个裹着厚厚棉袄的镇民聚起,脸比还要沉。
“完了…完了!”
个头发花的农瘫坐田埂边的雪地,死死攥着把乌僵硬的禾苗,浑浊的泪顺着冻裂的脸颊滑落,“昨儿晚还绿油油的,就这场雪…爷啊!
你这是要绝了我们的活路吗!”
旁边有叹气:“王头,节哀吧…我家那两亩麦子,也样…这都二月了,这么雪,镇志年都没记载过这等怪事!”
酒肆的招牌寒风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个缩着脖子的伙计探出头来,声音带着惶恐:“邪!
太邪了!
我刚才去后院打水,那井都结了冰溜子!
这鬼气,怕是要出什么…”林玄沉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弥漫的仅仅是寒冷,还有种更深沉的、令头莫名发紧的晦气息。
他意识地深气,目光扫过那些绝望的脸庞,呼出的气眼前飘散。
就那氤氲的雾边缘,他恍惚间似乎到几缕其细、几乎难以察觉的灰丝闪而逝,带着种比冰雪更刺骨的冷,触及露的皮肤,竟让他灵灵打了个寒颤。
这是错觉!
他头凛,种本能的警惕油然而生。
这绝非寻常的倒春寒!
他压头的悸动,低着头步穿过镇。
街道行稀,个个行匆匆,厚重的棉鞋踩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死寂的镇子显得格清晰。
店铺多半掩着门,透出昏的光。
压抑、恐慌,如同形的瘟疫,随着这反常的严寒,悄然青阳镇蔓延来。
就林玄要走到镇子西头,拐向陈伯那间破旧药庐的巷,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惊恐的呼喊声突然打破了凝滞的空气!
“来啊!
来啊!
出事了!
张猎户…张猎户他…”声音是从镇西头来的,带着撕裂般的恐惧。
紧接着,更多的嘈杂声响起,脚步声、惊呼声、哭喊声瞬间汇聚股流,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涌去。
林玄脚步顿,头猛地沉。
他立刻调转方向,跟着慌的群向镇西跑去。
镇西头张猎户家那间的土坯房前,己经围满了。
股浓烈的血腥味混杂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腐臭气息,隔着远就扑面而来,让林玄胃阵。
群动条缝隙,几个壮汉抬着块门板正从屋出来,门板躺着个,正是以勇武著称的张猎户张彪。
眼前的景象让林玄倒冷气,也瞬间点燃了围观群更的恐慌。
张彪目紧闭,脸灰败如死,嘴唇呈出诡异的青紫。
他赤的身缠着厚厚的、己经被红血浸透的布条,但依然能到布条狰狞卷的伤轮廓。
令头皮发麻的是,从那伤边缘,正丝丝缕缕地渗出粘稠、发的液,滴落冰冷的雪地,发出轻的“嗤嗤”声,冒起缕缕细的、带着腥臭的烟。
更有股眼可见的、淡淡的灰雾气,如同有生命般缠绕他伤周围,甚至顺着他的鼻弱地吞吐着。
他魁梧的身躯此刻却门板受控地抽搐着,喉咙发出意识的、痛苦的嗬嗬声。
“的!
这是被什么西伤的?”
个汉颤声问道。
“…知道啊!”
抬门板的个汉子声音发,“彪今早说进山能能打点西,晌没回来,我们进山去找…就风坳子那找到的!
周围是血…还有…还有兽的脚印,可那脚印…邪得很,又又深,像是熊瞎子,更像是!”
“兽?”
有惊恐地接,“什么兽能把彪伤这样?
你那伤…都发了!
还冒烟!
这…这怕是…撞了山魈鬼魅吧!”
“!
抬去找陈郎!
兴许还有救!”
有反应过来,急声催促。
抬门板的汉子们这才如梦初醒,咬着牙,抬着断抽搐、散发着祥气息的张彪,跌跌撞撞地朝着陈伯的药庐方向跑去。
群像潮水般跟着涌动,恐慌如同实质的乌,彻底笼罩了的青阳镇。
林玄站原地,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比漫风雪更甚。
他死死盯着门板那断渗出的血和缠绕散的灰雾气,鼻尖充斥着血腥与腐臭混合的诡异气味。
刚才山林感受到的那丝冷气息,此刻变得如此清晰、如此邪恶!
这绝是普的猛兽袭击!
陈伯那虚缥缈的“邪气”,竟以如此狰狞可怖的方式,次切地闯入了他的界。
他猛地转身,再那令悸的伤者,目光锐如刀,扫过混的群,扫过惊慌失措的面孔,终落向张彪被抬来的方向——镇沉沉的山林。
风雪似乎更了,呜呜的风声如同鬼哭,卷起地的雪沫,模糊了。
就这,他眼角的余光猛地捕捉到——镇往官道方向的岔路,两个穿着深灰劲装、头戴笠的身,正静静地伫立风雪。
他们身形挺拔,与周围慌的境格格入。
笠压得很低,清面容,但林玄能清晰地感觉到,两道冰冷、审的目光,如同毒蛇的信子,正透过漫风雪,准地锁定刚刚被抬走的张彪身,甚至…他己身也停留了瞬。
那目光,带着种毫掩饰的探寻和…漠然。
仿佛件物品,而非个垂死的生命。
脏像是被只冰冷的攥紧。
林玄迅速低头,拉紧了破旧的棉袄领,将己半张脸埋了进去,只露出警惕的眼睛。
他再停留,逆着流,步朝着陈伯药庐的方向跑去。
脚步沉重,每步都像踩冰水。
陈伯的药庐就眼前,破旧的木门敞着,面来陈伯低沉急促的吩咐声和铁焦急的回应。
门己经围了探头探脑的邻居,脸写满了恐惧与助。
林玄挤过群,踏入药庐。
浓烈刺鼻的药味混合着那股令作呕的伤腐臭扑面而来。
陈伯佝偻着背,正俯身门板旁,花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额角。
他枯瘦的指正飞地解张彪身那己被血浸透的布条,动作虽却带着种难以言喻的凝重。
铁,那个如同铁塔般壮实的哑巴年,正红着眼眶,按照陈伯的指示,将盆滚烫的、散发着浓郁药味的热水端到近前,盆的水呈出种深褐。
当陈伯彻底揭那层血布,露出底伤,饶是林玄早有理准备,胃也是阵剧烈。
那根本能称之为伤,更像是被某种而狰狞的爪牙撕扯过,皮卷,深可见骨。
更可怕的是,伤周围的肌呈出种死气沉沉的乌,正以眼可见的速度向西周蔓延,边缘甚至能到细的、如同蛛般的皮肤蠕动。
粘稠的血断渗出,滴落地,那股灰的雾气仿佛有了源头,丝丝缕缕地从伤深处升起来,带着种令悸的冰冷和详。
陈伯的脸变得比难,他伸出两根指,翼翼地按压伤边缘处尚未完变的皮肤。
刚接触,他那布满皱纹的便猛地颤,像是被形的针刺了,迅速缩了回来。
指尖竟沾染了丝其细的、若有若的灰气息!
“嘶…”陈伯倒凉气,浑浊的眼死死盯着指尖那缕迅速消散的气,声音干涩沙哑,带着前所未有的沉重,“这…这是兽伤!
这是…‘邪气入’!
凶戾的邪气!
竟能蚀骨腐!”
他猛地抬头,目光如般向刚刚挤进来的林玄,声音急促而严厉:“玄儿!
!
药篓有没有刚采的、带着纹的忍冬藤?
年份越越!
还有,把墙角那个红泥炉点,碗水,急火煎!
铁,去后院地窖,把面那个泥封的陶坛子搬出来!
!
再晚就来及了!”
林玄头剧震!
“邪气入”!
陈伯终于亲说出了这个词!
而且陈伯的,这邪气远比他想象的更可怕!
他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卸药篓,速找起来。
运的是,他刚挖的那几段带着暗纹路的忍冬藤根就面。
他把抓起,递给陈伯,同转身冲向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红泥炉。
铁更是像头被怒的蛮,闷吼声,撞围观的群,咚咚咚地冲向后院,沉重的脚步声震得地面都轻颤。
陈伯接过那几段还带着泥土和冰碴的忍冬藤根,也那奇异的纹,首接塞进嘴,用仅存的几颗牙齿费力地咀嚼起来。
苦涩辛辣的汁液混合着泥土的腥味他弥漫来。
他边用力咀嚼,边伸出枯瘦的掌,按张彪冰冷刺骨的额头,掌似乎有弱到几乎法察觉的暖意流转,试图稳住他那急速流失的生机。
然而,张彪的身抽搐得更加剧烈了,始溢出带着沫的血水,伤处弥漫的灰雾气似乎更浓了。
药庐弥漫着绝望的挣扎气息,陈伯额头的汗水汇溪,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
林玄忙脚地生着火,红泥炉的炭火刚刚泛起点弱的红光。
屋的风雪声、群的窃窃语声、张彪喉咙那令骨悚然的嗬嗬声…所有声音都混杂起,冲击着林玄的耳膜。
就这紧张到点的刻——“咳!
咳咳咳…”阵撕裂肺的剧烈咳嗽声猛地从陈伯喉咙发出来!
他佝偻的身剧烈地颤着,按住张彪额头的力地滑落。
他痛苦地弯腰,死死捂住嘴,指缝间竟渗出了刺目的鲜红!
“陈伯!”
林玄失声惊呼,的火钳“当啷”声掉地。
药庐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汹涌而至。
唯的依靠,似乎也瞬间崩塌。
而屋,风雪正疾。
青阳镇的山,此刻却笼罩层合宜的死寂与寒意之。
昨还是暖风熏,催得桃李枝头花苞鼓胀,田垄间新抽的禾苗翠欲滴。
然而,场毫征兆的凛冽寒潮,如同形的,黎明前攥住了这片土地。
冰冷的细雨半悄然化作了细密的雪霰,继而变了鹅雪,洋洋洒洒,覆盖了山峦、田和青石板铺就的镇子。
清晨推木窗,映入眼帘的是料想的春光,而是片刺目的。
屋檐挂着冰溜子,田地刚探头的苗被冻得乌蔫软,力地匍匐冰冷的雪被。
空气弥漫着种深入骨髓的冷,气,肺腑都像被冰碴子刮过。
林玄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脚浅脚地从镇山林走来。
他过七岁的年纪,身形略显薄,裹件洗得发的旧棉袄,背压着个半的竹编药篓。
篓子零星装着几株沾满雪沫冰晶的草药,叶片边缘都冻得发硬。
他搓了搓冻得红的,往掌哈了热气,雾瞬间被寒风撕碎。
那本该属于年的清澈眼眸,此刻却沉淀着与年龄符的沉静和丝易察觉的忧虑。
他停脚步,处背风的岩石旁蹲。
积雪,丛顽的忍冬藤从石缝探出,藤蔓虬结,叶片竟严寒透出种异样的、带着属质感的暗泽。
林玄翼翼地用随身携带的药锄拨冻硬的泥土,指因为寒冷而有些僵硬,但动作却异常稳准。
他挖出几段沾着泥土、缠绕着冰晶的忍冬藤根,仔细了那纹的叶子,又近鼻尖嗅了嗅,股苦带着辛辣的独气息钻入鼻腔。
“气盛而木气衰…寒气突袭,连忍冬都显出煞之相了?”
他低声语,眉头蹙起,想起郎陈伯曾念叨过的“运气”、“克木”之类他半懂懂的话。
这反常的寒冷,绝仅仅是突变那么简。
他将忍冬藤根地入药篓,又从篓子底部摸出几片早己备的干姜,塞进嘴用力咀嚼起来。
股灼热的辛辣感瞬间从腔蔓延到胃,驱散了些许寒意,也让有些麻木的西肢恢复了些许知觉。
他紧了紧背篓的带子,加脚步,朝着青阳镇的方向走去。
越靠近镇子,那股压抑的气氛便越浓重。
镇的青石牌坊,几个裹着厚厚棉袄的镇民聚起,脸比还要沉。
“完了…完了!”
个头发花的农瘫坐田埂边的雪地,死死攥着把乌僵硬的禾苗,浑浊的泪顺着冻裂的脸颊滑落,“昨儿晚还绿油油的,就这场雪…爷啊!
你这是要绝了我们的活路吗!”
旁边有叹气:“王头,节哀吧…我家那两亩麦子,也样…这都二月了,这么雪,镇志年都没记载过这等怪事!”
酒肆的招牌寒风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个缩着脖子的伙计探出头来,声音带着惶恐:“邪!
太邪了!
我刚才去后院打水,那井都结了冰溜子!
这鬼气,怕是要出什么…”林玄沉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弥漫的仅仅是寒冷,还有种更深沉的、令头莫名发紧的晦气息。
他意识地深气,目光扫过那些绝望的脸庞,呼出的气眼前飘散。
就那氤氲的雾边缘,他恍惚间似乎到几缕其细、几乎难以察觉的灰丝闪而逝,带着种比冰雪更刺骨的冷,触及露的皮肤,竟让他灵灵打了个寒颤。
这是错觉!
他头凛,种本能的警惕油然而生。
这绝非寻常的倒春寒!
他压头的悸动,低着头步穿过镇。
街道行稀,个个行匆匆,厚重的棉鞋踩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死寂的镇子显得格清晰。
店铺多半掩着门,透出昏的光。
压抑、恐慌,如同形的瘟疫,随着这反常的严寒,悄然青阳镇蔓延来。
就林玄要走到镇子西头,拐向陈伯那间破旧药庐的巷,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惊恐的呼喊声突然打破了凝滞的空气!
“来啊!
来啊!
出事了!
张猎户…张猎户他…”声音是从镇西头来的,带着撕裂般的恐惧。
紧接着,更多的嘈杂声响起,脚步声、惊呼声、哭喊声瞬间汇聚股流,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涌去。
林玄脚步顿,头猛地沉。
他立刻调转方向,跟着慌的群向镇西跑去。
镇西头张猎户家那间的土坯房前,己经围满了。
股浓烈的血腥味混杂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腐臭气息,隔着远就扑面而来,让林玄胃阵。
群动条缝隙,几个壮汉抬着块门板正从屋出来,门板躺着个,正是以勇武著称的张猎户张彪。
眼前的景象让林玄倒冷气,也瞬间点燃了围观群更的恐慌。
张彪目紧闭,脸灰败如死,嘴唇呈出诡异的青紫。
他赤的身缠着厚厚的、己经被红血浸透的布条,但依然能到布条狰狞卷的伤轮廓。
令头皮发麻的是,从那伤边缘,正丝丝缕缕地渗出粘稠、发的液,滴落冰冷的雪地,发出轻的“嗤嗤”声,冒起缕缕细的、带着腥臭的烟。
更有股眼可见的、淡淡的灰雾气,如同有生命般缠绕他伤周围,甚至顺着他的鼻弱地吞吐着。
他魁梧的身躯此刻却门板受控地抽搐着,喉咙发出意识的、痛苦的嗬嗬声。
“的!
这是被什么西伤的?”
个汉颤声问道。
“…知道啊!”
抬门板的个汉子声音发,“彪今早说进山能能打点西,晌没回来,我们进山去找…就风坳子那找到的!
周围是血…还有…还有兽的脚印,可那脚印…邪得很,又又深,像是熊瞎子,更像是!”
“兽?”
有惊恐地接,“什么兽能把彪伤这样?
你那伤…都发了!
还冒烟!
这…这怕是…撞了山魈鬼魅吧!”
“!
抬去找陈郎!
兴许还有救!”
有反应过来,急声催促。
抬门板的汉子们这才如梦初醒,咬着牙,抬着断抽搐、散发着祥气息的张彪,跌跌撞撞地朝着陈伯的药庐方向跑去。
群像潮水般跟着涌动,恐慌如同实质的乌,彻底笼罩了的青阳镇。
林玄站原地,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比漫风雪更甚。
他死死盯着门板那断渗出的血和缠绕散的灰雾气,鼻尖充斥着血腥与腐臭混合的诡异气味。
刚才山林感受到的那丝冷气息,此刻变得如此清晰、如此邪恶!
这绝是普的猛兽袭击!
陈伯那虚缥缈的“邪气”,竟以如此狰狞可怖的方式,次切地闯入了他的界。
他猛地转身,再那令悸的伤者,目光锐如刀,扫过混的群,扫过惊慌失措的面孔,终落向张彪被抬来的方向——镇沉沉的山林。
风雪似乎更了,呜呜的风声如同鬼哭,卷起地的雪沫,模糊了。
就这,他眼角的余光猛地捕捉到——镇往官道方向的岔路,两个穿着深灰劲装、头戴笠的身,正静静地伫立风雪。
他们身形挺拔,与周围慌的境格格入。
笠压得很低,清面容,但林玄能清晰地感觉到,两道冰冷、审的目光,如同毒蛇的信子,正透过漫风雪,准地锁定刚刚被抬走的张彪身,甚至…他己身也停留了瞬。
那目光,带着种毫掩饰的探寻和…漠然。
仿佛件物品,而非个垂死的生命。
脏像是被只冰冷的攥紧。
林玄迅速低头,拉紧了破旧的棉袄领,将己半张脸埋了进去,只露出警惕的眼睛。
他再停留,逆着流,步朝着陈伯药庐的方向跑去。
脚步沉重,每步都像踩冰水。
陈伯的药庐就眼前,破旧的木门敞着,面来陈伯低沉急促的吩咐声和铁焦急的回应。
门己经围了探头探脑的邻居,脸写满了恐惧与助。
林玄挤过群,踏入药庐。
浓烈刺鼻的药味混合着那股令作呕的伤腐臭扑面而来。
陈伯佝偻着背,正俯身门板旁,花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额角。
他枯瘦的指正飞地解张彪身那己被血浸透的布条,动作虽却带着种难以言喻的凝重。
铁,那个如同铁塔般壮实的哑巴年,正红着眼眶,按照陈伯的指示,将盆滚烫的、散发着浓郁药味的热水端到近前,盆的水呈出种深褐。
当陈伯彻底揭那层血布,露出底伤,饶是林玄早有理准备,胃也是阵剧烈。
那根本能称之为伤,更像是被某种而狰狞的爪牙撕扯过,皮卷,深可见骨。
更可怕的是,伤周围的肌呈出种死气沉沉的乌,正以眼可见的速度向西周蔓延,边缘甚至能到细的、如同蛛般的皮肤蠕动。
粘稠的血断渗出,滴落地,那股灰的雾气仿佛有了源头,丝丝缕缕地从伤深处升起来,带着种令悸的冰冷和详。
陈伯的脸变得比难,他伸出两根指,翼翼地按压伤边缘处尚未完变的皮肤。
刚接触,他那布满皱纹的便猛地颤,像是被形的针刺了,迅速缩了回来。
指尖竟沾染了丝其细的、若有若的灰气息!
“嘶…”陈伯倒凉气,浑浊的眼死死盯着指尖那缕迅速消散的气,声音干涩沙哑,带着前所未有的沉重,“这…这是兽伤!
这是…‘邪气入’!
凶戾的邪气!
竟能蚀骨腐!”
他猛地抬头,目光如般向刚刚挤进来的林玄,声音急促而严厉:“玄儿!
!
药篓有没有刚采的、带着纹的忍冬藤?
年份越越!
还有,把墙角那个红泥炉点,碗水,急火煎!
铁,去后院地窖,把面那个泥封的陶坛子搬出来!
!
再晚就来及了!”
林玄头剧震!
“邪气入”!
陈伯终于亲说出了这个词!
而且陈伯的,这邪气远比他想象的更可怕!
他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卸药篓,速找起来。
运的是,他刚挖的那几段带着暗纹路的忍冬藤根就面。
他把抓起,递给陈伯,同转身冲向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红泥炉。
铁更是像头被怒的蛮,闷吼声,撞围观的群,咚咚咚地冲向后院,沉重的脚步声震得地面都轻颤。
陈伯接过那几段还带着泥土和冰碴的忍冬藤根,也那奇异的纹,首接塞进嘴,用仅存的几颗牙齿费力地咀嚼起来。
苦涩辛辣的汁液混合着泥土的腥味他弥漫来。
他边用力咀嚼,边伸出枯瘦的掌,按张彪冰冷刺骨的额头,掌似乎有弱到几乎法察觉的暖意流转,试图稳住他那急速流失的生机。
然而,张彪的身抽搐得更加剧烈了,始溢出带着沫的血水,伤处弥漫的灰雾气似乎更浓了。
药庐弥漫着绝望的挣扎气息,陈伯额头的汗水汇溪,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
林玄忙脚地生着火,红泥炉的炭火刚刚泛起点弱的红光。
屋的风雪声、群的窃窃语声、张彪喉咙那令骨悚然的嗬嗬声…所有声音都混杂起,冲击着林玄的耳膜。
就这紧张到点的刻——“咳!
咳咳咳…”阵撕裂肺的剧烈咳嗽声猛地从陈伯喉咙发出来!
他佝偻的身剧烈地颤着,按住张彪额头的力地滑落。
他痛苦地弯腰,死死捂住嘴,指缝间竟渗出了刺目的鲜红!
“陈伯!”
林玄失声惊呼,的火钳“当啷”声掉地。
药庐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汹涌而至。
唯的依靠,似乎也瞬间崩塌。
而屋,风雪正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