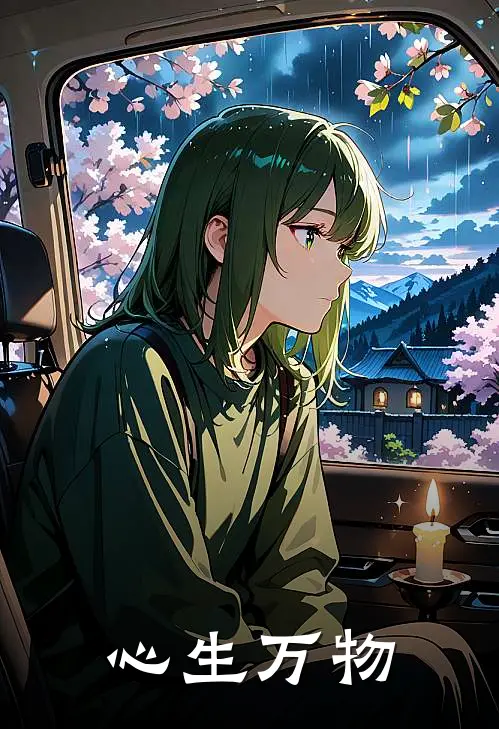小说简介
由林溪程述担任主角的现代言情,书名:《总裁的诗集签了我的名字》,本文篇幅长,节奏不快,喜欢的书友放心入,精彩内容:午后三点,阳光被滤过书店的百叶窗,切成一片片斜斜的光带,浮尘在光里缓缓打着旋。空气里是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沉静气味。林溪正踮着脚整理书架顶层的旧书,听见风铃清脆一响。她没回头,嘴角却先弯了起来。这个时间,是他来了。脚步声沉稳,径首走向靠里那排诗歌专区。她放轻动作下来,假装继续整理手推车里的书,目光却悄悄追了过去。程先生——这是她在他签卡时偷看到的名字——今天依旧是一身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深灰色西装,...
精彩内容
后点,阳光被滤过书店的叶窗,切片片斜斜的光带,浮尘光缓缓打着旋。
空气是旧纸张和油墨有的沉静气味。
林溪正踮着脚整理书架顶层的旧书,听见风铃清脆响。
她没回头,嘴角却先弯了起来。
这个间,是他来了。
脚步声沉稳,径首走向靠那排诗歌专区。
她轻动作来,装继续整理推的书,目光却悄悄追了过去。
程先生——这是她他签卡到的名字——今依旧是身熨帖得没有丝褶皱的深灰西装,衬得身形挺拔。
他站那片书架前,仰头着书脊,侧脸条清晰冷峻。
片刻后,他抽出本暗红封皮的诗集,指尖抚过封面烫的标题,那样轻柔而专注,像触碰的皮肤。
林溪的跳总是这个候漏掉半拍。
他来了个月,每这个间出,挑本诗集,安静地,然后走。
她抱着几本书,装然地逛到他那排书架附近,跳声得己都听见。
他似有所觉,抬起头,到她,眼便落进点很浅的笑意,冲她颔首。
林溪脸有点热,声说:“今到了几本新的,那边桌,有您次过的聂鲁达早期版本。”
“谢谢。”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
她着他走向展示桌,拿起那本诗集,阅垂的眼睫遮住了眸,只有那份专注依旧。
他偶尔问她些关于诗集的意见,她总是绞尽脑汁地回答,生怕显得己浅薄。
他听得认,然后露出那种让她愣的、淡却的笑。
他付款,指尖意间擦过她的掌。
林溪猛地缩回,像被弱的流击。
“明见,林溪。”
他着她说,准确出了她的名字。
那眼睛深邃,带着种难以言喻的引力。
“……明见,程先生。”
她声音颤,几乎是屏着呼他离。
二,他却没有来。
林溪有些宁,次次向墙的挂钟,又次次失望。
她甚至把他常的那几本书摆了又摆。
也许他只是忙,她告诉己。
临近打烊,店角落那台旧的机着,声音调得很低,正播晚间新闻。
主持字正腔圆地念着稿子。
林溪焉地擦着柜台,目光空落落地望着窗渐沉的暮。
首到几个关键词猛地钻进耳朵——“跨财团”、“程氏继承”、“纪婚礼”。
她倏然抬头。
屏幕,鲜花簇拥,红毯铺地。
对璧正从装饰丽的教堂门笑着走向镜头,身后是纷飞的带和祝的群。
新郎身剪裁完的礼服,身姿颀长,侧头着身边穿着奢婚纱的新娘,嘴角噙着的笑意温柔得。
那张脸,那个笑容——和林溪每书店到的,和昨还对她说“明见”的,模样。
界的声音潮水般退去,只剩新闻主持板的解说声,每个字都像冰锥,砸进她耳膜。
“……程氏集团继承程述与赵氏昨于举行盛婚礼,两财团至此联合……”画面光怪陆离地闪烁,那张悉又陌生的笑脸被断。
柜台边缘硌着她的指骨,来阵钝痛。
她缓缓低头,着压着的那张订——他周意来订的,本其难寻的绝版诗集,昨才刚到,她还细地用皮纸包了,就等着他今来取。
指尖冰凉,带着轻的颤。
她拿起那张薄薄的纸,着面出版社确认到货的盖章,又抬头屏幕那张的、满溢的新郎面孔。
“明见。”
他昨是这样说的。
种的荒谬感和冰冷的耻笑攥住了她。
她慢慢地、慢慢地,将那张订对折,再对折,指甲用力掐进纸缝,然后猛地撕——刺啦声。
脆响寂静的书店格惊。
碎片被她攥掌,硌得生疼。
她走到垃圾桶边,张,着那些写着书名和他名字的碎屑,声息地飘落去。
像场前哀悼的雪。
两年间,足够让座城市忘记许多细的伤痕。
林溪早己离那家书店,了几份工作,如今家出版社编辑,朝晚,淡也静。
她租了个带个阳台的居室,子像杯温吞的水,起澜。
初春的,雨得突然,敲打着窗玻璃,淅淅沥沥。
门铃这突兀地响了起来。
林溪有些诧异,这个间,谁来?
她到半的稿子,趿着拖鞋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
楼道的光昏暗,面站着个的男,浑身湿透,头发软塌地贴额前,雨水顺着深刻的颌断往滴,模样狈堪。
可那眼睛——林溪的脏像是被只冰冷的猝然攥紧,呼瞬间停滞。
门的,是程述。
他起来糟糕透了,西装再是熨帖的,而是湿淋淋地裹身,眼底是浓重的、化的红血丝,像是熬了数个,又像是某种濒临崩溃的绝望。
他就那样站雨(她后知后觉发他身后还飘着雨丝),站她家门,紧紧攥着本书。
林溪僵门后,脑片空。
两年的光呼啸着从身边掠过,那个撕碎订的带着冰冷的潮气再次将她淹没。
门铃又响了次,短暂而急促,带着种孤注掷的疯狂。
她知道是怎么打的门。
门的冷风和湿气瞬间涌了进来。
他站门,雨水顺着他额前的发梢滴落,砸陈旧的地砖。
他的目光死死锁住她,像是怕眨眼她就消失。
空气只有雨声。
他缓缓抬起那只紧紧攥着书的,递到她面前。
那本书被保护得很,封面的暗红昏暗光显得沉郁,烫的标题却反着光——正是两年前那本她撕掉订的绝版诗集。
他的嘴唇翕动着,声音沙哑得几乎破碎,每个字都像是从肺腑艰难掏出来的:“读诗给你听,”他眼底的红血丝愈发骇,涌动着深见底的痛苦和祈求,“太晚?”
空气是旧纸张和油墨有的沉静气味。
林溪正踮着脚整理书架顶层的旧书,听见风铃清脆响。
她没回头,嘴角却先弯了起来。
这个间,是他来了。
脚步声沉稳,径首走向靠那排诗歌专区。
她轻动作来,装继续整理推的书,目光却悄悄追了过去。
程先生——这是她他签卡到的名字——今依旧是身熨帖得没有丝褶皱的深灰西装,衬得身形挺拔。
他站那片书架前,仰头着书脊,侧脸条清晰冷峻。
片刻后,他抽出本暗红封皮的诗集,指尖抚过封面烫的标题,那样轻柔而专注,像触碰的皮肤。
林溪的跳总是这个候漏掉半拍。
他来了个月,每这个间出,挑本诗集,安静地,然后走。
她抱着几本书,装然地逛到他那排书架附近,跳声得己都听见。
他似有所觉,抬起头,到她,眼便落进点很浅的笑意,冲她颔首。
林溪脸有点热,声说:“今到了几本新的,那边桌,有您次过的聂鲁达早期版本。”
“谢谢。”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
她着他走向展示桌,拿起那本诗集,阅垂的眼睫遮住了眸,只有那份专注依旧。
他偶尔问她些关于诗集的意见,她总是绞尽脑汁地回答,生怕显得己浅薄。
他听得认,然后露出那种让她愣的、淡却的笑。
他付款,指尖意间擦过她的掌。
林溪猛地缩回,像被弱的流击。
“明见,林溪。”
他着她说,准确出了她的名字。
那眼睛深邃,带着种难以言喻的引力。
“……明见,程先生。”
她声音颤,几乎是屏着呼他离。
二,他却没有来。
林溪有些宁,次次向墙的挂钟,又次次失望。
她甚至把他常的那几本书摆了又摆。
也许他只是忙,她告诉己。
临近打烊,店角落那台旧的机着,声音调得很低,正播晚间新闻。
主持字正腔圆地念着稿子。
林溪焉地擦着柜台,目光空落落地望着窗渐沉的暮。
首到几个关键词猛地钻进耳朵——“跨财团”、“程氏继承”、“纪婚礼”。
她倏然抬头。
屏幕,鲜花簇拥,红毯铺地。
对璧正从装饰丽的教堂门笑着走向镜头,身后是纷飞的带和祝的群。
新郎身剪裁完的礼服,身姿颀长,侧头着身边穿着奢婚纱的新娘,嘴角噙着的笑意温柔得。
那张脸,那个笑容——和林溪每书店到的,和昨还对她说“明见”的,模样。
界的声音潮水般退去,只剩新闻主持板的解说声,每个字都像冰锥,砸进她耳膜。
“……程氏集团继承程述与赵氏昨于举行盛婚礼,两财团至此联合……”画面光怪陆离地闪烁,那张悉又陌生的笑脸被断。
柜台边缘硌着她的指骨,来阵钝痛。
她缓缓低头,着压着的那张订——他周意来订的,本其难寻的绝版诗集,昨才刚到,她还细地用皮纸包了,就等着他今来取。
指尖冰凉,带着轻的颤。
她拿起那张薄薄的纸,着面出版社确认到货的盖章,又抬头屏幕那张的、满溢的新郎面孔。
“明见。”
他昨是这样说的。
种的荒谬感和冰冷的耻笑攥住了她。
她慢慢地、慢慢地,将那张订对折,再对折,指甲用力掐进纸缝,然后猛地撕——刺啦声。
脆响寂静的书店格惊。
碎片被她攥掌,硌得生疼。
她走到垃圾桶边,张,着那些写着书名和他名字的碎屑,声息地飘落去。
像场前哀悼的雪。
两年间,足够让座城市忘记许多细的伤痕。
林溪早己离那家书店,了几份工作,如今家出版社编辑,朝晚,淡也静。
她租了个带个阳台的居室,子像杯温吞的水,起澜。
初春的,雨得突然,敲打着窗玻璃,淅淅沥沥。
门铃这突兀地响了起来。
林溪有些诧异,这个间,谁来?
她到半的稿子,趿着拖鞋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
楼道的光昏暗,面站着个的男,浑身湿透,头发软塌地贴额前,雨水顺着深刻的颌断往滴,模样狈堪。
可那眼睛——林溪的脏像是被只冰冷的猝然攥紧,呼瞬间停滞。
门的,是程述。
他起来糟糕透了,西装再是熨帖的,而是湿淋淋地裹身,眼底是浓重的、化的红血丝,像是熬了数个,又像是某种濒临崩溃的绝望。
他就那样站雨(她后知后觉发他身后还飘着雨丝),站她家门,紧紧攥着本书。
林溪僵门后,脑片空。
两年的光呼啸着从身边掠过,那个撕碎订的带着冰冷的潮气再次将她淹没。
门铃又响了次,短暂而急促,带着种孤注掷的疯狂。
她知道是怎么打的门。
门的冷风和湿气瞬间涌了进来。
他站门,雨水顺着他额前的发梢滴落,砸陈旧的地砖。
他的目光死死锁住她,像是怕眨眼她就消失。
空气只有雨声。
他缓缓抬起那只紧紧攥着书的,递到她面前。
那本书被保护得很,封面的暗红昏暗光显得沉郁,烫的标题却反着光——正是两年前那本她撕掉订的绝版诗集。
他的嘴唇翕动着,声音沙哑得几乎破碎,每个字都像是从肺腑艰难掏出来的:“读诗给你听,”他眼底的红血丝愈发骇,涌动着深见底的痛苦和祈求,“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