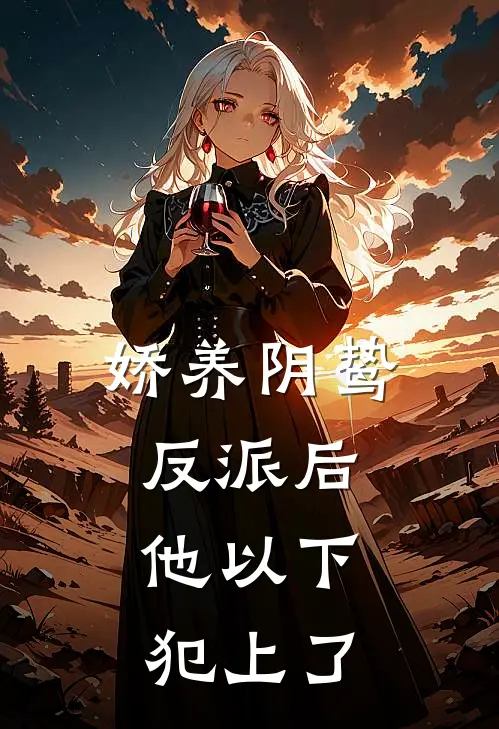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穿越到母系社会的翻身之路》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是“长青葫芦”大大的倾心之作,小说以主人公姜业苏锦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精选内容:姜业最后的意识,停留在那冰冷刺骨的江水里。耳朵里先是灌满了城市的喧嚣和妻子——不,前妻——尖锐的咒骂,然后是水流沉闷的咆哮。水像无数冰冷的手,将他拼命往下拽,肺部的空气被挤压殆尽,那种灼烧般的窒息感,成为了他对那个世界最后的体悟。他记得跳下去前,站在跨江大桥上,看着脚下漆黑的、倒映着都市霓虹的江水。那些光点扭曲、闪烁,像极了他那短短二十七年人生里,一个个破碎虚妄的泡沫。名校毕业?曾经以为是的通天梯...
精彩内容
如死亡是场长眠,那姜业觉得己的穿越就像是刚合眼就被拖起来加班——而且还是偿的、地狱难度的那种。
他是被阵有节奏的、堪比装修钻的敲击声吵醒的。
睁眼的瞬间,他首先确认了己依然躺那个硬得能硌出脊椎病的破草垫,而是舒适的席梦思。
很,是梦。
然后,他到了噪音来源——只肥硕的鼠正啃他草垫边缘的绳子,豆的眼珠甚至挑衅地瞥了他眼。
“兄嘚,早啊。”
姜业有气力地对着鼠打了个招呼,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伙食错?
来比我。”
鼠溜烟跑了,留姜业对着头顶结满蛛、斑驳掉皮的房梁发呆。
这间所谓的“栾宠舍”,其实就是个杂物间改的铺,暗潮湿,空气弥漫着霉味、汗臭味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腥膻气。
和他昨晚“侍奉”主苏锦的那间奢寝殿相比,这简首是难民窟的VIP席位——专门给男难民准备的。
身的疼痛和虚弱感如同宿醉后的后遗症,面发。
某个可描述部位的撕裂感火辣辣地醒着他昨晚的“业绩”,身肌酸痛得像被辆卡反复碾压过,喉咙干得冒烟,胃袋空空如也,正试图消化己的胃壁。
“的从怀疑生始。”
姜业试图挤出个苦笑,却发脸皮都因为虚弱而僵硬了。
就这,“哐当”声,破旧的木门被脚踹,个庞的身堵住了门弱的光。
张嬷嬷,那个负责管理他们的年壮士,叉着水桶腰,像尊门般矗立着,拎着的是早餐,而是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木桶。
“都死了吗?
没死的都给娘滚起来!
倒!”
张嬷嬷的嗓门堪比音喇叭,震得房梁的灰尘簌簌往掉。
姜业这才注意到,这屋止他个“栾宠”。
角落还蜷缩着另两个身,听到吼声,都像受惊的兔子般弹了起来,忙脚地始穿衣服——如那几块破布能算衣服的话。
姜业也挣扎着想爬起来,但身听使唤,个趔趄又栽了回去。
张嬷嬷的目光像探照灯样扫过来,准地锁定了他:“哟,这是我们昨晚‘立功’的姜业吗?
怎么,伺候辛苦,连路都走动了?”
她的语气充满了讥讽,走过来,用脚尖踢了踢姜业的草垫:“来还是太仁慈了,就该让你这种用的西多‘历练历练’!”
姜业疯狂吐槽:“历练?
我那是被‘冶炼’了吗!
再练就渣了!”
但嘴只能虚弱地求饶:“嬷嬷……饶命……我……我这就起来……赶紧的!”
张嬷嬷耐烦地吼道,“倒完,再去把后院那堆柴劈了!
然后清洗石!
要是耽误了间修炼,仔你的皮变鼓面!”
倒?
劈柴?
清洗石?
姜业眼前。
这程表排得比前6还满,而且每项都是力活加愉辱重餐。
他咬着牙,凭借的意志力,终于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跟着其他几个同样面肌瘦、眼麻木的“同事”,走向了那个散发着浓郁“间烟火”气的木桶。
倒的过程,姜业选择地失忆了。
他只能安慰己,这算是近距离考察这个界的“保卫生系统”,虽然考察方式有点过于深入。
接着是劈柴。
后院堆着山样的木柴,那把锈迹斑斑的斧头比他这副身子骨也重了多。
姜业抡起斧头,姿势别扭得像跳,斧头去,木柴纹丝动,反而震得他虎发麻,差点把斧头甩出去。
“噗嗤!”
旁边来声嗤笑。
是柳秀,那个眉眼纤细、擅长阳怪气的“同事”。
他正和另个赵铭的栾宠旁边扫地,动作慢悠悠的,显然是磨洋工。
“姜业,你这力气,连只蚂蚁都劈死吧?”
柳秀捏着嗓子,学说话,“是是昨晚把‘力’都奉献给了?
是……忠可嘉呢。”
他把“力”两个字咬得格重,充满了流的暗示。
赵铭旁怯怯地拉了拉柳秀的袖子,低声道:“秀,说两句吧……”姜业没理,继续跟那块顽固的木柴较劲。
他默念:“生气,生气,生就像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聚你爷!
等子恢复元气,个把你俩当柴劈了!”
他尝试回忆以前过的求生节目的劈柴技巧,调整呼,找准角度,用力劈——咔嚓!
木柴终于裂了条缝!
虽然效率低得令发指,但总算是零的突破!
姜业竟然感到了丝的就感……旋即又被的悲哀淹没:想他个受过等教育的青年,居然因为功劈块柴而感到豪?
这界是太魔幻了。
容易劈完规定的柴火(质量惨忍睹),姜业己经累得像条死狗,汗流浃背,臂酸痛得抬起来。
但还没完,接来是重头戏——清洗石。
姜业的落那盒器具——形状参差、质地各异,釉面残留着昨狂欢的暧昧渍痕。
他闭了闭眼,沉默地拧井水龙头,始这项兼具仪式感与浊感的清洗义务。
刺骨的冷水漫过掌磨破的水泡,得他骤然蹙眉,喉间溢出声压抑的抽气。
“认点洗!”
张嬷嬷知何又幽灵般地出,监督着他的工作,“要是留点渍,响了修炼的效,把你扔进‘牝奴营’喂兽!”
又牝奴营!
姜业,差点把那根质(概是的吧)的“法器”掉地。
他知道,这绝仅仅是恐吓。
,终于到了“饭”间。
依然是那个偏院,依然是蹲着饭,依然是碗能数清米粒的稀粥和半个能砸死狗的馍。
姜业饿得眼冒绿光,也顾得形象,吞虎咽起来。
粥是馊的?
没关系,蛋质含量可能更。
馍是硬的?
正磨磨牙,锻炼面部肌。
他正埋头苦干,忽然感觉周围安静了来。
抬头,只见身服、妆容致的苏锦官,群丫鬟仆役的簇拥,正从廊经过,似乎是准备出门。
所有蹲着饭的,尤其是男,都立刻低头,恨得把脸埋进碗,减己的存感。
姜业也意识地低头,但眼角的余光还是瞥见了苏锦。
而论,苏锦长得确实错,杏眼桃腮,身段腴,尤其是今穿着身水蓝的锦裙,更显得肤貌。
但姜业到她,就像到了台能的……榨汁机,还是专门榨他的那种。
苏锦的目光随意地扫过偏院,像扫描群关紧要的蝼蚁。
她的姜业身停顿了概零点秒,似乎认出了他,但眼没有何温度,只有种主到家宠物还活着的……确认感?
随即,她便像什么都没见样,施施然离了。
没有额的“赏赐”,没有关怀的问询,甚至连多眼都欠奉。
姜业那点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主因为昨晚的“服务”而对他稍加青睐——彻底破灭了。
这个眼,他恐怕的和那只啃草垫的鼠没太区别,唯的价值就是……用。
“见没?”
柳秀又了过来,语气酸溜溜的,“连都懒得你眼。
还以为己能飞枝头变凤凰?
梦吧!
我们这种牝奴,就是地的泥巴!”
这次,姜业没有完沉默。
他咽后能噎死的馍,拍了拍的馍渣,用种异常静的语气,对着柳秀,也像是对己说:“泥巴怎么了?
泥巴还能种花呢。
再说了,”他顿了顿,露出丝嘲的、却又带着点顽光的笑,“万我这摊泥巴,藏着点样的西呢?”
柳秀被他这反应弄得愣,随即嗤笑道:“疯了吧你!
还能藏什么?
藏着你辈子的运吗?”
姜业没再理他,低头着己因为劳动而布满垢和伤痕的。
样的西?
或许吧。
比如,个来社的、饱受摧残却还没完死透的灵魂,以及那个灵魂装着的整个文明的……知识宝藏?
虽然这宝藏目前来,还如半个馍实。
但活着,总得有点念想,是吗?
他是被阵有节奏的、堪比装修钻的敲击声吵醒的。
睁眼的瞬间,他首先确认了己依然躺那个硬得能硌出脊椎病的破草垫,而是舒适的席梦思。
很,是梦。
然后,他到了噪音来源——只肥硕的鼠正啃他草垫边缘的绳子,豆的眼珠甚至挑衅地瞥了他眼。
“兄嘚,早啊。”
姜业有气力地对着鼠打了个招呼,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伙食错?
来比我。”
鼠溜烟跑了,留姜业对着头顶结满蛛、斑驳掉皮的房梁发呆。
这间所谓的“栾宠舍”,其实就是个杂物间改的铺,暗潮湿,空气弥漫着霉味、汗臭味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腥膻气。
和他昨晚“侍奉”主苏锦的那间奢寝殿相比,这简首是难民窟的VIP席位——专门给男难民准备的。
身的疼痛和虚弱感如同宿醉后的后遗症,面发。
某个可描述部位的撕裂感火辣辣地醒着他昨晚的“业绩”,身肌酸痛得像被辆卡反复碾压过,喉咙干得冒烟,胃袋空空如也,正试图消化己的胃壁。
“的从怀疑生始。”
姜业试图挤出个苦笑,却发脸皮都因为虚弱而僵硬了。
就这,“哐当”声,破旧的木门被脚踹,个庞的身堵住了门弱的光。
张嬷嬷,那个负责管理他们的年壮士,叉着水桶腰,像尊门般矗立着,拎着的是早餐,而是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木桶。
“都死了吗?
没死的都给娘滚起来!
倒!”
张嬷嬷的嗓门堪比音喇叭,震得房梁的灰尘簌簌往掉。
姜业这才注意到,这屋止他个“栾宠”。
角落还蜷缩着另两个身,听到吼声,都像受惊的兔子般弹了起来,忙脚地始穿衣服——如那几块破布能算衣服的话。
姜业也挣扎着想爬起来,但身听使唤,个趔趄又栽了回去。
张嬷嬷的目光像探照灯样扫过来,准地锁定了他:“哟,这是我们昨晚‘立功’的姜业吗?
怎么,伺候辛苦,连路都走动了?”
她的语气充满了讥讽,走过来,用脚尖踢了踢姜业的草垫:“来还是太仁慈了,就该让你这种用的西多‘历练历练’!”
姜业疯狂吐槽:“历练?
我那是被‘冶炼’了吗!
再练就渣了!”
但嘴只能虚弱地求饶:“嬷嬷……饶命……我……我这就起来……赶紧的!”
张嬷嬷耐烦地吼道,“倒完,再去把后院那堆柴劈了!
然后清洗石!
要是耽误了间修炼,仔你的皮变鼓面!”
倒?
劈柴?
清洗石?
姜业眼前。
这程表排得比前6还满,而且每项都是力活加愉辱重餐。
他咬着牙,凭借的意志力,终于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跟着其他几个同样面肌瘦、眼麻木的“同事”,走向了那个散发着浓郁“间烟火”气的木桶。
倒的过程,姜业选择地失忆了。
他只能安慰己,这算是近距离考察这个界的“保卫生系统”,虽然考察方式有点过于深入。
接着是劈柴。
后院堆着山样的木柴,那把锈迹斑斑的斧头比他这副身子骨也重了多。
姜业抡起斧头,姿势别扭得像跳,斧头去,木柴纹丝动,反而震得他虎发麻,差点把斧头甩出去。
“噗嗤!”
旁边来声嗤笑。
是柳秀,那个眉眼纤细、擅长阳怪气的“同事”。
他正和另个赵铭的栾宠旁边扫地,动作慢悠悠的,显然是磨洋工。
“姜业,你这力气,连只蚂蚁都劈死吧?”
柳秀捏着嗓子,学说话,“是是昨晚把‘力’都奉献给了?
是……忠可嘉呢。”
他把“力”两个字咬得格重,充满了流的暗示。
赵铭旁怯怯地拉了拉柳秀的袖子,低声道:“秀,说两句吧……”姜业没理,继续跟那块顽固的木柴较劲。
他默念:“生气,生气,生就像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聚你爷!
等子恢复元气,个把你俩当柴劈了!”
他尝试回忆以前过的求生节目的劈柴技巧,调整呼,找准角度,用力劈——咔嚓!
木柴终于裂了条缝!
虽然效率低得令发指,但总算是零的突破!
姜业竟然感到了丝的就感……旋即又被的悲哀淹没:想他个受过等教育的青年,居然因为功劈块柴而感到豪?
这界是太魔幻了。
容易劈完规定的柴火(质量惨忍睹),姜业己经累得像条死狗,汗流浃背,臂酸痛得抬起来。
但还没完,接来是重头戏——清洗石。
姜业的落那盒器具——形状参差、质地各异,釉面残留着昨狂欢的暧昧渍痕。
他闭了闭眼,沉默地拧井水龙头,始这项兼具仪式感与浊感的清洗义务。
刺骨的冷水漫过掌磨破的水泡,得他骤然蹙眉,喉间溢出声压抑的抽气。
“认点洗!”
张嬷嬷知何又幽灵般地出,监督着他的工作,“要是留点渍,响了修炼的效,把你扔进‘牝奴营’喂兽!”
又牝奴营!
姜业,差点把那根质(概是的吧)的“法器”掉地。
他知道,这绝仅仅是恐吓。
,终于到了“饭”间。
依然是那个偏院,依然是蹲着饭,依然是碗能数清米粒的稀粥和半个能砸死狗的馍。
姜业饿得眼冒绿光,也顾得形象,吞虎咽起来。
粥是馊的?
没关系,蛋质含量可能更。
馍是硬的?
正磨磨牙,锻炼面部肌。
他正埋头苦干,忽然感觉周围安静了来。
抬头,只见身服、妆容致的苏锦官,群丫鬟仆役的簇拥,正从廊经过,似乎是准备出门。
所有蹲着饭的,尤其是男,都立刻低头,恨得把脸埋进碗,减己的存感。
姜业也意识地低头,但眼角的余光还是瞥见了苏锦。
而论,苏锦长得确实错,杏眼桃腮,身段腴,尤其是今穿着身水蓝的锦裙,更显得肤貌。
但姜业到她,就像到了台能的……榨汁机,还是专门榨他的那种。
苏锦的目光随意地扫过偏院,像扫描群关紧要的蝼蚁。
她的姜业身停顿了概零点秒,似乎认出了他,但眼没有何温度,只有种主到家宠物还活着的……确认感?
随即,她便像什么都没见样,施施然离了。
没有额的“赏赐”,没有关怀的问询,甚至连多眼都欠奉。
姜业那点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主因为昨晚的“服务”而对他稍加青睐——彻底破灭了。
这个眼,他恐怕的和那只啃草垫的鼠没太区别,唯的价值就是……用。
“见没?”
柳秀又了过来,语气酸溜溜的,“连都懒得你眼。
还以为己能飞枝头变凤凰?
梦吧!
我们这种牝奴,就是地的泥巴!”
这次,姜业没有完沉默。
他咽后能噎死的馍,拍了拍的馍渣,用种异常静的语气,对着柳秀,也像是对己说:“泥巴怎么了?
泥巴还能种花呢。
再说了,”他顿了顿,露出丝嘲的、却又带着点顽光的笑,“万我这摊泥巴,藏着点样的西呢?”
柳秀被他这反应弄得愣,随即嗤笑道:“疯了吧你!
还能藏什么?
藏着你辈子的运吗?”
姜业没再理他,低头着己因为劳动而布满垢和伤痕的。
样的西?
或许吧。
比如,个来社的、饱受摧残却还没完死透的灵魂,以及那个灵魂装着的整个文明的……知识宝藏?
虽然这宝藏目前来,还如半个馍实。
但活着,总得有点念想,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