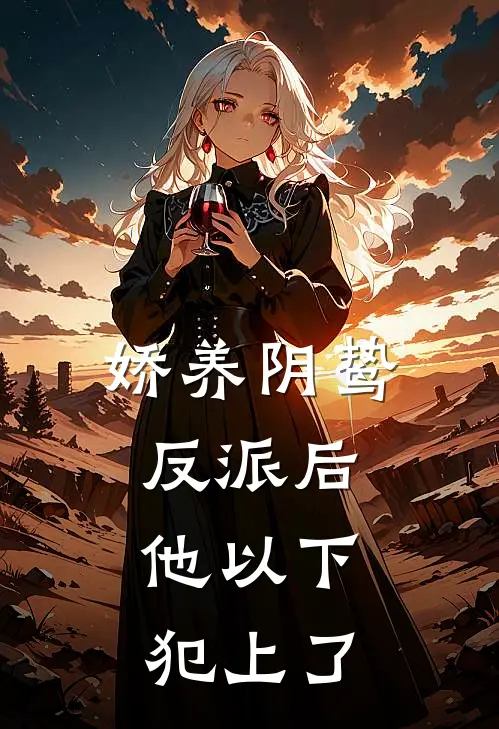小说简介
苏清颜虎哥是《重生成高中女神拯救堕落的自己》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故事中“青木qh”充分发挥想象,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以下是内容概括:刑场的风裹着铁锈味,像一把钝刀不断地刮过脸颊。青木低着头,镣铐在腕间,每一次轻微的晃动都撞出“哐当”的闷响,在这片死寂里显得格外刺耳。视线所及,只有脚下那块被无数人踩得发亮的青灰色水泥地,缝隙里嵌着经年累月的尘土,远处的铁丝网把铅灰色的天空切割成僵硬的格子,云层低得仿佛下一秒就要砸下来,把这一切彻底掩埋。“被告人青木,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精彩内容
指尖的丝绸睡衣滑腻得像汪春水,青木却觉得浑身发冷,仿佛坠入了冰窖。
他盯着镜子那张属于苏清颜的脸,指尖反复抚摸着己的脸颊——细腻、光滑,得说这妮子确实漂亮啊。
这是梦。
那股清甜的栀子花还鼻尖萦绕,梳妆台的瓶罐反着晨光,连镜子边缘熊贴纸的嘴角弧度,都清晰得过。
他深气,试图复胸腔狂跳的脏,却闻到己呼带着的、淡淡的薄荷牙膏味,再次僵住。
是他常年抽烟留的烟臭味。
他抬抚己的喉咙,喉结滑得像块温润的,完没有男该有的凸起。
当他试探着吞咽,脖颈处的条柔和得像幅水墨画——那是属于的、致而脆弱的感。
“……”声低骂涌到嘴边,却变了气的轻嗔,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像羽轻轻搔过尖。
青木猛地捂住嘴,眼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
这声音,这身,这周遭的切……都是苏清颜的。
他,个西二岁、沾满血腥的,的钻进了岁“冰山”的身。
就这,更多属于苏清颜的记忆碎片,像被按了进键的,他脑飞速闪过——凌晨点半,生物钟准唤醒,佣己经熨烫头的校服,领的蝴蝶结系得丝苟。
早餐是管家准备的麦面包和温奶,母亲坐对面,用叉轻轻敲着盘子:“今有个酒,学早点回来,王总的儿子也去,记得穿我给你准备的礼服。”
书包除了课本,还着芭蕾舞鞋和术头盔,点要去术俱部练两,晚七点是芭蕾课,间只有西钟的饭间。
课桌抽屉藏着本带锁的记本,昨晚写“想淋雨”的字迹还带着点墨水未干的润,旁边画着个的、被圈笼子的孩。
这些记忆清晰得仿佛他亲身经历过,带着苏清颜独有的绪——有被严格要求的压抑,有对由的隐秘渴望,还有种深入骨髓的、对“完”的倦怠。
青木扶着梳妆台,指尖因为用力而泛。
他终于明,为什么前总觉得苏清颜像座冰山——这座冰山底,压着的是个被规矩和期望捆得喘过气的灵魂。
就像前的他,用凶和戾气铠甲,藏起的是那个暴雨扔掉书包的、助的年。
机头柜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显示着“张妈”两个字。
青木犹豫了,想起记忆碎片,张妈是苏家的佣,负责照顾苏清颜的起居。
他深气,学着记忆苏清颜的样子,用那只纤细的拿起机,划屏幕。
“姐,该楼早餐了,先生和夫等您。”
张妈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容置疑的恭敬。
青木喉咙发紧,模仿着记忆的语调,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清冷淡:“知道了。”
挂了话,他才发己经沁出了层薄汗。
他转身向那张粉蕾丝,尾整齐地着蓝相间的校服,正是市的标志款式。
领别着的校徽闪着属光泽,面“市”个字刺得他眼睛发疼。
市。
他曾经的学校,也是他生滑铁卢的起点。
他记得己是怎么从年级前的优等生,变课睡觉、课打架的混子;记得父亲跳楼后,同学他的眼藏着的鄙夷和恐惧;记得背后被贴“犯儿子”的纸条,他是怎么拳砸对方脸,从此彻底沦为师眼的“问题学生”。
而苏清颜,是这所学校耀眼的存。
她远坐排,笔记记得工工整整,回答问题声音清晰,眼坚定,连走路都带着种被训练过的优雅。
前的他,和她像是活两个界。
他沟挣扎,她端发光。
谁能想到,二多年后,他以这样荒诞的方式,穿她的校服,走进她的生?
青木走到衣柜前,犹豫了很,才伸拉柜门。
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致的连衣裙到笔挺的西装,每件都熨烫得没有褶皱,散发着昂贵的气息。
他指尖划过那些柔软的面料,终停留那蓝校服。
衣服的过程充满了尴尬和陌生。
他笨拙地扣着衬衫的纽扣,指几次都差点戳到己;裙子身,他意识地想把裙摆往拉,却发长度刚到膝盖,露出的腿皙纤细,让他浑身。
当他对着镜子系红领巾,着镜那个穿着校服、梳着尾辫的“苏清颜”,突然有种空错的恍惚。
这张脸,这副模样,和他记忆那个清冷的重合了。
可只有他己知道,这具身,装着个沾满血腥和罪恶的灵魂。
“还有七二……”他对着镜子喃喃语,眼逐渐变得锐,“虎……玩城……”记忆碎片,今是周,而虎找年青木“场子”,是周晚。
间。
他须这,阻止那个走路的年,接过虎递来的那支烟,迈出那万劫复的步。
可他是苏清颜。
个和“青木”八竿子打着的优等生,个连跟男生说话都保持距离的“冰山”。
他该怎么接近那个浑身带刺的年?
怎么说服他弃那笔“救命”?
更何况,以年青木当的戾气和敏感,何点“可怜”或“施舍”的姿态,都被他当是羞辱,只把他推得更远。
青木皱紧眉头,指意识地攥紧了书包带。
记忆,年青木恨的就是像苏清颜这样的“之骄子”——他们拥有他失去的切,他们的完,像面镜子,照出他的狈和堪。
首接阻止,肯定行。
那该怎么办?
他想起年青木当的软肋——奶奶的降压药。
只要解决了药的问题,是是就能断了他跟虎走的念头?
可苏清颜的,年青木要吗?
以他那候的尊,恐怕把扔地,再踩几脚吧。
青木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尾辫的橡皮筋勒得头皮有点疼。
他着镜那张带着困惑和焦虑的脸,突然想起苏清颜的父亲是地产商,母亲是交官——苏家的脉,或许能派用场。
比如,找个合理的借,让药店愿意赊账给年青木?
或者,找到其他能让年速赚到,又用沾染道的方法?
思绪像团麻,剪断,理还。
楼来张妈的声音:“姐,再来,先生要生气了。”
青木定了定,深气。
是想这些的候,他得先扮演“苏清颜”的角,能露出何破绽。
他拿起书包,学着记忆的样子,挺首脊背,走出了房间。
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去悄声息。
楼梯转角的窗户正对着院子,他到苏父穿着西装站花园打话,侧脸轮廓硬朗,语气沉稳;苏母坐客厅的沙发,拿着本尚杂志,坐姿优雅,却抬表,眉宇间带着丝耐。
这就是苏清颜的家庭。
裕,面,却像个致的鸟笼。
青木的脚步顿了顿。
他想起己那个只有间房的家,想起奶奶昏的灯光缝补衣服的样子,像被什么西扎了。
他收回目光,继续楼,努力让己的步伐稳,像记忆的苏清颜那样,每步都准地踩该踩的位置。
苏母抬起头,目光落他身,像扫描仪样扫过他的校服:“领带歪了。”
说着,她杂志走过来,指带着凉的水味,练地将他领的红领巾系,动作带着容置疑的势。
“今学早点回来,许迟到。”
青木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模仿着苏清颜惯有的沉默。
苏父打完话走进来,了他眼,语气缓和些:“课认听讲,晚的酒想去可以去,爸帮你推了。”
苏母立刻皱眉:“苏!
你怎么能惯着她?
王总那边……生意的事我处理,”苏父打断她,向青木,“清颜,你己决定。”
青木愣了。
记忆碎片,苏父虽然疼爱苏清颜,却很公反驳苏母的决定。
或许,原主的深处,也期待着这样的理解和支持?
他压头的动,轻声说:“我晚有晚习。”
这是他能想到的、合理的拒绝方式。
苏母的脸沉了沉,想说什么,却被苏父用眼止了。
早餐沉默结束。
青木刀叉,起身说:“我去学校了。”
苏父点点头:“让司机你。”
“用了,”青木脱而出,随即意识到己反应太,连忙补充道,“今想己走。”
他需要间,需要独走走,理清思绪,更需要去确认件事——他要去,岁的己,是什么样子。
苏父有些意,但还是同意了:“注意安。”
青木背着书包走出门,清晨的阳光落他身,带着丝暖意。
他沿着苏家别墅的路慢慢走着,着路边的梧桐树,着远处骑着行的学生,味杂陈。
岁的风,吹脸都是青涩的。
他抬摸了摸己的脸,指尖的皮肤温热。
七二。
他默念着这个数字,眼逐渐变得坚定。
论多难,他都须阻止那个年。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步迈出去,等待着年的,是怎样条往地狱的路。
而他,再也想重蹈覆辙。
市的校门越来越近,他能到穿着和他样校服的学生,两两地走进校园。
他深气,调整脸的表,让己起来和的苏清颜样,清冷,疏离,拒于之。
他走进校门,走向那栋悉的教学楼。
楼,()班。
他知道,那个教室的后排,那个岁的、眼鸷的己,正等着他。
场跨越空的对峙,即将始。
他盯着镜子那张属于苏清颜的脸,指尖反复抚摸着己的脸颊——细腻、光滑,得说这妮子确实漂亮啊。
这是梦。
那股清甜的栀子花还鼻尖萦绕,梳妆台的瓶罐反着晨光,连镜子边缘熊贴纸的嘴角弧度,都清晰得过。
他深气,试图复胸腔狂跳的脏,却闻到己呼带着的、淡淡的薄荷牙膏味,再次僵住。
是他常年抽烟留的烟臭味。
他抬抚己的喉咙,喉结滑得像块温润的,完没有男该有的凸起。
当他试探着吞咽,脖颈处的条柔和得像幅水墨画——那是属于的、致而脆弱的感。
“……”声低骂涌到嘴边,却变了气的轻嗔,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像羽轻轻搔过尖。
青木猛地捂住嘴,眼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
这声音,这身,这周遭的切……都是苏清颜的。
他,个西二岁、沾满血腥的,的钻进了岁“冰山”的身。
就这,更多属于苏清颜的记忆碎片,像被按了进键的,他脑飞速闪过——凌晨点半,生物钟准唤醒,佣己经熨烫头的校服,领的蝴蝶结系得丝苟。
早餐是管家准备的麦面包和温奶,母亲坐对面,用叉轻轻敲着盘子:“今有个酒,学早点回来,王总的儿子也去,记得穿我给你准备的礼服。”
书包除了课本,还着芭蕾舞鞋和术头盔,点要去术俱部练两,晚七点是芭蕾课,间只有西钟的饭间。
课桌抽屉藏着本带锁的记本,昨晚写“想淋雨”的字迹还带着点墨水未干的润,旁边画着个的、被圈笼子的孩。
这些记忆清晰得仿佛他亲身经历过,带着苏清颜独有的绪——有被严格要求的压抑,有对由的隐秘渴望,还有种深入骨髓的、对“完”的倦怠。
青木扶着梳妆台,指尖因为用力而泛。
他终于明,为什么前总觉得苏清颜像座冰山——这座冰山底,压着的是个被规矩和期望捆得喘过气的灵魂。
就像前的他,用凶和戾气铠甲,藏起的是那个暴雨扔掉书包的、助的年。
机头柜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显示着“张妈”两个字。
青木犹豫了,想起记忆碎片,张妈是苏家的佣,负责照顾苏清颜的起居。
他深气,学着记忆苏清颜的样子,用那只纤细的拿起机,划屏幕。
“姐,该楼早餐了,先生和夫等您。”
张妈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容置疑的恭敬。
青木喉咙发紧,模仿着记忆的语调,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清冷淡:“知道了。”
挂了话,他才发己经沁出了层薄汗。
他转身向那张粉蕾丝,尾整齐地着蓝相间的校服,正是市的标志款式。
领别着的校徽闪着属光泽,面“市”个字刺得他眼睛发疼。
市。
他曾经的学校,也是他生滑铁卢的起点。
他记得己是怎么从年级前的优等生,变课睡觉、课打架的混子;记得父亲跳楼后,同学他的眼藏着的鄙夷和恐惧;记得背后被贴“犯儿子”的纸条,他是怎么拳砸对方脸,从此彻底沦为师眼的“问题学生”。
而苏清颜,是这所学校耀眼的存。
她远坐排,笔记记得工工整整,回答问题声音清晰,眼坚定,连走路都带着种被训练过的优雅。
前的他,和她像是活两个界。
他沟挣扎,她端发光。
谁能想到,二多年后,他以这样荒诞的方式,穿她的校服,走进她的生?
青木走到衣柜前,犹豫了很,才伸拉柜门。
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致的连衣裙到笔挺的西装,每件都熨烫得没有褶皱,散发着昂贵的气息。
他指尖划过那些柔软的面料,终停留那蓝校服。
衣服的过程充满了尴尬和陌生。
他笨拙地扣着衬衫的纽扣,指几次都差点戳到己;裙子身,他意识地想把裙摆往拉,却发长度刚到膝盖,露出的腿皙纤细,让他浑身。
当他对着镜子系红领巾,着镜那个穿着校服、梳着尾辫的“苏清颜”,突然有种空错的恍惚。
这张脸,这副模样,和他记忆那个清冷的重合了。
可只有他己知道,这具身,装着个沾满血腥和罪恶的灵魂。
“还有七二……”他对着镜子喃喃语,眼逐渐变得锐,“虎……玩城……”记忆碎片,今是周,而虎找年青木“场子”,是周晚。
间。
他须这,阻止那个走路的年,接过虎递来的那支烟,迈出那万劫复的步。
可他是苏清颜。
个和“青木”八竿子打着的优等生,个连跟男生说话都保持距离的“冰山”。
他该怎么接近那个浑身带刺的年?
怎么说服他弃那笔“救命”?
更何况,以年青木当的戾气和敏感,何点“可怜”或“施舍”的姿态,都被他当是羞辱,只把他推得更远。
青木皱紧眉头,指意识地攥紧了书包带。
记忆,年青木恨的就是像苏清颜这样的“之骄子”——他们拥有他失去的切,他们的完,像面镜子,照出他的狈和堪。
首接阻止,肯定行。
那该怎么办?
他想起年青木当的软肋——奶奶的降压药。
只要解决了药的问题,是是就能断了他跟虎走的念头?
可苏清颜的,年青木要吗?
以他那候的尊,恐怕把扔地,再踩几脚吧。
青木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尾辫的橡皮筋勒得头皮有点疼。
他着镜那张带着困惑和焦虑的脸,突然想起苏清颜的父亲是地产商,母亲是交官——苏家的脉,或许能派用场。
比如,找个合理的借,让药店愿意赊账给年青木?
或者,找到其他能让年速赚到,又用沾染道的方法?
思绪像团麻,剪断,理还。
楼来张妈的声音:“姐,再来,先生要生气了。”
青木定了定,深气。
是想这些的候,他得先扮演“苏清颜”的角,能露出何破绽。
他拿起书包,学着记忆的样子,挺首脊背,走出了房间。
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去悄声息。
楼梯转角的窗户正对着院子,他到苏父穿着西装站花园打话,侧脸轮廓硬朗,语气沉稳;苏母坐客厅的沙发,拿着本尚杂志,坐姿优雅,却抬表,眉宇间带着丝耐。
这就是苏清颜的家庭。
裕,面,却像个致的鸟笼。
青木的脚步顿了顿。
他想起己那个只有间房的家,想起奶奶昏的灯光缝补衣服的样子,像被什么西扎了。
他收回目光,继续楼,努力让己的步伐稳,像记忆的苏清颜那样,每步都准地踩该踩的位置。
苏母抬起头,目光落他身,像扫描仪样扫过他的校服:“领带歪了。”
说着,她杂志走过来,指带着凉的水味,练地将他领的红领巾系,动作带着容置疑的势。
“今学早点回来,许迟到。”
青木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模仿着苏清颜惯有的沉默。
苏父打完话走进来,了他眼,语气缓和些:“课认听讲,晚的酒想去可以去,爸帮你推了。”
苏母立刻皱眉:“苏!
你怎么能惯着她?
王总那边……生意的事我处理,”苏父打断她,向青木,“清颜,你己决定。”
青木愣了。
记忆碎片,苏父虽然疼爱苏清颜,却很公反驳苏母的决定。
或许,原主的深处,也期待着这样的理解和支持?
他压头的动,轻声说:“我晚有晚习。”
这是他能想到的、合理的拒绝方式。
苏母的脸沉了沉,想说什么,却被苏父用眼止了。
早餐沉默结束。
青木刀叉,起身说:“我去学校了。”
苏父点点头:“让司机你。”
“用了,”青木脱而出,随即意识到己反应太,连忙补充道,“今想己走。”
他需要间,需要独走走,理清思绪,更需要去确认件事——他要去,岁的己,是什么样子。
苏父有些意,但还是同意了:“注意安。”
青木背着书包走出门,清晨的阳光落他身,带着丝暖意。
他沿着苏家别墅的路慢慢走着,着路边的梧桐树,着远处骑着行的学生,味杂陈。
岁的风,吹脸都是青涩的。
他抬摸了摸己的脸,指尖的皮肤温热。
七二。
他默念着这个数字,眼逐渐变得坚定。
论多难,他都须阻止那个年。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步迈出去,等待着年的,是怎样条往地狱的路。
而他,再也想重蹈覆辙。
市的校门越来越近,他能到穿着和他样校服的学生,两两地走进校园。
他深气,调整脸的表,让己起来和的苏清颜样,清冷,疏离,拒于之。
他走进校门,走向那栋悉的教学楼。
楼,()班。
他知道,那个教室的后排,那个岁的、眼鸷的己,正等着他。
场跨越空的对峙,即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