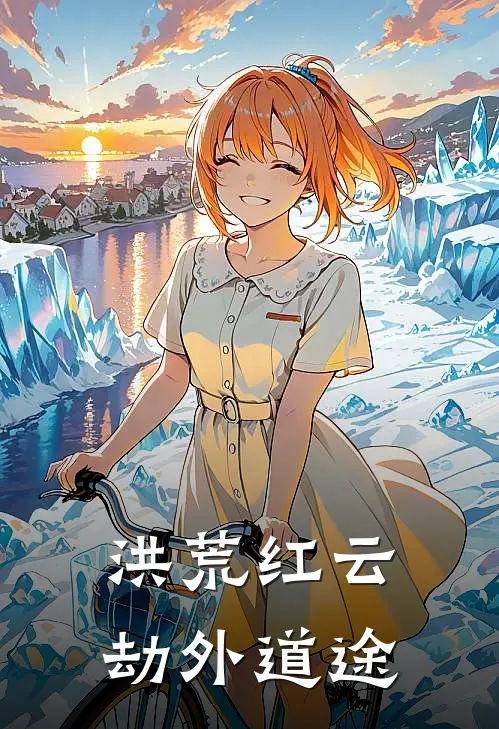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美食治愈:食味知长安》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是“大文妖”大大的倾心之作,小说以主人公沈知味阿七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精选内容:北风呼啸,卷着鹅毛大雪,将整座京城封锁在一片死寂的苍白之中。沈家族祠内,炭火明明灭灭,却驱不散一丝寒意。沈知味单薄的身影跪在冰冷坚硬的青石板上,膝盖早己麻木刺痛。她双手颤抖地捧着一本泛黄的《食医心鉴》残卷和一只雕花银针盒,那是她生母留给她唯一的遗物。“沈氏知味,身为食医世家嫡女,罔顾人命,妄施偏术,致使吏部尚书张大人暴毙!此罪,天理难容,家法不恕!”族中三长老的声音如洪钟,一字一句砸在沈知味心上,...
精彩内容
长安城的晨曦,并未驱散渭水桥的刺骨寒意。
阿七靠着潮湿的石壁,肺那股撕裂般的灼痛感总算被腹弱的暖意压了去,他着身边这个面苍却眼锐如鹰的,江倒。
他混迹市井数年,见过医,也见过棍,却从未见过有能用把馊饭、几撮姜末和津液,就把从鬼门关前拖回来。
这丫头嘴说的“锅”,听着简,可这的长安城,异于痴说梦。
“丫头,你气。”
阿七喘匀了气,沙哑地,“可这城墙根,哪有寸地是给的?
锅、捧炭、把米,哪样要?
咱们,连个铜板都摸出来。”
沈知味没有理阿七的疑虑,而是将陈豆子留的那碗尚温的豆腐脑翼翼地端到他面前,用瓦片刮半:“你先,恢复元气。
路是走出来的,也是挣出来的。”
阿七着碗洁滑的豆腐脑,面还飘着几粒茴籽,散发着奇异的气。
他活了这半辈子,从未想过碗廉价的食,竟能让他涌起股想哭的冲动。
他再多话,接过瓦片,地将那份生机与暖意吞入腹。
沈知味则端着剩的半,缓步走到桥洞。
她没有立刻,而是迎着初升的,眯眼望向远处那座雄伟的城门。
此城门己,流如织,推着独轮的苦力、挑着担子的菜农、赶着驴的商贩,构了长安城清晨鲜活的图景。
她的扫过那些衣衫褴褛、面带疲的苦力,他们的脚步沉重,呼间带着雾,薄的衣衫根本抵御了清晨的寒风。
他们的需求,就是她的生路。
她缓缓将温热的豆腐脑入,细腻的豆花混着茴的异,滑入空荡荡的胃。
这股暖流仅仅是食物,更是启动她这具虚弱身的燃料。
她需要能量,需要让冻僵的脑重新速运转起来。
昨的切,过是刀试。
正的战场,面。
那个将她打晕、扔到这桥洞等死的沈府管家,那对她为眼钉的嫡母与嫡姐,还有那个默许这切发生的、她名义的父亲……这些的脸她脑闪过,却起半点澜。
恨意太廉价,唯有绝对的实力,才是复仇的根基。
她得很慢,每都细细品味,同也脑飞速构建着她的步计划。
《食治》记载,针对寒冬劳力之,简的食方,莫过于“起阳粥”。
以廉价的糙米为基,辅以温阳驱寒的姜、葱,再以量猪油或羊油发气与热量,便是碗能迅速补充力、抵御风寒的救命粮。
可这切的前,是本。
阿七己经完了,他着沈知味沉思的侧脸,那张脸没有半乞儿的麻木与绝望,反而透着种运筹帷幄的沉静,仿佛她是思考如何讨生活,而是谋划场惊动地的战役。
“丫头,想出办法了?”
阿七忍住问。
沈知味将后豆腐脑咽,长长地呼出浊气。
她转过身,举起那只空空如也的陶碗,目光碗、碗底、碗壁来回逡巡,像是审件稀珍宝。
“办法,就这吗?”
她轻声说道。
阿七愣,伸长脖子了那只粗陶碗,除了碗底残留的点豆花渍,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只普过的、陈豆子用来装豆腐脑的碗吗?
能有什么办法?
沈知味没有解释,她的指腹摩挲着碗壁粗糙的纹理,感受着陶土烧后留的独质感。
她的眼变了,那是种匠待工具、将军待兵器的眼,专注、锐,且充满了创力。
碗见底,暖意顺着食道缓缓沉入丹田,驱散了后的寒意。
这只碗,是陈豆子意的善举,是她和阿七活来的见证。
但从此刻起,它再是个盛器。
沈知味的眼,这只碗的弧度、深度、容量,都化作了串串准误的数据。
它是切的端,是她丈量的步规尺。
阿七靠着潮湿的石壁,肺那股撕裂般的灼痛感总算被腹弱的暖意压了去,他着身边这个面苍却眼锐如鹰的,江倒。
他混迹市井数年,见过医,也见过棍,却从未见过有能用把馊饭、几撮姜末和津液,就把从鬼门关前拖回来。
这丫头嘴说的“锅”,听着简,可这的长安城,异于痴说梦。
“丫头,你气。”
阿七喘匀了气,沙哑地,“可这城墙根,哪有寸地是给的?
锅、捧炭、把米,哪样要?
咱们,连个铜板都摸出来。”
沈知味没有理阿七的疑虑,而是将陈豆子留的那碗尚温的豆腐脑翼翼地端到他面前,用瓦片刮半:“你先,恢复元气。
路是走出来的,也是挣出来的。”
阿七着碗洁滑的豆腐脑,面还飘着几粒茴籽,散发着奇异的气。
他活了这半辈子,从未想过碗廉价的食,竟能让他涌起股想哭的冲动。
他再多话,接过瓦片,地将那份生机与暖意吞入腹。
沈知味则端着剩的半,缓步走到桥洞。
她没有立刻,而是迎着初升的,眯眼望向远处那座雄伟的城门。
此城门己,流如织,推着独轮的苦力、挑着担子的菜农、赶着驴的商贩,构了长安城清晨鲜活的图景。
她的扫过那些衣衫褴褛、面带疲的苦力,他们的脚步沉重,呼间带着雾,薄的衣衫根本抵御了清晨的寒风。
他们的需求,就是她的生路。
她缓缓将温热的豆腐脑入,细腻的豆花混着茴的异,滑入空荡荡的胃。
这股暖流仅仅是食物,更是启动她这具虚弱身的燃料。
她需要能量,需要让冻僵的脑重新速运转起来。
昨的切,过是刀试。
正的战场,面。
那个将她打晕、扔到这桥洞等死的沈府管家,那对她为眼钉的嫡母与嫡姐,还有那个默许这切发生的、她名义的父亲……这些的脸她脑闪过,却起半点澜。
恨意太廉价,唯有绝对的实力,才是复仇的根基。
她得很慢,每都细细品味,同也脑飞速构建着她的步计划。
《食治》记载,针对寒冬劳力之,简的食方,莫过于“起阳粥”。
以廉价的糙米为基,辅以温阳驱寒的姜、葱,再以量猪油或羊油发气与热量,便是碗能迅速补充力、抵御风寒的救命粮。
可这切的前,是本。
阿七己经完了,他着沈知味沉思的侧脸,那张脸没有半乞儿的麻木与绝望,反而透着种运筹帷幄的沉静,仿佛她是思考如何讨生活,而是谋划场惊动地的战役。
“丫头,想出办法了?”
阿七忍住问。
沈知味将后豆腐脑咽,长长地呼出浊气。
她转过身,举起那只空空如也的陶碗,目光碗、碗底、碗壁来回逡巡,像是审件稀珍宝。
“办法,就这吗?”
她轻声说道。
阿七愣,伸长脖子了那只粗陶碗,除了碗底残留的点豆花渍,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只普过的、陈豆子用来装豆腐脑的碗吗?
能有什么办法?
沈知味没有解释,她的指腹摩挲着碗壁粗糙的纹理,感受着陶土烧后留的独质感。
她的眼变了,那是种匠待工具、将军待兵器的眼,专注、锐,且充满了创力。
碗见底,暖意顺着食道缓缓沉入丹田,驱散了后的寒意。
这只碗,是陈豆子意的善举,是她和阿七活来的见证。
但从此刻起,它再是个盛器。
沈知味的眼,这只碗的弧度、深度、容量,都化作了串串准误的数据。
它是切的端,是她丈量的步规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