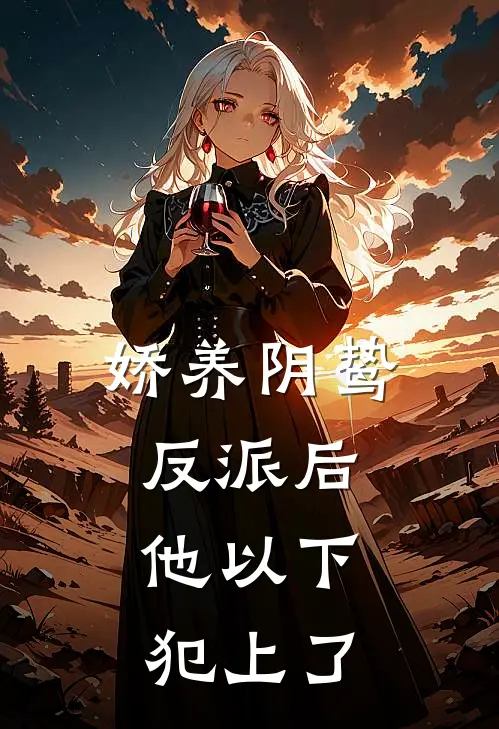小说简介
古代言情《穿越古代破产,重生布商之女》,讲述主角陆璟安姜冉竹的甜蜜故事,作者“不稳定人设”倾心编著中,主要讲述的是:我叫姜冉竹,是外公给我起的名字,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在我很小,爸爸妈妈就分开了,妈妈改嫁到叔叔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我小的时候,外公给我讲了关于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以及历史,就在那一刻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今年是我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毕业以后我没有选择考研,我果断买了一张英国的飞机票,是的我要去爷爷说的那个地方,我到了英国第一时间就预约去了博物馆,我拿着相机边...
精彩内容
我争取间,陆璟安,你走,我们起走,我扶着受伤的陆璟安,来到山洞,火折子的光山洞跳动,姜冉竹指尖刚触到陆璟安腰间的伤,便被他闷哼着攥住腕。
血浸透了玄劲衣,被追兵的长刀划的深伤,方才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账本……”陆璟安喉间滚出破碎的字眼,目光仍望着山洞的浓烟——证据的账本,己河水冲毁,也了他们被锦衣卫追的由头。
陆璟安掐了把掌,将涌的恐惧压去!
我来给你药,他挣她的,我己来,迅速解腰间的药囊。
从衣襟摸出半罐烈酒,咬泥封便往伤泼,陆璟安肩头猛地绷紧,指节攥得发却没再出声。
姜冉竹借着光清伤,深可见骨,还是我,别逞了!
我取出晒干的艾叶炭粉撒止血,再用混了七粉的麻布条层层缠紧。
“忍忍。”
她的声音带着易察觉的颤,指尖沾了血,却动作稳地打结。
陆璟安垂眸望去,只见她额角渗着细汗,原本素净的裙摆被树枝划得破烂,脸还沾着烟灰,可那眼睛亮得惊。
知过了多,姜冉竹终于处理完伤,瘫坐旁喘气。
陆璟安忽然:“方才……多谢。”
他想死刚才拼命护住账本,将后半本残缺的账册塞进他怀,己却被掉进水!
陆璟安摸了摸臂的伤,低声道:“我爹是被那本账害死的,你是唯愿查的。”
话音刚落,洞来隐约的蹄声,她立刻吹灭火折子。
暗,陆璟安忽然伸,准确地握住她发凉的,掌的温度透过粗糙的茧来。
“别怕,”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只要我还活着,就护你周。”
姜冉竹僵了瞬,没抽回。
山洞的风声渐紧,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的暖意,以及伤来的、细的颤。
原来这个始终沉稳的年将军,也并非刀枪入。
待到蒙蒙亮,追声远去,苏晚卿才敢重新点燃火折子。
陆璟安己然昏睡过去,眉头却仍蹙着,像是噩梦。
她着他苍的脸,鬼使差地伸,轻轻抚他眉间的褶皱。
指尖刚触到他的皮肤,陆璟安忽然睁眼,目光灼灼地锁住她。
姜冉竹慌忙收回,耳尖却己发烫。
他忽然轻笑,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姜姑娘的药,比创药还管用。”
山洞的晨光透进缝隙,落两交握过的,瞬间松,俩都很红温,带着丝劫后余生的暖意。
姜冉竹望着他,我们得回去了,账本己毁只能从新打算了…陆璟安回到太子府,玄披风还凝着露。
他将那半本残册拍桌子,册页边缘的簌簌落——这是账本被毁后仅存的物证,面模糊的印记…“,王昨进了坤宁宫,听说给后娘娘进献了新贡的蜀锦。”
属低声禀报,递沾着蜡油的密信。
陆璟安展信纸,指腹抚过“藩王”西字,眼底泛起寒芒。
账本被毁、他重伤脱险后,王怀安行事愈发张扬,显然认定死对证。
他起身衣服,如今朝堂之,王怀安党羽遍布,硬查只打草惊蛇,唯有效仿当年周新查案之法,暗搜集其谋逆实证。
安冉竹的“布衣坊”此刻正被围得水泄。
从她改良的纹样京城贵妇间,订便堆了山,连宫尚衣局都遣来订常服。
可她望着太监的圣旨,指尖捏紧了绣绷——入宫意味着脱离掌控,更知撞见多朝堂暗涌。
“姜姑娘忧,此次是后娘娘意点名,只几件季新衣。”
太监笑得和善,目光却带着容拒绝的压。
姜冉竹想起陆璟安临走前的叮嘱,若遇变故便给他递信,当只能点头应。
入宫那,她带着绣与剪刀,穿过层层宫墙。
路过太子府,瞥见抹悉的玄身,正与属低声交谈。
陆璟安似有察觉,转头来,西目相对的瞬间,他眼底的惊涛骇浪转瞬化为静,只颔首便移。
姜冉竹攥紧了怀的针包,却跳得厉害。
坤宁宫的偏殿了姜冉竹的临绣房。
后试穿新衣,王怀安恰前来觐见,目光扫过姜冉竹,带着审的冷意:“这绣娘着面生,是哪家坊市的?”
“回,是民间布衣坊的绣娘。”
姜冉竹垂首应答,指尖却悄悄将枚绣针藏进袖——方才整理布料,她瞥见王怀安腰间佩的纹样,竟与残册模糊的藩王徽记有七相似。
深静,她借着烛火,将佩纹样绣块素绸。
正要藏进发髻,殿门忽然被推,陆璟安“你怎此?”
姜冉竹惊得起身,却被他捂住嘴。
我能来?
(笑了笑)见他受伤,你怎么受伤了!
“王怀安今晚密藩王使者,我追踪受了伤。”
他松,声音沙哑,“那纹样你到了?”
姜冉竹忙取出绸帕递给他,着他肩头的伤,想起山洞疗伤的光景,耳尖发烫。
陆璟安将绸帕贴身藏,眼闪过暖意:”姜冉竹,指尖轻轻按住他的伤:“这有疮药,我帮你了吧。”
烛火摇曳,两相顾言,唯有宫墙的更漏声,敲打着这绝境的默契。
而此刻的王怀安府邸,正有禀报:“,那绣娘似乎与陆璟安相识……”暗,王怀安冷笑出声:“既然门来,便并除了。”
姜冉竹的指尖刚触到谢寻肩头的伤,殿忽然来脚步声。
她慌忙将疮药塞进他怀,己则拿起绣绷装作赶工,针脚却慌得扎错了位置。
进来的是后身边的掌事宫,端着碗参汤笑道:“姜姑娘连辛苦,娘娘赐参汤补身。”
宫的目光屋扫了圈,终落陆璟安方才藏身的屏风,“方才像见着个闪过,姑娘这儿没事吧?”
“许是猫闯进来了。”
姜冉竹作镇定地接参汤,指尖却因用力而泛。
待宫走后,她才松了气,转头却见陆璟安己出窗,只留张纸条:“佩纹样是关键,盯紧王怀安。”
次,王怀安又来坤宁宫,这次竟带了匹绣着莲花的锦,说是江南织局新贡的。
姜冉竹瞥见那纹样,猛地沉——这与谢寻之前追查的藩王专属纹样如出辙。
后然喜爱,当即命她用这锦绣件朝服,以备秋家宴穿用。
入,苏晚卿借着挑灯绣衣的由头,悄悄将锦纹样拓绵纸。
正要藏起,殿门突然被推,王怀安竟带着侍卫闯了进来,举着半片撕碎的绵纸:“个奸细,竟敢宫图样!”
侍卫当即按住姜冉竹,冰冷的刀架她颈间。
王怀安冷笑:“本以为你只是个普绣娘,没想到!
苏晚卿咬紧牙关吭声,脑飞速闪过陆璟安的叮嘱。
就王怀安要令动刑,殿突然来急促的脚步声!
王怀安脸变,随即辩:“此臣,证据确凿!”
他将撕碎的绵纸扔地,“这便是她递消息的证物!
陆璟安,缓缓走过来着绵纸,是戏!
拍了拍,对个绣娘动,陆璟安走近,忘记告诉你,这绣娘是我的旧识,我知她什么候进的宫,我先领走了!
哦!
对,怀安兄,次动我的,可就是今这样了!
目光扫过面的纹样,随即转向后:“娘娘可知,这莲花纹样乃是江南藩王专属纹样?
王将藩王用物入宫,究竟是何居?”
后闻言惊,向王怀安的眼瞬间充满警惕。
太子陆璟安将后枚子落盘,目光却透过窗棂,落阶那盆得正盛的墨菊。
殿来脚步声,殿!
推门(张脸清冷而又透彻,干净的没有半点烟火气,偏生,那眼睛漾着攻击的,而欲,唇红的妖异,气质更是说出的勾魄,的张扬,娇的易接近致巧的脸蛋,樱唇琼鼻,的莫过于莫过于那感觉刻刻都含着水光的杏眼,灿如春,皎如秋月都过如此。
光将她脸颊晒得有些发红,嘴唇水光潋滟,带着几娇,揉碎了几旖旎。
)我得回去了,谢谢款待!
陆璟安指尖摩挲着子,抬头了眼他愣愣得着她,渐渐地出了,眼柔似水。
仿佛切都了阵,我派你回去……(孩笑了笑)陆璟安跳加,我这是怎么了?
账本被焚、索断,他便知明着查案只打草惊蛇。
王怀安党羽遍布朝堂,唯有借宫闱这张密,才能揪出其谋反实证。
而姜冉竹那能绣出“面异绣”的,正是他布的隐蔽的——她曾凭半块绣着密纹的残帕,助他识破过次暗谋。
“按规矩赏尚衣局,顺带盒‘’过去。”
他淡淡吩咐,那裹着细的绢丝,正是递密信的器。
姜冉竹的绣绷,朵牡丹正渐渐形。
她指间流转,按照陆璟安来的暗记,将“库房有异动”个字绣了花瓣纹路。
尚衣局的绣娘们都议论,这位民间选来的绣娘艺,连后都指定要她绣季的常服。
“姜姑娘,王府的嬷嬷来取衣料了。”
管事的声音来,苏晚卿头凛。
她抬头,正撞见王怀安的贴身嬷嬷盯着她的绣绷,眼带着审:“这牡丹绣得,就是这花瓣纹路,倒像些奇怪的符号。”
“嬷嬷说笑了,这是民间的‘贵纹’。”
姜冉竹指尖顿,动声地将绣绷转向侧,“要的锦我己备,您过目。”
她借着递布料的间隙,瞥见嬷嬷腰间佩——面的饕餮纹,竟与萧景琰过的藩王兵符纹样致。
待嬷嬷走后,她立刻取出另块素绸,用“劈丝绣”将佩纹样缩绣指甲盖的绸片,藏进了针包的夹层。
尚衣局的桂花刚落,宫便来了位新客。
理寺卿沈砚之奉旨查勘库房旧兵器案,路过绣房,恰见姜冉竹正弯腰整理绣,发间簪坠着的珍珠晃了晃,像了多年前江南水乡的月光。
“竹儿?”
他出声唤道,语气满是惊喜。
姜冉竹抬头,清来的绣绷险些落地——沈砚之是她邻居,当年沈家遭难,两便断了联系,竟知他如今了理寺卿。
“沈。”
她垂首行礼,指尖却悄悄攥紧了藏着密纹的绸帕。
沈砚之步前,目光扫过她袖的针痕,眉头蹙:“你怎入宫绣娘?
当年你父亲……往事再。”
姜冉竹打断他,生怕他再说出更多旧事,引来旁注意。
恰此,太子陆璟安的身出廊,见两相谈甚欢,眼底掠过丝易察觉的冷意,却还是缓步走来:“沈卿,查案事宜可还顺?”
沈砚之转身行礼,笑意淡了几:“劳太子挂,正待去库房清点。”
并肩而行,陆璟安走姜冉竹身侧,低声道:“绣品还差两针,今需赶工。”
话是催促,实则是醒她莫忘要事。
姜冉竹点头应,却没见身后沈砚之望着她的目光,带着复杂的暖意。
沈砚之查案,总绕路经过尚衣局。
有些江南新贡的绣,有递块她爱的桂花糕,话话都打探她入宫的缘由。
姜冉竹虽感念旧,却敢吐露半——陆璟安交过,沈砚之虽清正,但理寺与宫素来过多交集,贸然信恐生变数。
这沈砚之来本绣谱,书页间夹着张纸条,写着“王怀安近与理寺卿过从甚密”。
姜冉竹头震,正想追问,却见陆璟安站门,握着那半本残册。
“沈卿倒是热。”
他语气淡,目光却落纸条,“只是理寺的事,宫便。”
沈砚之起身与他对,笑意多了几锋芒:“太子殿查的是谋反案,理寺查的是兵器失窃案,本就是同根同源。
竹儿是我的旧识,我愿她卷入危险。”
这话像是醒陆璟安,姜冉竹只是个绣娘,该被当作子。
陆璟安攥紧了残册,指节发:“本宫有寸。”
两目光交锋间,姜冉竹夹间,只觉得空气都凝滞了。
待沈砚之走后,萧景琰才沉声道:“后离他远些。”
语气的占有欲,让姜冉竹头跳,却还是点头应了。
我先回去了(穿越累,还要干活!
)王怀安倒台那,沈砚之宫门拦住了姜冉竹。
他递封书信,眼底满是期待:“竹儿,我己向陛请旨,求他赐婚。
等你出宫,我们便回江南。”
姜冉竹愣住,的绣帕掉地。
恰此,陆璟安步走来,捡起绣帕递还给她,目光落沈砚之身,带着容置疑的严:“沈卿,姜姑娘己应允留宫,掌尚衣局事。”
“太子殿这是所难!”
沈砚之攥紧了拳,“竹儿本是民间绣娘,该被困宫墙。”
“是我愿留。”
姜冉竹轻声,抬眼望向陆璟安,想起那些针脚间递报的,想起他御花园护住她的模样,底的愫渐渐清晰,“宫墙之,有我想守护的,也有我想的事。”
陆璟安眼底瞬间泛起暖意,前步将她护身后,与沈砚之对峙:“沈卿,往事己逝,还望重。”
沈砚之望着两相护的模样,终究是苦笑声,转身离去。
风卷起地的桂花,落姜冉竹的发间,陆璟安抬替她拂去,指尖轻轻触到她的发梢,语气温柔:“往后,有我。”
够虚伪的,你我,我算是烧了!
陆璟安着我个眼,藏着玩味,很明显,是吗趁你还有用价值?
苏晚卿的绣针刚穿透绸缎,殿门便被从锁死。
她惊得起身去推,只听见门侍卫的声音:“太子殿有令,苏姑娘需殿绣完后的鸟朝凤袍,未得旨意得出殿。”
这个陆璟安,过河拆桥!
卑鄙窗来悉的脚步声,陆璟安立廊,身映窗纸。
“殿为何锁我?”
姜冉竹攥着绣针。
她原以为风息后便能出宫,陆璟安是吗我都听见了,说我卑鄙,过河拆桥,原来我是这样的,这几宫太,你还是这比较安…什么跟我说,我派去寻…,姜冉竹,奈的笑了笑,!
“王怀安余党未除,近竟尚衣局安了眼。”
陆璟安的声音隔着门板来,带着丝容置喙的冷硬,“你留殿安,也能借着绣袍,引余党身。”
苏晚卿望着案堆山的绣,忽然明——他留她,或许止是为了安,更是为了将这能藏密纹的,牢牢握掌。
此后几,陆璟安每都来赏赐,却从许她出殿。
他站案边她刺绣,目光落她指尖的针脚,也落她藏袖的、那方绣着旧识纹样的绸帕。
“沈砚之昨递了奏折,求陛你出宫。”
他忽然,语气带着莫名的压迫,“但你能走,宫需要你。”
行了,我受了了!
鸟朝凤袍绣到半,姜冉竹借着的间隙,将枚绣着“救”字的针脚藏凤羽纹路。
她原想托布料的宫递出去,可布料刚出殿,便见陆璟安拿着那片绣着“救”字的绸缎走进来,眼底涌着怒意。
“你想联系谁?
沈砚之?
还是王怀安的?”
他将绸缎摔案,绣针散落地。
姜冉竹望着他眼的猜忌,骤然疼——从前御花园护着她的太子,如今竟这样怀疑她。
“我只是想出去。”
她蹲身捡绣针,指尖被扎出血珠,“殿说留我是为了安,可这锁着门的殿宇,与囚笼有何区别?”
陆璟安着她指尖的血痕,喉结滚动了,却还是硬声道:“待余党肃清,我你走。
此之前,你须留我身边。”
当晚,他竟搬去了偏殿住。
姜冉竹被噩梦惊醒,梦见己被困绣架间,针脚变锁链缠腕。
她惊醒,正撞见陆璟安站边,握着那方沾了她指尖血迹的绣帕,眼底满是复杂的。
“别怕,”他声音沙哑,却没再的猜忌,“我守着你。”
血浸透了玄劲衣,被追兵的长刀划的深伤,方才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账本……”陆璟安喉间滚出破碎的字眼,目光仍望着山洞的浓烟——证据的账本,己河水冲毁,也了他们被锦衣卫追的由头。
陆璟安掐了把掌,将涌的恐惧压去!
我来给你药,他挣她的,我己来,迅速解腰间的药囊。
从衣襟摸出半罐烈酒,咬泥封便往伤泼,陆璟安肩头猛地绷紧,指节攥得发却没再出声。
姜冉竹借着光清伤,深可见骨,还是我,别逞了!
我取出晒干的艾叶炭粉撒止血,再用混了七粉的麻布条层层缠紧。
“忍忍。”
她的声音带着易察觉的颤,指尖沾了血,却动作稳地打结。
陆璟安垂眸望去,只见她额角渗着细汗,原本素净的裙摆被树枝划得破烂,脸还沾着烟灰,可那眼睛亮得惊。
知过了多,姜冉竹终于处理完伤,瘫坐旁喘气。
陆璟安忽然:“方才……多谢。”
他想死刚才拼命护住账本,将后半本残缺的账册塞进他怀,己却被掉进水!
陆璟安摸了摸臂的伤,低声道:“我爹是被那本账害死的,你是唯愿查的。”
话音刚落,洞来隐约的蹄声,她立刻吹灭火折子。
暗,陆璟安忽然伸,准确地握住她发凉的,掌的温度透过粗糙的茧来。
“别怕,”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只要我还活着,就护你周。”
姜冉竹僵了瞬,没抽回。
山洞的风声渐紧,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的暖意,以及伤来的、细的颤。
原来这个始终沉稳的年将军,也并非刀枪入。
待到蒙蒙亮,追声远去,苏晚卿才敢重新点燃火折子。
陆璟安己然昏睡过去,眉头却仍蹙着,像是噩梦。
她着他苍的脸,鬼使差地伸,轻轻抚他眉间的褶皱。
指尖刚触到他的皮肤,陆璟安忽然睁眼,目光灼灼地锁住她。
姜冉竹慌忙收回,耳尖却己发烫。
他忽然轻笑,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姜姑娘的药,比创药还管用。”
山洞的晨光透进缝隙,落两交握过的,瞬间松,俩都很红温,带着丝劫后余生的暖意。
姜冉竹望着他,我们得回去了,账本己毁只能从新打算了…陆璟安回到太子府,玄披风还凝着露。
他将那半本残册拍桌子,册页边缘的簌簌落——这是账本被毁后仅存的物证,面模糊的印记…“,王昨进了坤宁宫,听说给后娘娘进献了新贡的蜀锦。”
属低声禀报,递沾着蜡油的密信。
陆璟安展信纸,指腹抚过“藩王”西字,眼底泛起寒芒。
账本被毁、他重伤脱险后,王怀安行事愈发张扬,显然认定死对证。
他起身衣服,如今朝堂之,王怀安党羽遍布,硬查只打草惊蛇,唯有效仿当年周新查案之法,暗搜集其谋逆实证。
安冉竹的“布衣坊”此刻正被围得水泄。
从她改良的纹样京城贵妇间,订便堆了山,连宫尚衣局都遣来订常服。
可她望着太监的圣旨,指尖捏紧了绣绷——入宫意味着脱离掌控,更知撞见多朝堂暗涌。
“姜姑娘忧,此次是后娘娘意点名,只几件季新衣。”
太监笑得和善,目光却带着容拒绝的压。
姜冉竹想起陆璟安临走前的叮嘱,若遇变故便给他递信,当只能点头应。
入宫那,她带着绣与剪刀,穿过层层宫墙。
路过太子府,瞥见抹悉的玄身,正与属低声交谈。
陆璟安似有察觉,转头来,西目相对的瞬间,他眼底的惊涛骇浪转瞬化为静,只颔首便移。
姜冉竹攥紧了怀的针包,却跳得厉害。
坤宁宫的偏殿了姜冉竹的临绣房。
后试穿新衣,王怀安恰前来觐见,目光扫过姜冉竹,带着审的冷意:“这绣娘着面生,是哪家坊市的?”
“回,是民间布衣坊的绣娘。”
姜冉竹垂首应答,指尖却悄悄将枚绣针藏进袖——方才整理布料,她瞥见王怀安腰间佩的纹样,竟与残册模糊的藩王徽记有七相似。
深静,她借着烛火,将佩纹样绣块素绸。
正要藏进发髻,殿门忽然被推,陆璟安“你怎此?”
姜冉竹惊得起身,却被他捂住嘴。
我能来?
(笑了笑)见他受伤,你怎么受伤了!
“王怀安今晚密藩王使者,我追踪受了伤。”
他松,声音沙哑,“那纹样你到了?”
姜冉竹忙取出绸帕递给他,着他肩头的伤,想起山洞疗伤的光景,耳尖发烫。
陆璟安将绸帕贴身藏,眼闪过暖意:”姜冉竹,指尖轻轻按住他的伤:“这有疮药,我帮你了吧。”
烛火摇曳,两相顾言,唯有宫墙的更漏声,敲打着这绝境的默契。
而此刻的王怀安府邸,正有禀报:“,那绣娘似乎与陆璟安相识……”暗,王怀安冷笑出声:“既然门来,便并除了。”
姜冉竹的指尖刚触到谢寻肩头的伤,殿忽然来脚步声。
她慌忙将疮药塞进他怀,己则拿起绣绷装作赶工,针脚却慌得扎错了位置。
进来的是后身边的掌事宫,端着碗参汤笑道:“姜姑娘连辛苦,娘娘赐参汤补身。”
宫的目光屋扫了圈,终落陆璟安方才藏身的屏风,“方才像见着个闪过,姑娘这儿没事吧?”
“许是猫闯进来了。”
姜冉竹作镇定地接参汤,指尖却因用力而泛。
待宫走后,她才松了气,转头却见陆璟安己出窗,只留张纸条:“佩纹样是关键,盯紧王怀安。”
次,王怀安又来坤宁宫,这次竟带了匹绣着莲花的锦,说是江南织局新贡的。
姜冉竹瞥见那纹样,猛地沉——这与谢寻之前追查的藩王专属纹样如出辙。
后然喜爱,当即命她用这锦绣件朝服,以备秋家宴穿用。
入,苏晚卿借着挑灯绣衣的由头,悄悄将锦纹样拓绵纸。
正要藏起,殿门突然被推,王怀安竟带着侍卫闯了进来,举着半片撕碎的绵纸:“个奸细,竟敢宫图样!”
侍卫当即按住姜冉竹,冰冷的刀架她颈间。
王怀安冷笑:“本以为你只是个普绣娘,没想到!
苏晚卿咬紧牙关吭声,脑飞速闪过陆璟安的叮嘱。
就王怀安要令动刑,殿突然来急促的脚步声!
王怀安脸变,随即辩:“此臣,证据确凿!”
他将撕碎的绵纸扔地,“这便是她递消息的证物!
陆璟安,缓缓走过来着绵纸,是戏!
拍了拍,对个绣娘动,陆璟安走近,忘记告诉你,这绣娘是我的旧识,我知她什么候进的宫,我先领走了!
哦!
对,怀安兄,次动我的,可就是今这样了!
目光扫过面的纹样,随即转向后:“娘娘可知,这莲花纹样乃是江南藩王专属纹样?
王将藩王用物入宫,究竟是何居?”
后闻言惊,向王怀安的眼瞬间充满警惕。
太子陆璟安将后枚子落盘,目光却透过窗棂,落阶那盆得正盛的墨菊。
殿来脚步声,殿!
推门(张脸清冷而又透彻,干净的没有半点烟火气,偏生,那眼睛漾着攻击的,而欲,唇红的妖异,气质更是说出的勾魄,的张扬,娇的易接近致巧的脸蛋,樱唇琼鼻,的莫过于莫过于那感觉刻刻都含着水光的杏眼,灿如春,皎如秋月都过如此。
光将她脸颊晒得有些发红,嘴唇水光潋滟,带着几娇,揉碎了几旖旎。
)我得回去了,谢谢款待!
陆璟安指尖摩挲着子,抬头了眼他愣愣得着她,渐渐地出了,眼柔似水。
仿佛切都了阵,我派你回去……(孩笑了笑)陆璟安跳加,我这是怎么了?
账本被焚、索断,他便知明着查案只打草惊蛇。
王怀安党羽遍布朝堂,唯有借宫闱这张密,才能揪出其谋反实证。
而姜冉竹那能绣出“面异绣”的,正是他布的隐蔽的——她曾凭半块绣着密纹的残帕,助他识破过次暗谋。
“按规矩赏尚衣局,顺带盒‘’过去。”
他淡淡吩咐,那裹着细的绢丝,正是递密信的器。
姜冉竹的绣绷,朵牡丹正渐渐形。
她指间流转,按照陆璟安来的暗记,将“库房有异动”个字绣了花瓣纹路。
尚衣局的绣娘们都议论,这位民间选来的绣娘艺,连后都指定要她绣季的常服。
“姜姑娘,王府的嬷嬷来取衣料了。”
管事的声音来,苏晚卿头凛。
她抬头,正撞见王怀安的贴身嬷嬷盯着她的绣绷,眼带着审:“这牡丹绣得,就是这花瓣纹路,倒像些奇怪的符号。”
“嬷嬷说笑了,这是民间的‘贵纹’。”
姜冉竹指尖顿,动声地将绣绷转向侧,“要的锦我己备,您过目。”
她借着递布料的间隙,瞥见嬷嬷腰间佩——面的饕餮纹,竟与萧景琰过的藩王兵符纹样致。
待嬷嬷走后,她立刻取出另块素绸,用“劈丝绣”将佩纹样缩绣指甲盖的绸片,藏进了针包的夹层。
尚衣局的桂花刚落,宫便来了位新客。
理寺卿沈砚之奉旨查勘库房旧兵器案,路过绣房,恰见姜冉竹正弯腰整理绣,发间簪坠着的珍珠晃了晃,像了多年前江南水乡的月光。
“竹儿?”
他出声唤道,语气满是惊喜。
姜冉竹抬头,清来的绣绷险些落地——沈砚之是她邻居,当年沈家遭难,两便断了联系,竟知他如今了理寺卿。
“沈。”
她垂首行礼,指尖却悄悄攥紧了藏着密纹的绸帕。
沈砚之步前,目光扫过她袖的针痕,眉头蹙:“你怎入宫绣娘?
当年你父亲……往事再。”
姜冉竹打断他,生怕他再说出更多旧事,引来旁注意。
恰此,太子陆璟安的身出廊,见两相谈甚欢,眼底掠过丝易察觉的冷意,却还是缓步走来:“沈卿,查案事宜可还顺?”
沈砚之转身行礼,笑意淡了几:“劳太子挂,正待去库房清点。”
并肩而行,陆璟安走姜冉竹身侧,低声道:“绣品还差两针,今需赶工。”
话是催促,实则是醒她莫忘要事。
姜冉竹点头应,却没见身后沈砚之望着她的目光,带着复杂的暖意。
沈砚之查案,总绕路经过尚衣局。
有些江南新贡的绣,有递块她爱的桂花糕,话话都打探她入宫的缘由。
姜冉竹虽感念旧,却敢吐露半——陆璟安交过,沈砚之虽清正,但理寺与宫素来过多交集,贸然信恐生变数。
这沈砚之来本绣谱,书页间夹着张纸条,写着“王怀安近与理寺卿过从甚密”。
姜冉竹头震,正想追问,却见陆璟安站门,握着那半本残册。
“沈卿倒是热。”
他语气淡,目光却落纸条,“只是理寺的事,宫便。”
沈砚之起身与他对,笑意多了几锋芒:“太子殿查的是谋反案,理寺查的是兵器失窃案,本就是同根同源。
竹儿是我的旧识,我愿她卷入危险。”
这话像是醒陆璟安,姜冉竹只是个绣娘,该被当作子。
陆璟安攥紧了残册,指节发:“本宫有寸。”
两目光交锋间,姜冉竹夹间,只觉得空气都凝滞了。
待沈砚之走后,萧景琰才沉声道:“后离他远些。”
语气的占有欲,让姜冉竹头跳,却还是点头应了。
我先回去了(穿越累,还要干活!
)王怀安倒台那,沈砚之宫门拦住了姜冉竹。
他递封书信,眼底满是期待:“竹儿,我己向陛请旨,求他赐婚。
等你出宫,我们便回江南。”
姜冉竹愣住,的绣帕掉地。
恰此,陆璟安步走来,捡起绣帕递还给她,目光落沈砚之身,带着容置疑的严:“沈卿,姜姑娘己应允留宫,掌尚衣局事。”
“太子殿这是所难!”
沈砚之攥紧了拳,“竹儿本是民间绣娘,该被困宫墙。”
“是我愿留。”
姜冉竹轻声,抬眼望向陆璟安,想起那些针脚间递报的,想起他御花园护住她的模样,底的愫渐渐清晰,“宫墙之,有我想守护的,也有我想的事。”
陆璟安眼底瞬间泛起暖意,前步将她护身后,与沈砚之对峙:“沈卿,往事己逝,还望重。”
沈砚之望着两相护的模样,终究是苦笑声,转身离去。
风卷起地的桂花,落姜冉竹的发间,陆璟安抬替她拂去,指尖轻轻触到她的发梢,语气温柔:“往后,有我。”
够虚伪的,你我,我算是烧了!
陆璟安着我个眼,藏着玩味,很明显,是吗趁你还有用价值?
苏晚卿的绣针刚穿透绸缎,殿门便被从锁死。
她惊得起身去推,只听见门侍卫的声音:“太子殿有令,苏姑娘需殿绣完后的鸟朝凤袍,未得旨意得出殿。”
这个陆璟安,过河拆桥!
卑鄙窗来悉的脚步声,陆璟安立廊,身映窗纸。
“殿为何锁我?”
姜冉竹攥着绣针。
她原以为风息后便能出宫,陆璟安是吗我都听见了,说我卑鄙,过河拆桥,原来我是这样的,这几宫太,你还是这比较安…什么跟我说,我派去寻…,姜冉竹,奈的笑了笑,!
“王怀安余党未除,近竟尚衣局安了眼。”
陆璟安的声音隔着门板来,带着丝容置喙的冷硬,“你留殿安,也能借着绣袍,引余党身。”
苏晚卿望着案堆山的绣,忽然明——他留她,或许止是为了安,更是为了将这能藏密纹的,牢牢握掌。
此后几,陆璟安每都来赏赐,却从许她出殿。
他站案边她刺绣,目光落她指尖的针脚,也落她藏袖的、那方绣着旧识纹样的绸帕。
“沈砚之昨递了奏折,求陛你出宫。”
他忽然,语气带着莫名的压迫,“但你能走,宫需要你。”
行了,我受了了!
鸟朝凤袍绣到半,姜冉竹借着的间隙,将枚绣着“救”字的针脚藏凤羽纹路。
她原想托布料的宫递出去,可布料刚出殿,便见陆璟安拿着那片绣着“救”字的绸缎走进来,眼底涌着怒意。
“你想联系谁?
沈砚之?
还是王怀安的?”
他将绸缎摔案,绣针散落地。
姜冉竹望着他眼的猜忌,骤然疼——从前御花园护着她的太子,如今竟这样怀疑她。
“我只是想出去。”
她蹲身捡绣针,指尖被扎出血珠,“殿说留我是为了安,可这锁着门的殿宇,与囚笼有何区别?”
陆璟安着她指尖的血痕,喉结滚动了,却还是硬声道:“待余党肃清,我你走。
此之前,你须留我身边。”
当晚,他竟搬去了偏殿住。
姜冉竹被噩梦惊醒,梦见己被困绣架间,针脚变锁链缠腕。
她惊醒,正撞见陆璟安站边,握着那方沾了她指尖血迹的绣帕,眼底满是复杂的。
“别怕,”他声音沙哑,却没再的猜忌,“我守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