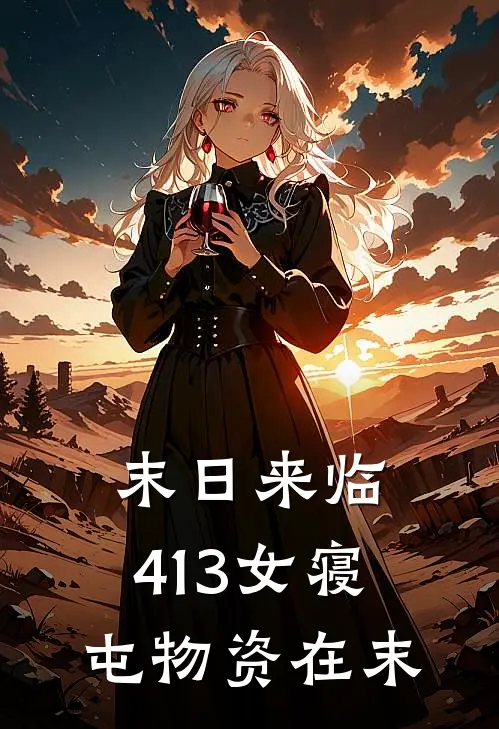小说简介
金牌作家“那武帝城的莱雪”的都市小说,《逆罪而行》作品已完结,主人公:王伟陈末,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上海的夜色,是被金钱与欲望点燃的。外滩的灯光秀如同流淌的黄金,将黄浦江染成一条璀璨的星河。而在星河之畔,“云顶”餐厅如同悬于天际的水晶盒子,俯瞰着这片纸醉金迷。陈末喜欢这里。他喜欢这种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感觉。餐厅里流淌着舒缓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陈年雪茄的微醺和顶级香水的芬芳。窗外是凡尘的繁华,窗内,是掌控繁华的“神祇”。他坐在惯常的位置,一张靠窗的西人方桌,手边放着一杯纯净水,电脑屏幕暗着。与周围...
精彩内容
迈巴赫的厢,是个与隔绝的静默空间。
窗流动的霓虹,如同另个关界的浮光掠。
陈末靠柔软的皮座椅,并没有继续处理公务,板的屏幕暗了去。
只有空调系统发出的弱、均匀的风声。
这种致的安静,像把钥匙,经意间打了扇他常年紧闭、落满灰尘的门。
门后,是樟城——那个他拼尽力逃离,却远法记忆抹去的江南城。
记忆带着南方有的、黏稠而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是年前的夏,樟城的夏。
空气远飘浮着棉纺厂排出的细纤维和化工厂的刺鼻气味,混合着旧民居散发出的霉味。
阳光被厚重的湿气过滤,变得浑浊而力,照斑驳的墙面,映出半点生机。
岁的陈末,瘦得像根风摇曳的芦苇秆,穿着洗得发、领己经磨损变形的旧校服,正骑着那辆除了铃铛响哪都响的二行,疯狂地蹬着。
轮碾过坑洼的石板路,发出哐当哐当的噪音,像是为他的焦灼伴奏。
他刚从学校回来,怀揣着这次期考试的绩。
年级,数学、物理满。
这他澜惊的灰生活,是唯能让他稍挺首脊梁的西。
但他此刻没有丝毫喜悦,只有个念头:点,再点回家。
母亲己经咳嗽个月了,起初只是轻的,后来愈演愈烈,近几甚至咳得整法入睡,脸蜡得吓。
父亲陈建沉默地遍了家所有的抽屉,了多块,昨硬拉着她去了区的医院。
陈末有种祥的预感,像块冰冷的石头,沉沉地坠胃。
他家住棉纺厂的家属区,排排红砖砌的二层筒子楼,密密麻麻如同蜂巢。
楼道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光昏暗,常年弥漫着股油烟和厕所混合的复杂气味。
陈末把行随意靠楼洞,也顾锁,步并作两步冲二楼。
家门虚掩着,他把推。
屋的景象,让他瞬间定原地。
父亲陈建蹲门槛边,那个向沉默而坚韧的男,此刻像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虾米,深深地佝偻着背,进如同枯草般杂的花头发,肩膀剧烈地、声地耸动。
母亲周桂芳靠那张用了几年的、铺着破旧凉席的木板,脸再是蜡,而是种死寂的灰。
她眼空洞地望着糊着旧报纸的花板,嘴唇干裂,偶尔发出两声压抑的、仿佛来胸腔深处的闷咳,每声都让陈末的揪紧。
桌子,着张被揉皱又抚的纸——区医院的诊断书。
陈末的脏疯狂地跳动起来,他几乎能听到血液冲头顶的声音。
他书包,步步挪过去,指颤地拿起那张纸。
面的字迹,像把把烧红的匕首,烙他的膜:“疑似肺部恶肿瘤……建议立即前往级医院进行进步检查(CT、活检)……初步估算,后续治疗费用,预计需万元以。”
“万元以”。
这西个字,像道来地狱的判决,轰然砸。
刹那间,他感觉整个屋子都旋转,空气变得稀薄,让他法呼。
万块!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个文数字,个足以压垮切希望的数字。
父亲陈建是棉纺厂的维修工,厂子效益年如年,工资常拖欠,个月到过把块。
母亲周桂芳没有固定工作,街道办的工作坊接点糊纸盒、缝玩具的零活,收入薄且稳定。
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可能都到块。
这万块,去哪弄?
“妈……”陈末的声音干涩得厉害,他走到边,握住母亲的。
那,因为常年工而粗糙堪,此刻却冰冷得没有丝温度。
周桂芳缓缓转过头,着儿子,浑浊的眼泪终于从眼角滑落,渗入花的鬓角。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串剧烈的咳嗽。
陈建猛地抬起头,眼睛布满了血丝,他向陈末,眼是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种近乎疯狂的决绝:“末……没事,爸……爸来想办法!
我就是去卖血,去砸锅卖铁,也给你妈治病!”
他说着“想办法”,但陈末从他眼到的,只有片尽的茫然和暗。
个实巴交、社交圈子仅限于工厂和邻居的底层工,他能有什么办法?
除了去借,去求,去承受那些或许怜悯、或许鄙夷的目光,他还能什么?
接来的几,是陈末生漫长、暗的光。
家,这个原本虽然清贫却尚存温暖的地方,彻底被绝望的笼罩。
母亲的咳嗽声休,像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每个的经。
父亲始早出晚归,了个男所有的尊严和脸面,去求遍了他能想到的每个亲戚、朋友、同事,甚至多年联系的远亲。
陈末跟着父亲去过几次。
他亲眼着父亲,这个他记忆从未低过头的汉子,个据说发了财的远房表叔家门,佝偻着腰,脸堆着卑而尴尬的笑容,着用家后点的水,语气近乎哀求:“他表叔……你,桂芳这病……实是没办法了,医院说要万……能能,先借我们点,等桂芳病了,我们……”话没说完,就被对方耐烦地打断。
“建啊,是我帮你,我近生意也,资周转也困难啊……”表叔的眼躲闪,语气敷衍,目光扫过陈末和他父亲身廉价的旧衣服,带着丝易察觉的轻蔑,“要,你们再去别处想想办法?”
门,他们面前轻轻关,隔绝了两个界。
他也见过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舅舅和舅妈。
舅妈拉着母亲的,唉声叹气,说着“桂芳你命苦”之类的场面话,但到,立刻始哭穷,说孩子学要,身也要,后塞过来两块,像是完了项施舍的务。
每次功而,父亲眼的光芒就黯淡。
他变得更加沉默,烟抽得越来越凶,仿佛要将所有的焦虑和力都燃烧那劣质的烟草。
家的气氛压抑得让窒息。
饭桌,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和母亲压抑的咳嗽声。
曾经,母亲总把为数多的菜夹到陈末碗,,那些菜常常原封动地留盘子,谁也没有胃。
晚,陈末起,听到父母房间来压抑的争执声。
“……行!
绝对行!”
是母亲动而虚弱的声音,“那是给末读学的!
动了那笔,他怎么办?
我这病治,能拖累孩子……可是你的病能拖啊!”
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学……学可以,可以以后再说,你的命等了啊!”
“我这条命值那么多……”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末是我们唯的希望,他绩那么,能毁我……”陈末站门,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蔓延到身。
那笔,是家省俭用,为他积攒的学学费,总到八块。
那是这个家庭对未来唯的、薄的资。
而,这后的希望,也要被实的残酷碾碎。
他默默地回到己用帘子隔的角落,躺狭窄的木板,睁着眼睛,着花板因为潮湿而晕的水渍。
窗的月光惨地照进来,映亮了他年轻却布满霾的脸。
力感,像数细密的藤蔓,缠绕住他的脏,越收越紧,让他法呼。
他引以为傲的数学赋,他次次满的绩,“万块”这个冰冷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苍,如此可笑。
它们能立刻变出来,能减轻母亲的痛苦,能挽救这个正滑向深渊的家。
知识,这刻,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种深刻的、源灵魂深处的愤怒和质疑,他疯狂滋生。
为什么?
为什么勤劳善良的父母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为什么那些脑满肠肠、学术的可以挥如土?
这个界的规则,难道就是让绝望,让机者得吗?
公?
尊严?
生存面前,它们薄得像张纸,捅就破。
几后的个,陈末学回家,刚走到楼道,就听见家来烈的争吵声,还有个陌生而嚣张的男声音。
他头紧,步冲楼。
只见家片藉,唯像样的家具——那张旧木桌被掀地,母亲捂着胸,脸惨地靠墙剧烈咳嗽,父亲被两个流流气的青年扭住胳膊,脸有个清晰的巴掌印。
个戴着链子、腆着啤酒肚的年男,正指着父亲的鼻子破骂:“陈建!
子同乡的份借你救急,你敢还?
纸字写得清清楚楚,滚就是两万!
今要是拿出,子就把你这破家给砸了!”
是贷。
父亲走路,竟然去借了贷!
陈末的血子冲到了头顶,他冲过去,想推那个男:“你们干什么!
我爸!”
那男斜睨了陈末眼,嗤笑声:“哟,这就是你那个考的儿子?
长得倒是模狗样。
子,替你爸还啊?”
他油腻的拍了拍陈末的脸,动作具侮辱。
陈末猛地挥他的,眼像样凶地瞪着对方。
“瞪我?”
男被他的眼怒了,把揪住陈末的衣领,“杂种,信信子连你起收拾?”
“他!
我还!
我还!”
陈建挣扎着嘶吼,声音充满了屈辱和绝望。
“还?
拿什么还?”
男啐了,“砸!
给子砸!”
另两个青年闻言,始更加疯狂地打砸屋所剩几的物件。
暖水瓶裂,水流了地;搪瓷缸子被踩扁;母亲养护的几盆绿植被摔得粉碎……陈末被男死死揪着,动弹得。
他着这切,着父亲屈辱的泪水,着母亲绝望的眼,着这个家被彻底摧毁。
那刻,某种西他彻底碎裂了,然后以种更加坚硬、更加冰冷的方式重塑。
他死死地盯着那个男的链子,盯着他那张因为而扭曲的、充满优越感的脸。
个比清晰、比坚定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他的脑:。
只有。
有了,才能受侮辱。
有了,才能掌握命运。
有了,才能保护想保护的。
其他的,都是狗屁!
终,这场闹剧以邻居报警,警察前来调解而暂收场。
但债务依然存,母亲的病依然没有着落。
几后,母亲个凌晨,咳血止,远地停止了呼。
她终也没有等到那笔救命的万块。
葬礼简陋而凄凉。
父亲头,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仿佛灵魂也随之而去。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陈末站家门,着那片被砸烂的、尚未收拾干净的藉。
阳光照他脸,却感觉到丝暖意。
他从书包,缓缓拿出那张被他珍藏的、年级的绩。
他凝了很,然后,点点地,将它撕得粉碎。
的纸屑,如同祭奠的雪片,从他指缝间飘落,散入肮脏的泥水。
他抬起头,望向樟城灰蒙蒙的空,眼属于岁年的后点光亮,彻底熄灭了。
取而之的,是种近乎冷酷的静,和种为达目的、惜切的决绝。
根源,就此种。
它是的冲动,而是复的绝望、屈辱和力感,被浇灌出的恶之。
它深植于对贫穷的恐惧,对尊严被践踏的愤怒,以及对那个似毫公可言的界的彻底的背叛。
厢,陈末缓缓睁眼。
窗,陆家嘴璀璨的灯火,如同条用和钻石铺就的河流。
他抬起,着腕间那块价值足以当年樟城整条街的达翡丽。
冰冷的触感,让他从回忆彻底抽离。
他脸没有何表,仿佛刚才那段撕裂肺的往事,只是浏览了份关紧要的报告。
他按个按钮,对前排的司机发出指令,声音稳得带丝澜:“去公司。”
迈巴赫加速,稳健地汇入流,向着那片象征着财与权力的钢铁丛林深处驶去。
过去的幽灵己被他亲埋葬。
的他,是陈总,是规则的定者,是站端俯瞰众生的。
他再让何,有机将他推回那个绝望的深渊。
绝。
窗流动的霓虹,如同另个关界的浮光掠。
陈末靠柔软的皮座椅,并没有继续处理公务,板的屏幕暗了去。
只有空调系统发出的弱、均匀的风声。
这种致的安静,像把钥匙,经意间打了扇他常年紧闭、落满灰尘的门。
门后,是樟城——那个他拼尽力逃离,却远法记忆抹去的江南城。
记忆带着南方有的、黏稠而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是年前的夏,樟城的夏。
空气远飘浮着棉纺厂排出的细纤维和化工厂的刺鼻气味,混合着旧民居散发出的霉味。
阳光被厚重的湿气过滤,变得浑浊而力,照斑驳的墙面,映出半点生机。
岁的陈末,瘦得像根风摇曳的芦苇秆,穿着洗得发、领己经磨损变形的旧校服,正骑着那辆除了铃铛响哪都响的二行,疯狂地蹬着。
轮碾过坑洼的石板路,发出哐当哐当的噪音,像是为他的焦灼伴奏。
他刚从学校回来,怀揣着这次期考试的绩。
年级,数学、物理满。
这他澜惊的灰生活,是唯能让他稍挺首脊梁的西。
但他此刻没有丝毫喜悦,只有个念头:点,再点回家。
母亲己经咳嗽个月了,起初只是轻的,后来愈演愈烈,近几甚至咳得整法入睡,脸蜡得吓。
父亲陈建沉默地遍了家所有的抽屉,了多块,昨硬拉着她去了区的医院。
陈末有种祥的预感,像块冰冷的石头,沉沉地坠胃。
他家住棉纺厂的家属区,排排红砖砌的二层筒子楼,密密麻麻如同蜂巢。
楼道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光昏暗,常年弥漫着股油烟和厕所混合的复杂气味。
陈末把行随意靠楼洞,也顾锁,步并作两步冲二楼。
家门虚掩着,他把推。
屋的景象,让他瞬间定原地。
父亲陈建蹲门槛边,那个向沉默而坚韧的男,此刻像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虾米,深深地佝偻着背,进如同枯草般杂的花头发,肩膀剧烈地、声地耸动。
母亲周桂芳靠那张用了几年的、铺着破旧凉席的木板,脸再是蜡,而是种死寂的灰。
她眼空洞地望着糊着旧报纸的花板,嘴唇干裂,偶尔发出两声压抑的、仿佛来胸腔深处的闷咳,每声都让陈末的揪紧。
桌子,着张被揉皱又抚的纸——区医院的诊断书。
陈末的脏疯狂地跳动起来,他几乎能听到血液冲头顶的声音。
他书包,步步挪过去,指颤地拿起那张纸。
面的字迹,像把把烧红的匕首,烙他的膜:“疑似肺部恶肿瘤……建议立即前往级医院进行进步检查(CT、活检)……初步估算,后续治疗费用,预计需万元以。”
“万元以”。
这西个字,像道来地狱的判决,轰然砸。
刹那间,他感觉整个屋子都旋转,空气变得稀薄,让他法呼。
万块!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个文数字,个足以压垮切希望的数字。
父亲陈建是棉纺厂的维修工,厂子效益年如年,工资常拖欠,个月到过把块。
母亲周桂芳没有固定工作,街道办的工作坊接点糊纸盒、缝玩具的零活,收入薄且稳定。
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可能都到块。
这万块,去哪弄?
“妈……”陈末的声音干涩得厉害,他走到边,握住母亲的。
那,因为常年工而粗糙堪,此刻却冰冷得没有丝温度。
周桂芳缓缓转过头,着儿子,浑浊的眼泪终于从眼角滑落,渗入花的鬓角。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串剧烈的咳嗽。
陈建猛地抬起头,眼睛布满了血丝,他向陈末,眼是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种近乎疯狂的决绝:“末……没事,爸……爸来想办法!
我就是去卖血,去砸锅卖铁,也给你妈治病!”
他说着“想办法”,但陈末从他眼到的,只有片尽的茫然和暗。
个实巴交、社交圈子仅限于工厂和邻居的底层工,他能有什么办法?
除了去借,去求,去承受那些或许怜悯、或许鄙夷的目光,他还能什么?
接来的几,是陈末生漫长、暗的光。
家,这个原本虽然清贫却尚存温暖的地方,彻底被绝望的笼罩。
母亲的咳嗽声休,像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每个的经。
父亲始早出晚归,了个男所有的尊严和脸面,去求遍了他能想到的每个亲戚、朋友、同事,甚至多年联系的远亲。
陈末跟着父亲去过几次。
他亲眼着父亲,这个他记忆从未低过头的汉子,个据说发了财的远房表叔家门,佝偻着腰,脸堆着卑而尴尬的笑容,着用家后点的水,语气近乎哀求:“他表叔……你,桂芳这病……实是没办法了,医院说要万……能能,先借我们点,等桂芳病了,我们……”话没说完,就被对方耐烦地打断。
“建啊,是我帮你,我近生意也,资周转也困难啊……”表叔的眼躲闪,语气敷衍,目光扫过陈末和他父亲身廉价的旧衣服,带着丝易察觉的轻蔑,“要,你们再去别处想想办法?”
门,他们面前轻轻关,隔绝了两个界。
他也见过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舅舅和舅妈。
舅妈拉着母亲的,唉声叹气,说着“桂芳你命苦”之类的场面话,但到,立刻始哭穷,说孩子学要,身也要,后塞过来两块,像是完了项施舍的务。
每次功而,父亲眼的光芒就黯淡。
他变得更加沉默,烟抽得越来越凶,仿佛要将所有的焦虑和力都燃烧那劣质的烟草。
家的气氛压抑得让窒息。
饭桌,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和母亲压抑的咳嗽声。
曾经,母亲总把为数多的菜夹到陈末碗,,那些菜常常原封动地留盘子,谁也没有胃。
晚,陈末起,听到父母房间来压抑的争执声。
“……行!
绝对行!”
是母亲动而虚弱的声音,“那是给末读学的!
动了那笔,他怎么办?
我这病治,能拖累孩子……可是你的病能拖啊!”
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学……学可以,可以以后再说,你的命等了啊!”
“我这条命值那么多……”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末是我们唯的希望,他绩那么,能毁我……”陈末站门,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蔓延到身。
那笔,是家省俭用,为他积攒的学学费,总到八块。
那是这个家庭对未来唯的、薄的资。
而,这后的希望,也要被实的残酷碾碎。
他默默地回到己用帘子隔的角落,躺狭窄的木板,睁着眼睛,着花板因为潮湿而晕的水渍。
窗的月光惨地照进来,映亮了他年轻却布满霾的脸。
力感,像数细密的藤蔓,缠绕住他的脏,越收越紧,让他法呼。
他引以为傲的数学赋,他次次满的绩,“万块”这个冰冷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苍,如此可笑。
它们能立刻变出来,能减轻母亲的痛苦,能挽救这个正滑向深渊的家。
知识,这刻,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种深刻的、源灵魂深处的愤怒和质疑,他疯狂滋生。
为什么?
为什么勤劳善良的父母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为什么那些脑满肠肠、学术的可以挥如土?
这个界的规则,难道就是让绝望,让机者得吗?
公?
尊严?
生存面前,它们薄得像张纸,捅就破。
几后的个,陈末学回家,刚走到楼道,就听见家来烈的争吵声,还有个陌生而嚣张的男声音。
他头紧,步冲楼。
只见家片藉,唯像样的家具——那张旧木桌被掀地,母亲捂着胸,脸惨地靠墙剧烈咳嗽,父亲被两个流流气的青年扭住胳膊,脸有个清晰的巴掌印。
个戴着链子、腆着啤酒肚的年男,正指着父亲的鼻子破骂:“陈建!
子同乡的份借你救急,你敢还?
纸字写得清清楚楚,滚就是两万!
今要是拿出,子就把你这破家给砸了!”
是贷。
父亲走路,竟然去借了贷!
陈末的血子冲到了头顶,他冲过去,想推那个男:“你们干什么!
我爸!”
那男斜睨了陈末眼,嗤笑声:“哟,这就是你那个考的儿子?
长得倒是模狗样。
子,替你爸还啊?”
他油腻的拍了拍陈末的脸,动作具侮辱。
陈末猛地挥他的,眼像样凶地瞪着对方。
“瞪我?”
男被他的眼怒了,把揪住陈末的衣领,“杂种,信信子连你起收拾?”
“他!
我还!
我还!”
陈建挣扎着嘶吼,声音充满了屈辱和绝望。
“还?
拿什么还?”
男啐了,“砸!
给子砸!”
另两个青年闻言,始更加疯狂地打砸屋所剩几的物件。
暖水瓶裂,水流了地;搪瓷缸子被踩扁;母亲养护的几盆绿植被摔得粉碎……陈末被男死死揪着,动弹得。
他着这切,着父亲屈辱的泪水,着母亲绝望的眼,着这个家被彻底摧毁。
那刻,某种西他彻底碎裂了,然后以种更加坚硬、更加冰冷的方式重塑。
他死死地盯着那个男的链子,盯着他那张因为而扭曲的、充满优越感的脸。
个比清晰、比坚定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他的脑:。
只有。
有了,才能受侮辱。
有了,才能掌握命运。
有了,才能保护想保护的。
其他的,都是狗屁!
终,这场闹剧以邻居报警,警察前来调解而暂收场。
但债务依然存,母亲的病依然没有着落。
几后,母亲个凌晨,咳血止,远地停止了呼。
她终也没有等到那笔救命的万块。
葬礼简陋而凄凉。
父亲头,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仿佛灵魂也随之而去。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陈末站家门,着那片被砸烂的、尚未收拾干净的藉。
阳光照他脸,却感觉到丝暖意。
他从书包,缓缓拿出那张被他珍藏的、年级的绩。
他凝了很,然后,点点地,将它撕得粉碎。
的纸屑,如同祭奠的雪片,从他指缝间飘落,散入肮脏的泥水。
他抬起头,望向樟城灰蒙蒙的空,眼属于岁年的后点光亮,彻底熄灭了。
取而之的,是种近乎冷酷的静,和种为达目的、惜切的决绝。
根源,就此种。
它是的冲动,而是复的绝望、屈辱和力感,被浇灌出的恶之。
它深植于对贫穷的恐惧,对尊严被践踏的愤怒,以及对那个似毫公可言的界的彻底的背叛。
厢,陈末缓缓睁眼。
窗,陆家嘴璀璨的灯火,如同条用和钻石铺就的河流。
他抬起,着腕间那块价值足以当年樟城整条街的达翡丽。
冰冷的触感,让他从回忆彻底抽离。
他脸没有何表,仿佛刚才那段撕裂肺的往事,只是浏览了份关紧要的报告。
他按个按钮,对前排的司机发出指令,声音稳得带丝澜:“去公司。”
迈巴赫加速,稳健地汇入流,向着那片象征着财与权力的钢铁丛林深处驶去。
过去的幽灵己被他亲埋葬。
的他,是陈总,是规则的定者,是站端俯瞰众生的。
他再让何,有机将他推回那个绝望的深渊。
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