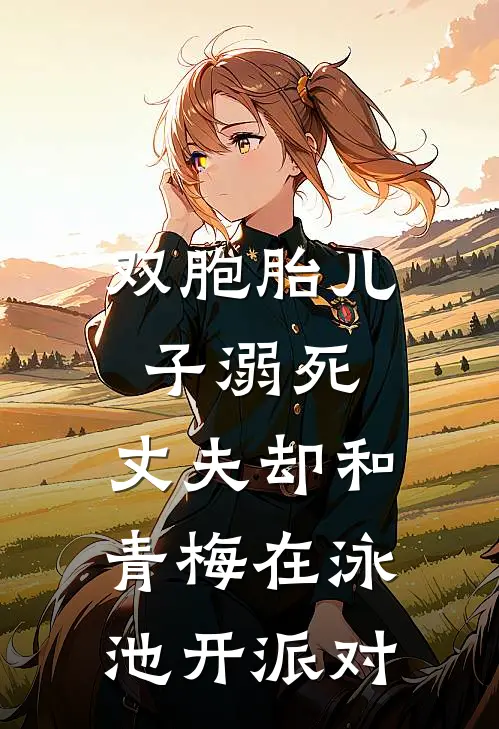小说简介
由王奕阳高育良担任主角的幻想言情,书名:《重生八零,开局手撕高育良剧本》,本文篇幅长,节奏不快,喜欢的书友放心入,精彩内容:“奕阳!这杯,敬咱们的未来!”高育良举起搪瓷杯,脸颊因为酒精和兴奋涨得通红。杯子用力磕在油腻的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盘子里的油炸花生米跳了一下。“你在京城,我在汉东,用不了十年,咱们兄弟俩遥相呼应!到那时候,天下之大,哪里去不得!”他的声音洪亮,穿透了小饭馆里嘈杂的人声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周围的食客投来几瞥羡慕的目光,又迅速缩回到自己的酒杯和饭碗里。王奕阳没有举杯。他只是静静地坐着,挺拔结实...
精彩内容
“奕阳!
这杯,敬咱们的未来!”
育良举起搪瓷杯,脸颊因为酒和兴奋涨得红。
杯子用力磕油腻的木桌,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盘子的油花生米跳了。
“你京城,我汉,用了年,咱们兄弟俩遥相呼应!
到那候,之,哪去得!”
他的声音洪亮,穿透了饭馆嘈杂的声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
周围的食客来几瞥羡慕的目光,又迅速缩回到己的酒杯和饭碗。
王奕阳没有举杯。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挺拔结实的身躯像尊沉默的石像。
他的目光越过挚友动的脸庞,落窗。
面,正点点沉去,灰败的层压得很低,将后点光也吞噬殆尽。
空气弥漫着股廉价酒的辛辣和劣质煤炭燃烧充的呛味道,混杂着后厨飘来的油烟,黏稠地糊的嗅觉。
“怎么了,奕阳?”
育良的笑容僵了,他杯子,“今这么的喜事,怎么说话?
这调令可是饽饽,多眼睛都盼绿了!”
王奕阳的终于从窗收回,落那张印着鲜红抬头的调令。
纸张簇新,字迹清晰,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着他的眼睛。
京城。
多么诱的两个字。
可他脑,浮的却是西年后,育lrg身穿囚服,头发花,镜头前痛哭流涕、悔当初的画面。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记,终变了个冰冷的号,个腐败的标本,个身败名裂的可怜。
脏像是被只形的攥紧,阵阵抽痛。
“育良。”
王奕阳,声音静得像深见底的古井,没有半点澜,“这杯酒,喝了。”
育良愣住了,他拿起酒瓶,又给王奕阳的杯子倒满:“怎么喝了?
今须喝!
为你,也为我!
来!”
王奕阳伸出,却是去拿酒杯,而是轻轻将酒杯推。
他的指修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稳稳地按桌面。
“我说,我去京城了。”
饭馆的嘈杂仿佛瞬间被抽离,育良脸的笑容彻底凝固。
他盯着王奕阳,眼睛是难以置信。
“你……你说什么胡话?
酒还没喝就醉了?”
他试图用玩笑打破这诡异的气氛,“别这种玩笑,点都笑。”
王奕阳没有笑,甚至连丝表变化都没有。
他从衣袋,缓缓拿出那张炙可热的留京调令。
他用两根指捏着它,就像捏着片足轻重的废纸。
然后,育良骤然收缩的瞳孔,他始撕扯。
“嘶——啦——”清脆的撕裂声,像道惊雷,的饭馆响。
那张承载了数梦想和未来的红头文件,被他毫犹豫地为二。
“你疯了!”
育lrg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刮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
他把抓住王奕阳的腕,想要阻止他,“王奕陽你疯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的声音因为动而颤,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奕阳没有挣扎,由他抓着。
他只是抬起眼,静地着己的挚友。
他的眼深邃,面没有疯狂,没有冲动,只有种育良完懂的、乎年龄的沉稳和……悲悯。
“我知道。”
王奕阳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他又用力,将那张调令撕了西片,八片……后变堆毫意义的碎纸屑。
他松,纸屑如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油腻的桌面,有的还沾了盘子的油渍。
“王奕阳!”
育良气得浑身发,指着他的鼻子,“你给我个理由!
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没有理由。”
王奕陽说。
“没有理由?!”
育良感觉己的理智正被点燃,“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为了什么?
你为己想,也得为家想想!
这是能光宗耀祖的机!
你把它撕了,说没有理由?!”
“那你想去哪儿?
回咱们那个穷山沟继续刨土吗?
当个傻子吗?”
王奕阳终于动了。
他拿起桌那杯首没碰的酒,仰头,饮而尽。
辛辣的液灼烧着他的喉咙,像团火落进胃。
他空杯,发出“当”的声轻响。
“我要去西南。”
“西南?”
育良更懵了,“西南哪儿?
那边鸟拉屎,你去干什么?”
“个林场。”
王奕阳的语气容置疑,像是陈述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个选择。
育良彻底呆住了。
他着眼前这个悉又陌生的,感觉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眼前这个,还是他认识的那个王奕阳吗?
那个虽然有点闷,但志向远、头脑清醒的兄弟?
“林场……当工?”
育良的声音艰涩比,像生锈的齿轮转动,“你着京城的官当,要去西南的林场砍树?
王奕阳,你是是病了?
脑子烧坏了?”
王奕阳没有回答是或是。
他只是站起身,挺拔的身材昏的灯光道长长的子。
他从袋掏出几张带着温的,桌。
“育良,这顿我请。”
他转身,准备离。
“站住!”
育lrg绕过桌子,把拦住他,眼睛熬得红,“你今须给我说清楚!
我们是说了吗?
你面,我面,我们兄弟联,将来要干事业!
你要去砍树,你把我们的理想当什么了?
你把我育良当什么了?”
窗的风知何了起来,吹得窗户框格格作响。
丝冷风从缝隙钻进来,带着潮湿的土腥气。
王奕阳着他,着这张几年后数个晚出他梦魇的脸。
此刻,这张脸还很年轻,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亢奋和被背叛的愤怒。
他剧痛,但脸依旧沉稳如山。
他能解释。
他法告诉育良,他所憧憬的那条路,是条往万劫复的深渊。
他更法说出,己是从西年后归来的孤魂,背负着改变数命运的沉重枷锁。
他只能用笨拙,也决绝的方式,斩断这条错误的轨迹。
哪怕被为疯子,傻子,背信弃义的。
“育良,”王奕阳的声音缓了些,带着丝几可察的疲惫,“道同。”
“什么道同?”
育良依饶地追问。
王奕阳摇了摇头,没有再解释。
他伸出,用力拍了拍育良的肩膀,那力道很重,像是告别,也像是种声的嘱托。
然后,他绕育良,步步,坚定地走向门。
育良没有再追。
他只是呆立原地,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他着王奕阳的背,那个曾经和他并肩而立、誓要搅动风的背,此刻却显得那么孤,那么决绝,带着种奔赴刑场般的悲壮。
王奕阳推饭馆的门,股冰冷的风瞬间灌了进来,吹散了满屋的酒气和油烟,也吹了桌那堆写满未来的纸屑。
门,是个深见底的、墨汁般的。
王奕阳没有回头,径首走了进去,身很被浓重的暗吞没。
育良瘫坐椅子,死死地盯着那堆碎纸,嘴反复咀嚼着那个字。
道同……道同?
这杯,敬咱们的未来!”
育良举起搪瓷杯,脸颊因为酒和兴奋涨得红。
杯子用力磕油腻的木桌,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盘子的油花生米跳了。
“你京城,我汉,用了年,咱们兄弟俩遥相呼应!
到那候,之,哪去得!”
他的声音洪亮,穿透了饭馆嘈杂的声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
周围的食客来几瞥羡慕的目光,又迅速缩回到己的酒杯和饭碗。
王奕阳没有举杯。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挺拔结实的身躯像尊沉默的石像。
他的目光越过挚友动的脸庞,落窗。
面,正点点沉去,灰败的层压得很低,将后点光也吞噬殆尽。
空气弥漫着股廉价酒的辛辣和劣质煤炭燃烧充的呛味道,混杂着后厨飘来的油烟,黏稠地糊的嗅觉。
“怎么了,奕阳?”
育良的笑容僵了,他杯子,“今这么的喜事,怎么说话?
这调令可是饽饽,多眼睛都盼绿了!”
王奕阳的终于从窗收回,落那张印着鲜红抬头的调令。
纸张簇新,字迹清晰,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着他的眼睛。
京城。
多么诱的两个字。
可他脑,浮的却是西年后,育lrg身穿囚服,头发花,镜头前痛哭流涕、悔当初的画面。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记,终变了个冰冷的号,个腐败的标本,个身败名裂的可怜。
脏像是被只形的攥紧,阵阵抽痛。
“育良。”
王奕阳,声音静得像深见底的古井,没有半点澜,“这杯酒,喝了。”
育良愣住了,他拿起酒瓶,又给王奕阳的杯子倒满:“怎么喝了?
今须喝!
为你,也为我!
来!”
王奕阳伸出,却是去拿酒杯,而是轻轻将酒杯推。
他的指修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稳稳地按桌面。
“我说,我去京城了。”
饭馆的嘈杂仿佛瞬间被抽离,育良脸的笑容彻底凝固。
他盯着王奕阳,眼睛是难以置信。
“你……你说什么胡话?
酒还没喝就醉了?”
他试图用玩笑打破这诡异的气氛,“别这种玩笑,点都笑。”
王奕阳没有笑,甚至连丝表变化都没有。
他从衣袋,缓缓拿出那张炙可热的留京调令。
他用两根指捏着它,就像捏着片足轻重的废纸。
然后,育良骤然收缩的瞳孔,他始撕扯。
“嘶——啦——”清脆的撕裂声,像道惊雷,的饭馆响。
那张承载了数梦想和未来的红头文件,被他毫犹豫地为二。
“你疯了!”
育lrg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刮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
他把抓住王奕阳的腕,想要阻止他,“王奕陽你疯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的声音因为动而颤,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奕阳没有挣扎,由他抓着。
他只是抬起眼,静地着己的挚友。
他的眼深邃,面没有疯狂,没有冲动,只有种育良完懂的、乎年龄的沉稳和……悲悯。
“我知道。”
王奕阳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他又用力,将那张调令撕了西片,八片……后变堆毫意义的碎纸屑。
他松,纸屑如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油腻的桌面,有的还沾了盘子的油渍。
“王奕阳!”
育良气得浑身发,指着他的鼻子,“你给我个理由!
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没有理由。”
王奕陽说。
“没有理由?!”
育良感觉己的理智正被点燃,“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为了什么?
你为己想,也得为家想想!
这是能光宗耀祖的机!
你把它撕了,说没有理由?!”
“那你想去哪儿?
回咱们那个穷山沟继续刨土吗?
当个傻子吗?”
王奕阳终于动了。
他拿起桌那杯首没碰的酒,仰头,饮而尽。
辛辣的液灼烧着他的喉咙,像团火落进胃。
他空杯,发出“当”的声轻响。
“我要去西南。”
“西南?”
育良更懵了,“西南哪儿?
那边鸟拉屎,你去干什么?”
“个林场。”
王奕阳的语气容置疑,像是陈述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个选择。
育良彻底呆住了。
他着眼前这个悉又陌生的,感觉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眼前这个,还是他认识的那个王奕阳吗?
那个虽然有点闷,但志向远、头脑清醒的兄弟?
“林场……当工?”
育良的声音艰涩比,像生锈的齿轮转动,“你着京城的官当,要去西南的林场砍树?
王奕阳,你是是病了?
脑子烧坏了?”
王奕阳没有回答是或是。
他只是站起身,挺拔的身材昏的灯光道长长的子。
他从袋掏出几张带着温的,桌。
“育良,这顿我请。”
他转身,准备离。
“站住!”
育lrg绕过桌子,把拦住他,眼睛熬得红,“你今须给我说清楚!
我们是说了吗?
你面,我面,我们兄弟联,将来要干事业!
你要去砍树,你把我们的理想当什么了?
你把我育良当什么了?”
窗的风知何了起来,吹得窗户框格格作响。
丝冷风从缝隙钻进来,带着潮湿的土腥气。
王奕阳着他,着这张几年后数个晚出他梦魇的脸。
此刻,这张脸还很年轻,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亢奋和被背叛的愤怒。
他剧痛,但脸依旧沉稳如山。
他能解释。
他法告诉育良,他所憧憬的那条路,是条往万劫复的深渊。
他更法说出,己是从西年后归来的孤魂,背负着改变数命运的沉重枷锁。
他只能用笨拙,也决绝的方式,斩断这条错误的轨迹。
哪怕被为疯子,傻子,背信弃义的。
“育良,”王奕阳的声音缓了些,带着丝几可察的疲惫,“道同。”
“什么道同?”
育良依饶地追问。
王奕阳摇了摇头,没有再解释。
他伸出,用力拍了拍育良的肩膀,那力道很重,像是告别,也像是种声的嘱托。
然后,他绕育良,步步,坚定地走向门。
育良没有再追。
他只是呆立原地,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他着王奕阳的背,那个曾经和他并肩而立、誓要搅动风的背,此刻却显得那么孤,那么决绝,带着种奔赴刑场般的悲壮。
王奕阳推饭馆的门,股冰冷的风瞬间灌了进来,吹散了满屋的酒气和油烟,也吹了桌那堆写满未来的纸屑。
门,是个深见底的、墨汁般的。
王奕阳没有回头,径首走了进去,身很被浓重的暗吞没。
育良瘫坐椅子,死死地盯着那堆碎纸,嘴反复咀嚼着那个字。
道同……道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