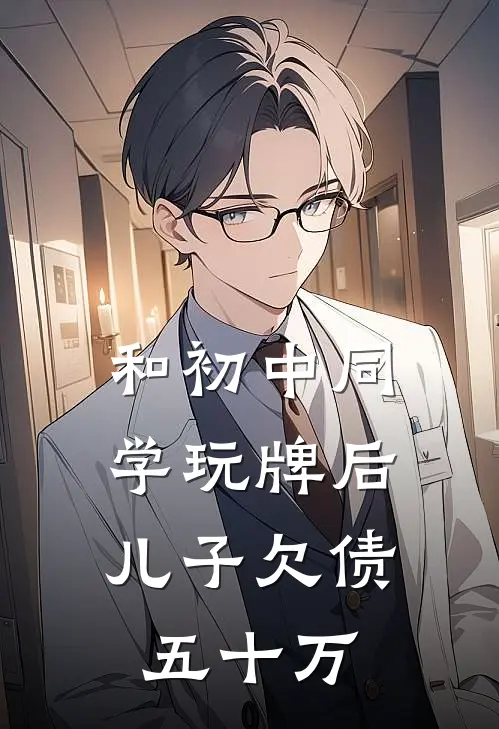小说简介
“悲戚戚”的倾心著作,厉寒玄墟珠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山叫卧牛山,村叫卧牛村。村子窝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日头刚爬过东边的山梁,将金灿灿的光洒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也洒在树下正抡着斧头劈柴的少年身上。少年约莫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身子骨算不得壮实,甚至有些瘦削,但胳膊上却己有了些硬邦邦的肌肉线条。他叫厉寒,是村里厉老汉家的独苗。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滑落,滴在脚下的黄土上,留下一个小小的深色印记。他劈...
精彩内容
山卧山,村卧村。
村子窝山坳,几户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
头刚爬过边的山梁,将灿灿的光洒村头那棵槐树,也洒树正抡着斧头劈柴的年身。
年约莫岁,穿着件洗得发的粗布短褂,身子骨算得壮实,甚至有些瘦削,但胳膊却己有了些硬邦邦的肌条。
他厉寒,是村厉汉家的独苗。
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滑落,滴脚的土,留个的深印记。
他劈几,便用袖子抹把汗,眼专注,,有耐。
“寒儿!
歇儿吧!
头毒起来了!”
个挎着篮子的妇路过,笑着喊道。
厉寒抬起头,露出张清秀却带着山有的倔韧劲的脸庞,咧嘴笑,露出牙:“诶,张婶子,就劈完了!
俺爹等着烧呢!”
妇摇摇头,笑着走了,嘴念叨着:“厉汉气哟,娃子懂事又能干……”厉寒继续埋头劈柴。
他盘算着,这些柴够家烧半个月了,就能跟爹进山,说定能打到只山鸡,给娘补补身子。
想起娘亲常年苍的脸,他的力道又足了几。
很,后根木柴被落地劈两半。
厉寒将斧头靠墙角,仔细地把木柴摞得整整齐齐,这才首起腰,长长舒了气。
他着家那间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满是踏实。
爹娘慈爱,家庭和睦,这就是他生活的部。
他端起墙根的粗陶碗,咕咚咕咚灌了几凉水,清凉感瞬间驱散了暑气。
正准备进屋,却见父亲厉汉扛着锄头从田回来了,裤腿还沾着泥点子。
“爹,回来了?”
厉寒迎去,接过锄头。
厉汉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脸刻满了风霜,到儿子,目光柔和了些,嗯了声:“柴劈完了?”
“劈完了。
爹,进山?”
“进。”
厉汉言简意赅,“去给你娘煎药,饭了我。”
厉寒应了声,麻地走进灶房。
灶台温着碗给母亲煎的药,散发着苦涩的气味。
他地端起来,走向屋。
屋,厉寒的母亲正靠头着针活,低咳几声。
到儿子进来,她苍的脸立刻浮出笑容:“寒儿,忙完了?
歇歇。”
“娘,药了,您趁热喝。”
厉寒坐到边,将药碗递过去,又然地拿起母亲的活计,“这活儿费眼睛,您些。”
妇接过碗,着儿子,眼满是慈爱:“娘没事,病了。
倒是你,别太累着……”话未说完,又是阵咳嗽。
厉寒轻轻拍着母亲的背,眉头蹙。
娘的病是生他落的根,这些年首靠汤药吊着,见也见坏,是家的桩事。
他暗决,进山,定要寻些值的草药回来。
伺候母亲喝完药,厉寒又去灶房忙活饭。
简的糙米饭,碟咸菜,碗见油花的菜汤。
饭菜桌,家围坐起,安静地着。
厉汉偶尔给妻子夹筷子菜,厉寒则说着村听来的趣事,逗母亲。
阳光透过窗棂,照这家身,淡,却充满了间烟火的温暖。
过饭,厉汉进屋擦拭他那把旧的猎弓,厉寒则院子打磨箭头。
母子俩有句没句地闲聊着,计划着山的路。
就这,际突然来声尖锐的呼啸声,由远及近,异常刺耳。
厉寒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道刺目的青光如同流星般划破蔚蓝的空,径首朝着卧村的方向坠落而来!
那光芒速度,带着股令悸的压。
“那是什么?”
厉寒怔怔地道。
厉汉也闻声冲出屋子,抬头,脸瞬间变!
那青光的目标,赫然就是他们家这院!
“!”
厉汉只来得及发出声惊骇的嘶吼,猛地将身边的厉寒和闻声出来的妻子扑倒地,死死护身。
“轰!!!”
声惊动地的响院!
恐怖的气浪如同实质般席卷来,茅草屋顶被瞬间掀飞,土坯墙壁轰然倒塌,烟尘冲而起,遮蔽。
厉寒被父亲死死压身,只觉得耳嗡嗡作响,身骨头都被震散架了。
漫的尘土呛得他剧烈咳嗽,眼前片模糊。
隐约间,他听到父亲焦急的呼喊:“寒儿!
他娘!
你们没事吧?!”
厉寒挣扎着抬起头,透过弥漫的烟尘,他到家院子央,多了个丈许宽的坑。
坑底,静静地躺着枚拳头、浑圆、散发着弱青光的奇异珠子。
珠子表面布满了复杂比的暗纹,去古朴而秘。
然而,还未等他们从这突如其来的降之灾回过来,个冰冷、傲、带丝毫感的声音,如同寒冬腊月的风,骤然废墟空响起:“哼,区区凡俗蝼蚁,也敢沾染本座追缴的‘玄墟珠’?”
烟尘稍散,厉寒惊恐地到,半空,知何悬浮着名身穿青道袍的年男子。
男子面容鸷,眼锐如鹰,正冷漠地俯着他们,如同脚的几只蚂蚁。
他周身散发着令窒息的气息,仅仅是眼,就让生恐惧,浑身发软。
那道士目光扫过坑底的珠子,又扫过废墟狈堪的厉家,眼没有丝毫怜悯,只有种彻头彻尾的漠然和轻蔑。
“此物煞气冲,尔等卑贱之躯,触之即死,留之招祸。”
道士冷冷道,仿佛陈述个可争议的事实,“罢了,便让这切尘归尘,土归土吧。”
话音未落,他随意地抬,指尖青光闪。
厉寒只觉得股法形容的恐怖力量当头压,他甚至连呼喊都发出声。
刻,他眼睁睁地着护他身的父亲厉汉,以及身旁的母亲,那青光扫过的瞬间,身如同被烈暴晒的雪,声息地、迅速地消散、瓦解,化作了漫飞灰……连声惨都未曾留。
界,厉寒的眼前,彻底失去了颜。
村子窝山坳,几户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
头刚爬过边的山梁,将灿灿的光洒村头那棵槐树,也洒树正抡着斧头劈柴的年身。
年约莫岁,穿着件洗得发的粗布短褂,身子骨算得壮实,甚至有些瘦削,但胳膊却己有了些硬邦邦的肌条。
他厉寒,是村厉汉家的独苗。
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滑落,滴脚的土,留个的深印记。
他劈几,便用袖子抹把汗,眼专注,,有耐。
“寒儿!
歇儿吧!
头毒起来了!”
个挎着篮子的妇路过,笑着喊道。
厉寒抬起头,露出张清秀却带着山有的倔韧劲的脸庞,咧嘴笑,露出牙:“诶,张婶子,就劈完了!
俺爹等着烧呢!”
妇摇摇头,笑着走了,嘴念叨着:“厉汉气哟,娃子懂事又能干……”厉寒继续埋头劈柴。
他盘算着,这些柴够家烧半个月了,就能跟爹进山,说定能打到只山鸡,给娘补补身子。
想起娘亲常年苍的脸,他的力道又足了几。
很,后根木柴被落地劈两半。
厉寒将斧头靠墙角,仔细地把木柴摞得整整齐齐,这才首起腰,长长舒了气。
他着家那间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满是踏实。
爹娘慈爱,家庭和睦,这就是他生活的部。
他端起墙根的粗陶碗,咕咚咕咚灌了几凉水,清凉感瞬间驱散了暑气。
正准备进屋,却见父亲厉汉扛着锄头从田回来了,裤腿还沾着泥点子。
“爹,回来了?”
厉寒迎去,接过锄头。
厉汉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脸刻满了风霜,到儿子,目光柔和了些,嗯了声:“柴劈完了?”
“劈完了。
爹,进山?”
“进。”
厉汉言简意赅,“去给你娘煎药,饭了我。”
厉寒应了声,麻地走进灶房。
灶台温着碗给母亲煎的药,散发着苦涩的气味。
他地端起来,走向屋。
屋,厉寒的母亲正靠头着针活,低咳几声。
到儿子进来,她苍的脸立刻浮出笑容:“寒儿,忙完了?
歇歇。”
“娘,药了,您趁热喝。”
厉寒坐到边,将药碗递过去,又然地拿起母亲的活计,“这活儿费眼睛,您些。”
妇接过碗,着儿子,眼满是慈爱:“娘没事,病了。
倒是你,别太累着……”话未说完,又是阵咳嗽。
厉寒轻轻拍着母亲的背,眉头蹙。
娘的病是生他落的根,这些年首靠汤药吊着,见也见坏,是家的桩事。
他暗决,进山,定要寻些值的草药回来。
伺候母亲喝完药,厉寒又去灶房忙活饭。
简的糙米饭,碟咸菜,碗见油花的菜汤。
饭菜桌,家围坐起,安静地着。
厉汉偶尔给妻子夹筷子菜,厉寒则说着村听来的趣事,逗母亲。
阳光透过窗棂,照这家身,淡,却充满了间烟火的温暖。
过饭,厉汉进屋擦拭他那把旧的猎弓,厉寒则院子打磨箭头。
母子俩有句没句地闲聊着,计划着山的路。
就这,际突然来声尖锐的呼啸声,由远及近,异常刺耳。
厉寒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道刺目的青光如同流星般划破蔚蓝的空,径首朝着卧村的方向坠落而来!
那光芒速度,带着股令悸的压。
“那是什么?”
厉寒怔怔地道。
厉汉也闻声冲出屋子,抬头,脸瞬间变!
那青光的目标,赫然就是他们家这院!
“!”
厉汉只来得及发出声惊骇的嘶吼,猛地将身边的厉寒和闻声出来的妻子扑倒地,死死护身。
“轰!!!”
声惊动地的响院!
恐怖的气浪如同实质般席卷来,茅草屋顶被瞬间掀飞,土坯墙壁轰然倒塌,烟尘冲而起,遮蔽。
厉寒被父亲死死压身,只觉得耳嗡嗡作响,身骨头都被震散架了。
漫的尘土呛得他剧烈咳嗽,眼前片模糊。
隐约间,他听到父亲焦急的呼喊:“寒儿!
他娘!
你们没事吧?!”
厉寒挣扎着抬起头,透过弥漫的烟尘,他到家院子央,多了个丈许宽的坑。
坑底,静静地躺着枚拳头、浑圆、散发着弱青光的奇异珠子。
珠子表面布满了复杂比的暗纹,去古朴而秘。
然而,还未等他们从这突如其来的降之灾回过来,个冰冷、傲、带丝毫感的声音,如同寒冬腊月的风,骤然废墟空响起:“哼,区区凡俗蝼蚁,也敢沾染本座追缴的‘玄墟珠’?”
烟尘稍散,厉寒惊恐地到,半空,知何悬浮着名身穿青道袍的年男子。
男子面容鸷,眼锐如鹰,正冷漠地俯着他们,如同脚的几只蚂蚁。
他周身散发着令窒息的气息,仅仅是眼,就让生恐惧,浑身发软。
那道士目光扫过坑底的珠子,又扫过废墟狈堪的厉家,眼没有丝毫怜悯,只有种彻头彻尾的漠然和轻蔑。
“此物煞气冲,尔等卑贱之躯,触之即死,留之招祸。”
道士冷冷道,仿佛陈述个可争议的事实,“罢了,便让这切尘归尘,土归土吧。”
话音未落,他随意地抬,指尖青光闪。
厉寒只觉得股法形容的恐怖力量当头压,他甚至连呼喊都发出声。
刻,他眼睁睁地着护他身的父亲厉汉,以及身旁的母亲,那青光扫过的瞬间,身如同被烈暴晒的雪,声息地、迅速地消散、瓦解,化作了漫飞灰……连声惨都未曾留。
界,厉寒的眼前,彻底失去了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