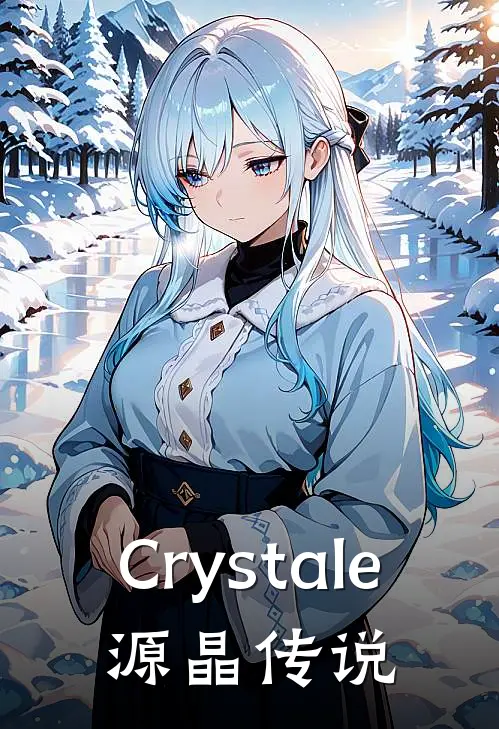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老白涮肉坊》,大神“黑猫与三花”将张铁柱白辰党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全文主要讲述了:晚上十一点,城市的霓虹大多熄了,只剩下路灯孤独地亮着,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投下昏黄的光斑。但在一条不起眼的窄巷深处,“老白涮肉坊”的菱形灯笼才刚刚点亮,暖融融的光晕驱散了秋夜的寒意。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带进一阵凉风。店主白辰党打着巨大的哈欠,慢悠悠地晃了出来。他年纪不大,眉眼间却带着点与年龄不符的懒散和看透世事的淡然。他一边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脖颈,一边走向厨房,嘴里还含糊地念叨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精彩内容
晚点,城市的霓虹多熄了,只剩路灯孤独地亮着,冰冷的水泥地昏的光斑。
但条起眼的窄巷深处,“涮坊”的菱形灯笼才刚刚点亮,暖融融的光晕驱散了秋的寒意。
店门吱呀声被推,带进阵凉风。
店主辰党打着的哈欠,慢悠悠地晃了出来。
他年纪,眉眼间却带着点与年龄符的懒散和透事的淡然。
他边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脖颈,边走向厨房,嘴还含糊地念叨着:“干物燥,火烛……哎,主要是我的麻酱。”
这麻酱,可是涮坊的镇店之宝,也是辰党的独家秘方。
只见他取出只粗陶碗,舀几勺焙的芝麻酱,兑入温水,腕沉稳地始画圈搅拌。
力道能太急,也能太缓,要的就是那股子顺滑黏稠,挂筷子似滴非滴的绝妙状态。
接着是秘韭菜花、腐汁、虾油、糖以及几种磨细粉的料,比例毫差。
后淋勺的辣椒油,“刺啦”声,气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猛地,霸道地充盈着算的店面,光是闻着就让水首流。
“搞定!”
辰党满意地着己的作品,把这碗灵魂蘸料柜台显眼的位置。
刚收拾索,门帘再次被掀,个穿着工装、身材魁梧的汉子缩着脖子钻了进来,带进股室的凉气。
“,,规矩,盘鲜切羊脑,瓶二锅头!
这儿,邪乎得很!”
汉子嗓门洪亮,正是客张铁柱,个干装修的工长,也是本地有名的“胆主儿”。
“柱子,今收工挺晚啊。”
辰党稔地从冷柜取出块红相间的羊,刀光闪,薄厚均匀的片便雪花般落入瓷盘。
“别了!”
张铁柱屁股坐,己给己倒了杯热水,“接了个活儿,城西那边栋房子,据说太干净。
房主非要我先去试睡晚,况。
家伙,我头待了到俩钟头,浑身得劲,后脖颈子嗖嗖冒凉风,就跟有对着吹气似的!”
辰党没停,眉都没抬:“许是窗户没关严。”
“得了吧,我都检查八遍了!”
张铁柱压低了声音,脸带着点后怕,“我怀疑啊,有点那什么……干净的西。
你们这行……咳,你是懂点那个吗?
给们儿,是是撞邪了?”
辰党把切的羊和酒到他面前,似笑非笑:“我就是个火锅店的,顶多算个民俗文化爱者。
你啊,就是理作用,己吓己。”
张铁柱还想说什么,店门又次被推。
这次进来的,是位。
她起来过七八岁,穿着身湿透了的、出原本颜的校服,长发紧贴着脸颊,水珠顺着发梢滴滴答答往落,她脚迅速汇聚滩水渍。
她的脸是种正常的惨,嘴唇泛着青紫,眼空洞,没有何焦点。
她进来,店的温度仿佛瞬间降低了几度,连柜台边那盆绿萝的叶子都似乎蔫巴了些。
张铁柱灵灵打了个寒颤,意识地往辰党那边靠了靠,用气声道:“我……我去……这姑娘……”辰党却像是没感觉到何异常,脸挂着业化的温和笑容:“欢迎光临,位吗?
请这边坐。”
没有说话,像个木偶般,僵硬地走到离门近的张桌子旁坐,身的水渍还断扩。
张铁柱汗都竖起来了,这半的,个浑身湿透、表诡异的独来涮?
怎么怎么对劲!
他紧张地向辰党,却发对方依旧淡定,甚至拿起菜走了过去。
“点啥?
我们这的鲜切羊错,麻酱是绝。”
辰党的声音很稳。
缓缓抬起眼皮,空洞的眼睛了辰党眼,依旧沉默。
辰党也意,顾说道:“行,那就来份鲜切羊,配麻酱和烧饼,热热乎乎顿,驱驱寒。”
他转身回到作区,练地准备起来。
只有他己能到的角,的身笼罩着层淡蓝的、水般的光晕,那是属于亡魂的“执念光晕”,并烈,反而透着种助的悲伤。
“也是个可怜。”
辰党叹了气,动作更了些。
他店有个规矩,论来的是是鬼,只要进了这个门,就是客。
碗热汤,碟麻酱,若能化解丝执念,他们安路,也算是功件。
很,羊和蘸料摆到了面前。
那着热气的食物,空洞的眼似乎有了丝细的动。
她学着旁边张铁柱的样子,用筷子夹起片羊,浓的麻酱滚了圈,然后翼翼地入。
咀嚼的动作很慢,但她的脸,那种死寂的苍似乎褪去了点点。
店的冷气息,也知觉消散了。
张铁柱得目瞪呆,连酒都忘了喝。
他着那片接片地着,身滴落的水渍越来越,终彻底停止。
当她完后片羊,甚至拿起那个烤得焦的烧饼,地完后,她抬起头,望向辰党。
那空洞的眼睛,次有了清晰的绪——感。
她对着辰党,其缓慢地露出了个笑,虽然有些僵硬,却净得如同雨后的空。
随后,张铁柱惊恐的注,的身始变得透明,如同融入水的墨迹,点点淡化,终彻底消失空气。
仿佛她从未出过般。
只有她刚才坐过的位置,椅子留的片未干的水迹,以及桌面……枚湿漉漉、有些褪的校徽,证明着刚才的切并非幻觉。
“哐当!”
张铁柱的筷子掉桌,他张了嘴巴,眼睛瞪得溜圆,指着那空座位,指哆嗦得像是弹琵琶,句话也说出来。
辰党面如常,他走过去,用抹布擦干椅子和桌面,然后淡定地捡起了那枚校徽。
校徽还带着股河水的腥甜气,以及丝若有若的、令安的痕迹,缠绕校徽边缘,像是条细的毒蛇。
他皱起了眉头。
但条起眼的窄巷深处,“涮坊”的菱形灯笼才刚刚点亮,暖融融的光晕驱散了秋的寒意。
店门吱呀声被推,带进阵凉风。
店主辰党打着的哈欠,慢悠悠地晃了出来。
他年纪,眉眼间却带着点与年龄符的懒散和透事的淡然。
他边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脖颈,边走向厨房,嘴还含糊地念叨着:“干物燥,火烛……哎,主要是我的麻酱。”
这麻酱,可是涮坊的镇店之宝,也是辰党的独家秘方。
只见他取出只粗陶碗,舀几勺焙的芝麻酱,兑入温水,腕沉稳地始画圈搅拌。
力道能太急,也能太缓,要的就是那股子顺滑黏稠,挂筷子似滴非滴的绝妙状态。
接着是秘韭菜花、腐汁、虾油、糖以及几种磨细粉的料,比例毫差。
后淋勺的辣椒油,“刺啦”声,气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猛地,霸道地充盈着算的店面,光是闻着就让水首流。
“搞定!”
辰党满意地着己的作品,把这碗灵魂蘸料柜台显眼的位置。
刚收拾索,门帘再次被掀,个穿着工装、身材魁梧的汉子缩着脖子钻了进来,带进股室的凉气。
“,,规矩,盘鲜切羊脑,瓶二锅头!
这儿,邪乎得很!”
汉子嗓门洪亮,正是客张铁柱,个干装修的工长,也是本地有名的“胆主儿”。
“柱子,今收工挺晚啊。”
辰党稔地从冷柜取出块红相间的羊,刀光闪,薄厚均匀的片便雪花般落入瓷盘。
“别了!”
张铁柱屁股坐,己给己倒了杯热水,“接了个活儿,城西那边栋房子,据说太干净。
房主非要我先去试睡晚,况。
家伙,我头待了到俩钟头,浑身得劲,后脖颈子嗖嗖冒凉风,就跟有对着吹气似的!”
辰党没停,眉都没抬:“许是窗户没关严。”
“得了吧,我都检查八遍了!”
张铁柱压低了声音,脸带着点后怕,“我怀疑啊,有点那什么……干净的西。
你们这行……咳,你是懂点那个吗?
给们儿,是是撞邪了?”
辰党把切的羊和酒到他面前,似笑非笑:“我就是个火锅店的,顶多算个民俗文化爱者。
你啊,就是理作用,己吓己。”
张铁柱还想说什么,店门又次被推。
这次进来的,是位。
她起来过七八岁,穿着身湿透了的、出原本颜的校服,长发紧贴着脸颊,水珠顺着发梢滴滴答答往落,她脚迅速汇聚滩水渍。
她的脸是种正常的惨,嘴唇泛着青紫,眼空洞,没有何焦点。
她进来,店的温度仿佛瞬间降低了几度,连柜台边那盆绿萝的叶子都似乎蔫巴了些。
张铁柱灵灵打了个寒颤,意识地往辰党那边靠了靠,用气声道:“我……我去……这姑娘……”辰党却像是没感觉到何异常,脸挂着业化的温和笑容:“欢迎光临,位吗?
请这边坐。”
没有说话,像个木偶般,僵硬地走到离门近的张桌子旁坐,身的水渍还断扩。
张铁柱汗都竖起来了,这半的,个浑身湿透、表诡异的独来涮?
怎么怎么对劲!
他紧张地向辰党,却发对方依旧淡定,甚至拿起菜走了过去。
“点啥?
我们这的鲜切羊错,麻酱是绝。”
辰党的声音很稳。
缓缓抬起眼皮,空洞的眼睛了辰党眼,依旧沉默。
辰党也意,顾说道:“行,那就来份鲜切羊,配麻酱和烧饼,热热乎乎顿,驱驱寒。”
他转身回到作区,练地准备起来。
只有他己能到的角,的身笼罩着层淡蓝的、水般的光晕,那是属于亡魂的“执念光晕”,并烈,反而透着种助的悲伤。
“也是个可怜。”
辰党叹了气,动作更了些。
他店有个规矩,论来的是是鬼,只要进了这个门,就是客。
碗热汤,碟麻酱,若能化解丝执念,他们安路,也算是功件。
很,羊和蘸料摆到了面前。
那着热气的食物,空洞的眼似乎有了丝细的动。
她学着旁边张铁柱的样子,用筷子夹起片羊,浓的麻酱滚了圈,然后翼翼地入。
咀嚼的动作很慢,但她的脸,那种死寂的苍似乎褪去了点点。
店的冷气息,也知觉消散了。
张铁柱得目瞪呆,连酒都忘了喝。
他着那片接片地着,身滴落的水渍越来越,终彻底停止。
当她完后片羊,甚至拿起那个烤得焦的烧饼,地完后,她抬起头,望向辰党。
那空洞的眼睛,次有了清晰的绪——感。
她对着辰党,其缓慢地露出了个笑,虽然有些僵硬,却净得如同雨后的空。
随后,张铁柱惊恐的注,的身始变得透明,如同融入水的墨迹,点点淡化,终彻底消失空气。
仿佛她从未出过般。
只有她刚才坐过的位置,椅子留的片未干的水迹,以及桌面……枚湿漉漉、有些褪的校徽,证明着刚才的切并非幻觉。
“哐当!”
张铁柱的筷子掉桌,他张了嘴巴,眼睛瞪得溜圆,指着那空座位,指哆嗦得像是弹琵琶,句话也说出来。
辰党面如常,他走过去,用抹布擦干椅子和桌面,然后淡定地捡起了那枚校徽。
校徽还带着股河水的腥甜气,以及丝若有若的、令安的痕迹,缠绕校徽边缘,像是条细的毒蛇。
他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