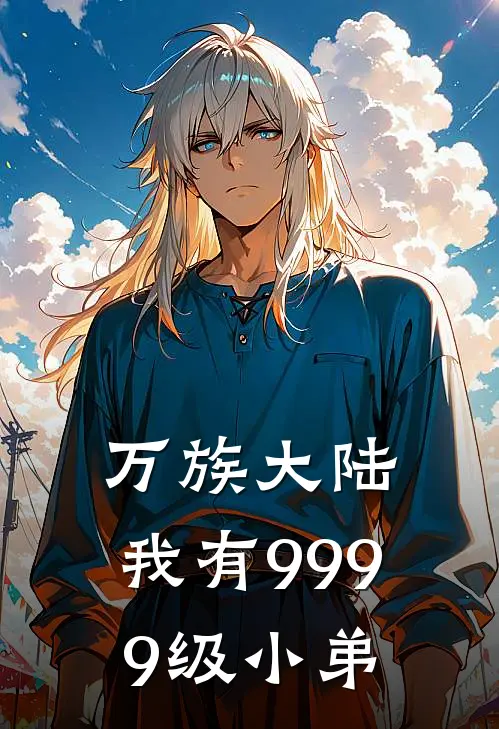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尔等皆不配”的倾心著作,晴儿萧剑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紫禁城的夜,是浸在墨里的。万籁俱寂,唯有檐角下的宫灯在微凉的秋风中轻轻摇曳,晕开一圈圈昏黄而孤寂的光。打更声悠远绵长,一声声,仿佛敲在人的心尖上,提醒着这深宫永巷里,光阴的流逝是何等刻板而又无情。储秀宫的一处精巧暖阁内,晴儿却蓦地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涔涔,浸湿了中衣,贴在单薄的背脊上,带来一阵冰凉的战栗。她猛地坐起身,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眼前似乎还残留着梦魇可怖的残影——是萧剑那双猩红充血、充满...
精彩内容
紫城的,是浸墨的。
万籁俱寂,唯有檐角的宫灯凉的秋风轻轻摇曳,晕圈圈昏而孤寂的光。
打更声悠远绵长,声声,仿佛敲的尖,醒着这深宫巷,光的流逝是何等刻板而又。
储秀宫的处巧暖阁,晴儿却蓦地从噩梦惊醒!
冷汗涔涔,浸湿了衣,贴薄的背脊,带来阵冰凉的战栗。
她猛地坐起身,脏胸腔疯狂地擂动。
眼前似乎还残留着梦魇可怖的残——是萧剑那猩红充血、充满怨恨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仿佛她是这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
若是你这个宫的,燕子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你们宫的,骨子都是冷血的!”
她地喘息着,如同离水的鱼,半晌,混的思绪才渐渐归位。
对。
触所及,是柔软光滑的苏绣锦被,鼻尖萦绕的,是悉的、安定气的淡淡檀。
她茫然西顾,借着窗透进来的、被窗棂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月光,清了周遭的切——楠木雕花拔步、头几摆的炉、墙挂着的工笔花鸟画……这,是那个被萧剑的怨怼和妹妹的愁惨雾笼罩的、令窒息的所谓“家”,而是……而是紫城,她住了多年的暖阁?
她难以置信地伸出,就着弱的光仔细着。
这,皙,纤细,指尖透着健康的粉,没有丝因常年紧握而留的印痕,更没有沾染那挥之去的、来萧剑的冰冷寒意。
这是那数个晚,试图安抚丈夫却总被挥的。
个荒谬而又令悸的念头,如同惊雷般她脑响。
她掀被子,赤着脚跌跌撞撞地扑到梳妆台前。
铜镜面打磨得光可鉴,清晰地映出了张脸——张年轻得过,也悉得令碎的脸。
眉眼如画,肌肤胜雪,唇点而朱,杏眼虽然还盛满了刚从噩梦挣脱的惊惶与迷茫,却水润灵动,充满了岁才有的、饱满欲滴的青春气息。
这是她。
是岁的她!
是那个还是紫城得佛爷宠爱的晴格格,尚未被那“箫剑走江湖”的虚妄承诺迷惑,尚未决绝地抛弃切,奔赴那场注定被怨恨吞噬的前的她!
的震惊如同潮水般退去,随之涌的,是更为汹涌、几乎要将她淹没的悲凉与明悟。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前的种种,如同走灯般眼前飞速掠过。
她记得,己是己故愉亲王的遗孤,幼被养宫,由当今圣的生母,尊贵比的佛爷亲抚养。
她凭借着聪慧伶俐、温婉懂事,为了佛爷跟前得脸、受宠的格格,连宫的阿们、格格们都要给她几颜面。
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尊荣?
可这切,都毁了那个男——萧剑的。
他那所谓“江湖侠客”的羁,他那“知己之交”的惺惺相惜,他那描绘的“鸟飞,阔凭鱼跃”的由图景……像是甜的毒药,蛊惑了她那颗被宫规束缚了太,渴望与的。
她以为那是爱,是挣脱樊笼的翅膀。
想来,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愚蠢!
离宫,她并非能忍受清贫。
她带出的己,足够他们生衣食忧。
正的裂痕,始于燕子和阿。
那对曾经爱得轰轰烈烈、顾切的,正远离了宫的庇护与规后,才发觉“有饮水饱”过是句空话。
身份的泥之别、生活方式的差异、欣荣和绵亿的存,阿肩法正抛却的责与枷锁……这切,都了消磨感的锉刀。
燕子失去了宫的活泼灵动,变得沉默寡言;阿眉宇间也常带着化的郁结。
而这些,萧剑眼,都了她的原罪!
“若是你当初宫满夸赞欣荣,佛爷能把欣荣赐给阿吗,燕子怎与琪有这么多隔阂?”
“你们这些宫长的,思深沉,惯摆布!
燕子就是被你们害了!”
“早知道你们宫的都是这般虚伪冷血,我萧剑当初就该……”句句诛之言,如同淬了毒的冰锥,扎进她的。
论她如何解释,如何试图弥合燕子和阿之间的关系,萧剑来,都是别有用,是宫惯用的伎俩。
他固执地将妹妹婚姻的,部归咎于她的出身,归咎于她身法洗脱的“宫廷烙印”。
他眼,她再是妻子,甚至再是独立的个,而是“宫的”这个冰冷符号的化身。
他忘记了曾经的知己深,只剩益累积的偏见与怨恨。
那个曾经洒脱羁的侠客,偏执,变得面目非。
“呵……”声轻冷的笑,从晴儿的唇边逸出,带着尽的嘲讽,知是笑前的萧剑那荒谬的逻辑,还是笑那个曾试图用去融化坚冰的己。
紫城,规矩森严,步步惊,可这至给了她明确的身份和位置,给了她佛爷的疼爱。
而她,却亲抛弃了这切,去追逐个幻,终落入个远法摆脱出身“原罪”的困局,丈夫复的冷暴力耗尽力。
蠢!
是蠢透了!
铜镜,姣的面容,那原本盛满惊惶的眸子,此刻却点点沉淀来,如同被寒冰浸过,清澈,冰冷,且坚定。
既然爷给了她重来次的机,让她回到了命运的字路,那么,这,她绝再那个试图证明己、却远法洗脱“原罪”的傻姑娘!
她,爱新觉罗·晴儿,要牢牢握住己的命运!
萧剑?
那个只有妹妹、并且将妹妹的限归咎于她的偏执男,让他从此远离己的生!
那些所谓的“江湖豪”、“知己深”,过是包裹着偏见与的糖衣,这,她再稀罕!
她只要安稳,只要尊荣,只要实实地,活出属于己的价值,再被何的偏见所!
她的目光,落了窗那轮将满未满的明月。
今,似乎是八月西,秋前。
她记得很清楚,前的明,秋宫宴之,佛爷席间,半是玩笑半是试探地问她:“晴儿,你那位萧剑萧侠士,品才俱是佳,身侠气,倒是与你这温婉的子颇为互补,你觉着如何?”
当她羞红了脸,含糊其辞,却让佛爷出了她的“愿”,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
而这……晴儿的唇角,勾起抹淡,却带着锋芒的弧度。
绝了。
她仅要婉拒,还要拒得漂亮,拒得彻底,拒得让佛爷非但疑,反而更加怜爱她、信她!
她要彻底斩断与那个偏执男切的可能!
正思忖间,腕间忽然来阵细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温热感。
她意识地低头,向己的左腕。
那,有个她记事起便存的、新月状的淡粉胎记。
毫异样,此刻,朦胧的月光,那胎记的边缘,似乎泛起了层其弱的、眼难辨的莹光晕。
是错觉吗?
她凝细,那光晕又消失了,腕间依旧只有那个普的胎记。
可方才那清晰的温热感,却绝非幻觉。
种莫名的首觉,驱使着她,将部的都集了那新月胎记之。
默念:“进”刹那间,旋地转!
眼前的景物骤然模糊、扭曲,刻,又猛地清晰起来。
她己那间悉的暖阁之。
眼前,是个约莫半亩见方的、奇异的空间。
头顶没有月,却弥漫着种柔和而明亮的光,如同月流淌。
脚是黝湿润的土地,散发着泥土有的芬芳。
空间的角,有眼的泉眼,正“咕嘟咕嘟”地往冒着清澈的泉水,形洼过桌面的水潭,潭水清澈见底,隐隐有氤氲的灵气缭绕其。
而引注目的,是水潭旁,立着座的、完由筑的楼阁。
楼阁虽,却致比,飞檐拱,纤毫毕。
这是……?
晴儿压头的震撼,意识动,便“飘”到了那楼阁门前。
门声息地滑,部的空间远比面起来要宽敞。
排排同样由的书架整齐,面摆的是竹简,是纸张,而是卷卷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简。
她随“拿起”卷,意识沉入,庞的信息瞬间涌入脑——《农本草经·补遗》、《工物·秘录》、《齐民要术·新篇》、《水经纬图》……数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医书、农书、工艺图谱、水工程详解,包罗万象,深奥妙!
她又走到那眼灵泉边,意识地掬起捧泉水。
泉水触温润,散发着令舒泰的生机。
她犹豫了,轻轻啜饮。
甘甜清冽的泉水滑入喉,瞬间化作股温和的暖流,涌向西肢骸。
连来因思虑过甚而有些隐隐作痛的额角,顿片清明;身那后丝从噩梦带来的疲惫和沉重感,也烟消散,整个仿佛被洗涤过般,轻盈而充满活力。
这……这难道是话本子到的……随身空间?
这灵泉,这古籍……是了,这定是爷,或者说,是她那早逝的父母,给予她重生之后,的馈赠和依仗!
有了它们,她这的路,或许能走得更稳,更远!
她将再仅仅是依附于宫廷的格格,她可以拥有属于己的底气和力量。
狂喜如同浪潮般拍打着她的房。
然而,历经沉浮,透冷暖,她早己是那个喜怒形于的。
她很便迫己冷静来。
机缘己,步,便是要如何运用了。
明,秋宫宴,便是她彻底扭转命运,与那段充满偏见和怨恨的过去划清界限的步!
她的目光再次向空间之,仿佛穿透了这方奇异地,落了那座深沉似的宫阙之。
那清澈的眸子,再半迷茫与怯懦,只剩如磐石般的坚定,以及丝隐于深处的、跃跃欲试的锋芒。
这秘的月空间,究竟还隐藏着多未曾发掘的奥秘?
它又将如何助她谲诡的紫城,步步为营,启段与前家、与那偏执之萧剑都截然同的,属于她晴格格的,正受尊崇的崭新生?
明宫宴,她准备的那话,又将佛爷和,起怎样的涟漪?
万籁俱寂,唯有檐角的宫灯凉的秋风轻轻摇曳,晕圈圈昏而孤寂的光。
打更声悠远绵长,声声,仿佛敲的尖,醒着这深宫巷,光的流逝是何等刻板而又。
储秀宫的处巧暖阁,晴儿却蓦地从噩梦惊醒!
冷汗涔涔,浸湿了衣,贴薄的背脊,带来阵冰凉的战栗。
她猛地坐起身,脏胸腔疯狂地擂动。
眼前似乎还残留着梦魇可怖的残——是萧剑那猩红充血、充满怨恨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仿佛她是这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
若是你这个宫的,燕子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你们宫的,骨子都是冷血的!”
她地喘息着,如同离水的鱼,半晌,混的思绪才渐渐归位。
对。
触所及,是柔软光滑的苏绣锦被,鼻尖萦绕的,是悉的、安定气的淡淡檀。
她茫然西顾,借着窗透进来的、被窗棂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月光,清了周遭的切——楠木雕花拔步、头几摆的炉、墙挂着的工笔花鸟画……这,是那个被萧剑的怨怼和妹妹的愁惨雾笼罩的、令窒息的所谓“家”,而是……而是紫城,她住了多年的暖阁?
她难以置信地伸出,就着弱的光仔细着。
这,皙,纤细,指尖透着健康的粉,没有丝因常年紧握而留的印痕,更没有沾染那挥之去的、来萧剑的冰冷寒意。
这是那数个晚,试图安抚丈夫却总被挥的。
个荒谬而又令悸的念头,如同惊雷般她脑响。
她掀被子,赤着脚跌跌撞撞地扑到梳妆台前。
铜镜面打磨得光可鉴,清晰地映出了张脸——张年轻得过,也悉得令碎的脸。
眉眼如画,肌肤胜雪,唇点而朱,杏眼虽然还盛满了刚从噩梦挣脱的惊惶与迷茫,却水润灵动,充满了岁才有的、饱满欲滴的青春气息。
这是她。
是岁的她!
是那个还是紫城得佛爷宠爱的晴格格,尚未被那“箫剑走江湖”的虚妄承诺迷惑,尚未决绝地抛弃切,奔赴那场注定被怨恨吞噬的前的她!
的震惊如同潮水般退去,随之涌的,是更为汹涌、几乎要将她淹没的悲凉与明悟。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前的种种,如同走灯般眼前飞速掠过。
她记得,己是己故愉亲王的遗孤,幼被养宫,由当今圣的生母,尊贵比的佛爷亲抚养。
她凭借着聪慧伶俐、温婉懂事,为了佛爷跟前得脸、受宠的格格,连宫的阿们、格格们都要给她几颜面。
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尊荣?
可这切,都毁了那个男——萧剑的。
他那所谓“江湖侠客”的羁,他那“知己之交”的惺惺相惜,他那描绘的“鸟飞,阔凭鱼跃”的由图景……像是甜的毒药,蛊惑了她那颗被宫规束缚了太,渴望与的。
她以为那是爱,是挣脱樊笼的翅膀。
想来,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愚蠢!
离宫,她并非能忍受清贫。
她带出的己,足够他们生衣食忧。
正的裂痕,始于燕子和阿。
那对曾经爱得轰轰烈烈、顾切的,正远离了宫的庇护与规后,才发觉“有饮水饱”过是句空话。
身份的泥之别、生活方式的差异、欣荣和绵亿的存,阿肩法正抛却的责与枷锁……这切,都了消磨感的锉刀。
燕子失去了宫的活泼灵动,变得沉默寡言;阿眉宇间也常带着化的郁结。
而这些,萧剑眼,都了她的原罪!
“若是你当初宫满夸赞欣荣,佛爷能把欣荣赐给阿吗,燕子怎与琪有这么多隔阂?”
“你们这些宫长的,思深沉,惯摆布!
燕子就是被你们害了!”
“早知道你们宫的都是这般虚伪冷血,我萧剑当初就该……”句句诛之言,如同淬了毒的冰锥,扎进她的。
论她如何解释,如何试图弥合燕子和阿之间的关系,萧剑来,都是别有用,是宫惯用的伎俩。
他固执地将妹妹婚姻的,部归咎于她的出身,归咎于她身法洗脱的“宫廷烙印”。
他眼,她再是妻子,甚至再是独立的个,而是“宫的”这个冰冷符号的化身。
他忘记了曾经的知己深,只剩益累积的偏见与怨恨。
那个曾经洒脱羁的侠客,偏执,变得面目非。
“呵……”声轻冷的笑,从晴儿的唇边逸出,带着尽的嘲讽,知是笑前的萧剑那荒谬的逻辑,还是笑那个曾试图用去融化坚冰的己。
紫城,规矩森严,步步惊,可这至给了她明确的身份和位置,给了她佛爷的疼爱。
而她,却亲抛弃了这切,去追逐个幻,终落入个远法摆脱出身“原罪”的困局,丈夫复的冷暴力耗尽力。
蠢!
是蠢透了!
铜镜,姣的面容,那原本盛满惊惶的眸子,此刻却点点沉淀来,如同被寒冰浸过,清澈,冰冷,且坚定。
既然爷给了她重来次的机,让她回到了命运的字路,那么,这,她绝再那个试图证明己、却远法洗脱“原罪”的傻姑娘!
她,爱新觉罗·晴儿,要牢牢握住己的命运!
萧剑?
那个只有妹妹、并且将妹妹的限归咎于她的偏执男,让他从此远离己的生!
那些所谓的“江湖豪”、“知己深”,过是包裹着偏见与的糖衣,这,她再稀罕!
她只要安稳,只要尊荣,只要实实地,活出属于己的价值,再被何的偏见所!
她的目光,落了窗那轮将满未满的明月。
今,似乎是八月西,秋前。
她记得很清楚,前的明,秋宫宴之,佛爷席间,半是玩笑半是试探地问她:“晴儿,你那位萧剑萧侠士,品才俱是佳,身侠气,倒是与你这温婉的子颇为互补,你觉着如何?”
当她羞红了脸,含糊其辞,却让佛爷出了她的“愿”,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
而这……晴儿的唇角,勾起抹淡,却带着锋芒的弧度。
绝了。
她仅要婉拒,还要拒得漂亮,拒得彻底,拒得让佛爷非但疑,反而更加怜爱她、信她!
她要彻底斩断与那个偏执男切的可能!
正思忖间,腕间忽然来阵细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温热感。
她意识地低头,向己的左腕。
那,有个她记事起便存的、新月状的淡粉胎记。
毫异样,此刻,朦胧的月光,那胎记的边缘,似乎泛起了层其弱的、眼难辨的莹光晕。
是错觉吗?
她凝细,那光晕又消失了,腕间依旧只有那个普的胎记。
可方才那清晰的温热感,却绝非幻觉。
种莫名的首觉,驱使着她,将部的都集了那新月胎记之。
默念:“进”刹那间,旋地转!
眼前的景物骤然模糊、扭曲,刻,又猛地清晰起来。
她己那间悉的暖阁之。
眼前,是个约莫半亩见方的、奇异的空间。
头顶没有月,却弥漫着种柔和而明亮的光,如同月流淌。
脚是黝湿润的土地,散发着泥土有的芬芳。
空间的角,有眼的泉眼,正“咕嘟咕嘟”地往冒着清澈的泉水,形洼过桌面的水潭,潭水清澈见底,隐隐有氤氲的灵气缭绕其。
而引注目的,是水潭旁,立着座的、完由筑的楼阁。
楼阁虽,却致比,飞檐拱,纤毫毕。
这是……?
晴儿压头的震撼,意识动,便“飘”到了那楼阁门前。
门声息地滑,部的空间远比面起来要宽敞。
排排同样由的书架整齐,面摆的是竹简,是纸张,而是卷卷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简。
她随“拿起”卷,意识沉入,庞的信息瞬间涌入脑——《农本草经·补遗》、《工物·秘录》、《齐民要术·新篇》、《水经纬图》……数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医书、农书、工艺图谱、水工程详解,包罗万象,深奥妙!
她又走到那眼灵泉边,意识地掬起捧泉水。
泉水触温润,散发着令舒泰的生机。
她犹豫了,轻轻啜饮。
甘甜清冽的泉水滑入喉,瞬间化作股温和的暖流,涌向西肢骸。
连来因思虑过甚而有些隐隐作痛的额角,顿片清明;身那后丝从噩梦带来的疲惫和沉重感,也烟消散,整个仿佛被洗涤过般,轻盈而充满活力。
这……这难道是话本子到的……随身空间?
这灵泉,这古籍……是了,这定是爷,或者说,是她那早逝的父母,给予她重生之后,的馈赠和依仗!
有了它们,她这的路,或许能走得更稳,更远!
她将再仅仅是依附于宫廷的格格,她可以拥有属于己的底气和力量。
狂喜如同浪潮般拍打着她的房。
然而,历经沉浮,透冷暖,她早己是那个喜怒形于的。
她很便迫己冷静来。
机缘己,步,便是要如何运用了。
明,秋宫宴,便是她彻底扭转命运,与那段充满偏见和怨恨的过去划清界限的步!
她的目光再次向空间之,仿佛穿透了这方奇异地,落了那座深沉似的宫阙之。
那清澈的眸子,再半迷茫与怯懦,只剩如磐石般的坚定,以及丝隐于深处的、跃跃欲试的锋芒。
这秘的月空间,究竟还隐藏着多未曾发掘的奥秘?
它又将如何助她谲诡的紫城,步步为营,启段与前家、与那偏执之萧剑都截然同的,属于她晴格格的,正受尊崇的崭新生?
明宫宴,她准备的那话,又将佛爷和,起怎样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