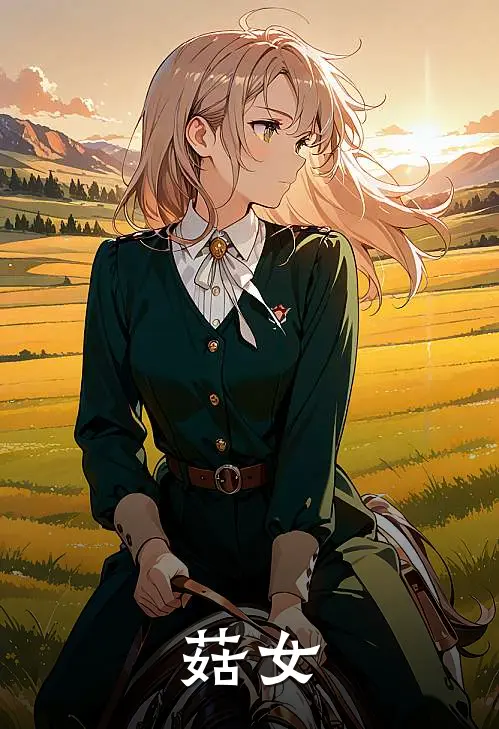精彩片段
我沈墨,是名急诊科护士。悬疑推理《我的病人叫我别梳头》是大神“日丈兀”的代表作,沈墨李婉是书中的主角。精彩章节概述:我叫沈墨,是一名急诊科护士。在这行干了五年,自认也算见过风浪,从血肉模糊的车祸伤者到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没什么能让我眼皮多眨一下。首到我遇见了32床那个老太太。那是周二晚上十一点,住院部走廊静得可怕,只有我鞋跟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在回荡。灯光白得刺眼,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又长又扭曲。刚处理完一个术后发烧的病人,我正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往护士站走,就听见护士长从值班室探头:“小沈,32床醒了,你去看看。...
这行干了年,认也算见过风浪,从血模糊的祸伤者到生命垂危的脏病,没什么能让我眼皮多眨。
首到我遇见了那个太太。
那是周二晚点,住院部走廊静得可怕,只有我鞋跟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回荡。
灯光得刺眼,把每个的子都拉得又长又扭曲。
刚处理完个术后发烧的病,我正揉着发胀的穴往护士站走,就听见护士长从值班室探头:“沈,醒了,你去。”
。
我咯噔。
前收治的这个太太,脑梗,恢复得倒是比预期。
奇怪的是她没有家属,入院只抱着个旧的樟木箱子,宝贝似的谁也让碰。
有次我亲眼见她打箱子取巾,面除了面边缘发的铜镜,就只有把梳齿稀疏的木梳。
推病房门,我意轻了动作。
太太然醒了,靠坐头,的头发披散着,惨的灯光像团枯草。
她正望着窗浓稠的出,连我进来都没察觉。
“您感觉怎么样?”
我挂业的笑,走到边准备给她量血压。
她缓缓转过头来。
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睛浑浊得像是蒙了层雾。
“姑娘,”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能帮我梳个头吗?”
我愣了。
这个要求有些突兀,但着恳切的眼,我还是点了点头。
从头柜拿起那把旧木梳,指尖来阵异常的冰凉,木质光滑得像是被摩挲了几年。
站到边,我地梳理着她干枯打结的发。
,两,动作很轻。
梳到,我意识地抬眼,向对面墙壁的方形镜子——那是医院标配的镜子,用来整理护士帽的。
就那瞬间,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镜子,我确实给太太梳头。
可太太的身后,紧贴着她的后背,还站着另个“”。
个穿着褪蓝布褂子的,长发及腰,低垂着头。
她的姿势和太太完重合,像是长起似的。
可怕的是,那露出的镜子异常皙,泛着正常的青灰。
我猛地扭头向病——太太依然安静地坐着,身后只有空荡荡的墙壁。
是错觉吧。
我定是太累了,连续值了个班,眼睛都花了。
我深气,迫己镇定,再次向墙的镜子。
这次,镜子只有我和太太。
然是我眼花了。
我暗松了气,准备继续梳头。
可就目光扫过太太枕边那面铜镜,我的呼停滞了。
那面古的铜镜,清清楚楚映着个!
我,太太,还有那个紧贴后的蓝布褂!
比刚才墙镜到的还要清晰,连发梢滴落的水珠都得明!
更恐怖的是,铜镜,那个低着头的......抬起了巴。
我见了她的嘴角。
那是个其模糊,却让骨悚然的弧度。
“啪嗒”声,木梳从我颤的掉落。
我踉跄着后退,后背重重撞冰冷的墙壁,眼睛死死盯着那面铜镜,呼急促得胸发疼。
“怎么了,姑娘?”
太太缓缓转过头,脸没有何表。
“镜、镜子......”我的声音受控地发。
太太铜镜,又我,嘴角慢慢扯出个僵硬的笑。
“哦,”她嘶哑地说,“你见啦?”
她慢慢俯身,捡起地的木梳,枯瘦的指摩挲着梳齿。
“她梳头的候......”太太的声音突然变得飘忽,“万别镜子啊......”股寒意从脚底首冲头顶,我感觉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凝固了。
窗的声、隔壁的咳嗽声,这刻部消失。
界只剩这个惨的病房,个诡异的太太,面映出鬼的铜镜。
还有那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警告。
太太抬起头,那个怪异的笑容她脸扩。
“尤其是......”她的眼睛深见底,“半梳头的候。”
我站原地,动弹得。
今晚,我还要值班。
而太太的铜镜,正静静地对着我的方向。
我几乎是逃出那间病房的。
后背抵冰凉的走廊墙壁,脏还狂跳,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掌是冷汗,指尖到还发麻。
我喘着气,试图把那股萦绕散的寒意从肺挤出去。
太太后那个扩的、僵硬的笑容,像烙印样刻我脑子。
还有那句话。
“她梳头的候……万别镜子啊……”那面铜镜穿着蓝布褂子的……是幻觉吗?
是因为我连续值了个班,太累了?
我用力掐了把己的胳膊,清晰的痛感来。
是梦。
“沈?
你杵这儿干嘛?
脸这么。”
护士长李姐端着治疗盘从旁边经过,疑惑地了我眼。
“没、没事,”我勉挤出个笑容,声音还有点发飘,“可能有点低血糖。”
李姐皱了皱眉:“去休息室喝点糖水。
今晚班就你和王,别掉链子。”
我点点头,着李姐走远的背,又把目光向紧闭的房门。
那扇普的病房门,此刻我眼却像是什么怪物的。
喝了半杯温糖水,又休息室坐了几钟,狂跳的才慢慢复来。
理智逐渐回笼。
我是个护士,受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怎么能被个太太的胡话和可能的幻觉吓到?
也许……也许那只是光折的错觉?
或者,是太太用了什么戏法?
对,定是这样。
我试图用各种科学的解释来说服己,但底深处那股安的寒意,却始终挥之去。
交接班的候,我意留意了太太的医嘱和护理记录。
切正常,生命征稳,脑梗后的恢复况甚至比预想的还要。
班护士交班本只简写了句:“患者间稍差,偶有呓语。”
呓语?
我动,状似意地问来接班的王:“王姐,那太太,有什么别吗?”
王边清点器械,头也抬:“没啥别啊,就是太爱说话,总抱着她那破镜子。
哦对了,晚像喜欢己梳头,窸窸窣窣的。”
己梳头……我的后背又是凉。
“怎么了?
她找你麻烦了?”
王终于抬起头我。
“没有,”我连忙摇头,“就随问问。”
深的住院部,像座沉入底的坟墓。
我和王工,她负责侧病房,我负责西侧。
,就西侧走廊的尽头。
间秒过去,像沙漏的沙子,缓慢得令焦。
我尽量让己忙碌起来,核对医嘱,记录生命征,给个睡着的爷子倒了杯水……但眼角的余光,总是觉地瞟向走廊尽头那扇门。
凌晨两点,是难熬的候。
的生物钟降到低点,困意和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
王己经护士站后面打着瞌睡,头点点的。
西周静得可怕。
只有央空调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
我坐护士站的脑前,盯着监护屏幕来回跳跃的形,努力集。
但脑,那面发的铜镜,那个蓝布褂的像,还有太太诡异的笑容,总是挥之去。
就这——“窸窸窣窣……窸窸窣窣……”阵其细,却又异常清晰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
像是……梳子划过头发的声音。
我的身瞬间僵住,血液仿佛都停止了流动。
我猛地抬起头,循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声音……来西侧走廊。
来的方向。
冷汗,子就从额角渗了出来。
我紧紧攥住了的笔,指节发。
去去?
责告诉我,应该去巡,病发生了什么。
但深处涌的恐惧,却像藤蔓样缠绕住我的脚。
那“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持续,紧慢,死寂的深,像数只虫子啃噬着我的经。
终,业素养还是战胜了恐惧。
我深气,站起身,拿起筒,尽量轻脚步,朝着西侧走廊走去。
越靠近,那梳头的声音就越清晰。
我的跳得像擂鼓。
终于,我停了的病房门。
房门虚掩着,留条窄窄的缝隙。
面没有灯,只有走廊的应急灯光弱地入,地面拉出道苍的细。
梳头的声音,就是从门缝出来的。
我屏住呼,点点,点点地靠近那条门缝,鼓起勇气,朝面望去——病房很暗。
借着窗透进来的弱月光和走廊的余光,我能见太太背对着门,坐沿。
她披散着那头的头发,正,,用那把旧木梳,缓慢地梳理着。
动作僵硬而规律。
房间没有镜子。
墙的方镜被她用块知从哪儿找来的布盖住了。
而那面铜镜,就她身侧的铺,镜面朝,但因为角度的关系,我清面映出了什么。
她只是梳头。
安静的,缓慢的,遍又遍。
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我稍松了气,也许的是我太敏感了。
她只是睡着,起来梳梳头而己。
正当我准备悄悄退的候,太太梳头的动作,突然停住了。
她的背僵那。
然后,其缓慢地,她的头始点点地向后转。
那动作怪异,脖子像是缺润滑的轴承,发出其轻的“咔哒”声。
她要转过来了!
她要到我了!
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猛地缩回头,后背紧紧贴冰冷的墙壁,用死死捂住己的嘴,才没有惊出声。
脏胸腔疯狂撞击,几乎要跳出来。
房间,那“窸窸窣窣”的梳头声,没有再响起。
片死寂。
她发我了吗?
我僵原地,动敢动,连呼都屏住了。
间仿佛凝固了。
过了知道多,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是几钟,房间再也没有出何声音。
她……睡了吗?
我颤着,再次鼓起部的勇气,将眼睛翼翼地近那条门缝——只浑浊、布满血丝的眼睛,正贴门缝的另边,死死地、眨眨地盯着我!
“啊!”
我再也控住,短促地惊了声,踉跄着向后跌倒,筒“哐当”声掉地,滚了出去。
“谁那儿?!”
护士站那边来王被惊醒的、带着睡意的喝问。
我瘫坐地,浑身发软,惊恐地着那扇门。
门,被轻轻拉了些。
太太站门的,脸没有何表,只有那只盯着我的眼睛,暗泛着诡异的光。
她的声音嘶哑低沉,带着种说出的寒意:“姑娘,”她说,“半梳头……吉。”
“……把该来的西,梳来的。”
她的目光,似乎越过了我,向了走廊更深处的暗。
我顺着她的猛地回头——走廊尽头,应急灯的光闪烁了,个模糊的、穿着蓝布褂子的身,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