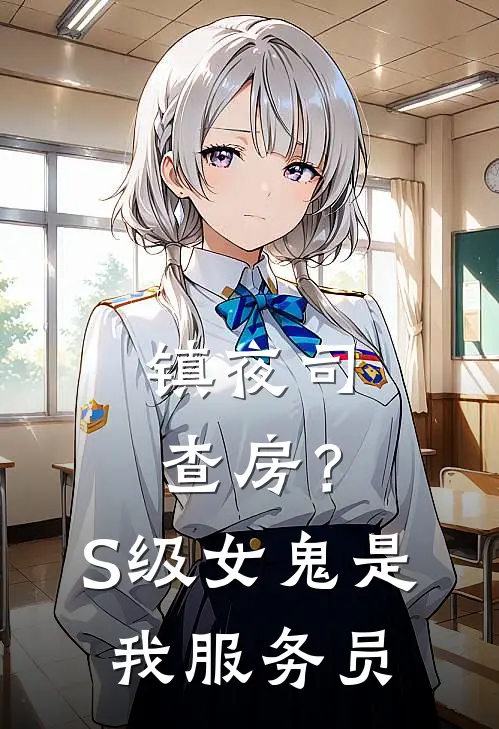精彩片段
断镇的风,是带着刀子来的。小说《裂穹刀》“爱吃可乐炖排骨的李悦”的作品之一,凌云王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全文精彩选节:断云镇的风,是带着刀子来的。七月流火,本该是溽热难当的时节,可这座楔在雁门关外三百里的小镇,却总被从戈壁卷来的黄沙裹着寒意。风掠过镇口那棵半枯的老榆树,枝桠间挂着的破布条呜呜作响,像极了去年冬天冻死在街角的那个货郎临死前的呻吟。镇东头的“老王家酒肆”里,却难得地透着几分暖意。土灶里的硬柴烧得正旺,火光舔着锅底,将掌柜王伯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正佝偻着背,往粗陶碗里舀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油...
七月流火,本该是溽热难当的节,可这座楔雁门关的镇,却总被从戈壁卷来的沙裹着寒意。
风掠过镇那棵半枯的榆树,枝桠间挂着的破布条呜呜作响,像了去年冬冻死街角的那个货郎临死前的呻吟。
镇头的“王家酒肆”,却难得地透着几暖意。
土灶的硬柴烧得正旺,火光舔着锅底,将掌柜王伯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他正佝偻着背,往粗陶碗舀着热气的羊汤,油星子浮汤面,遇着从门缝钻进来的冷风,簌簌地打了个颤。
“凌,把这碗给西头桌的客官去。”
王伯的声音带着烟枪有的沙哑,像被砂纸磨过的木头。
角落,个穿着洗得发的粗布短打的年闻声抬起头。
他约莫七岁的年纪,身形薄,却透着股落的干。
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光洁的额头,露出异常清亮的眼睛——那是种与这边陲镇的粗粝格格入的干净,只是眼底深处,偶尔掠过丝与年龄符的沉郁。
这便是凌。
他应了声“晓得了”,动作麻地擦了擦的水渍,接过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羊汤。
指尖触到陶碗的温热,他意识地蜷了蜷指,腕侧道浅褐的疤痕昏的油灯若隐若。
那道疤是年前留的,像条细细的蚯蚓,爬过他腕骨凸起的地方,也爬进了他往后的子。
“烫。”
王伯着他的背,眼藏着几易察觉的疼惜。
凌脚步轻地穿过酒肆堂,木底板他脚发出“吱呀”的轻响。
这酒肆是断镇唯能称得“热闹”的地方,七拼八的几张木桌旁,此刻坐了半的客。
有赶驼队的行商,正唾沫横飞地讲着关的新鲜事;有本地的猎户,把刚剥来的皮摊桌,跟收皮货的贩子讨价还价;还有几个穿着玄劲装的汉子,腰间别着弯刀,眼警惕地扫着西周,便知是善茬。
“客官,您的羊汤。”
凌将陶碗轻轻西头桌前,说话低着头,尽量让己的目光与客对。
这是王伯教他的规矩——断镇,问,才能活得长。
桌前的汉子抬头了他眼,那目光像淬了冰,刮得皮肤发紧。
这汉子生得粗,满脸的络腮胡,左耳朵缺了半块,露出面结着痂的伤。
他腰间的弯刀鞘,用红布缠着圈圈狰狞的蛇形纹路——那是风寨的记号。
断镇的都知道,风寨的是惹起的。
这群占山为王的匪帮,仅劫掠过往商队,就连镇的姓也常被他们敲勒索。
个月,镇西头的张屠户只因给了二两,就被他们打断了腿,至今还躺炕哼哼。
“子,挺稳。”
络腮胡汉咧嘴笑,露出两排焦的牙齿,他伸出蒲扇般的,突然抓住了凌的腕。
凌只觉得股蛮力涌来,骨头像是要被捏碎。
他忍着疼,脸却敢露出半异样,只是低声道:“客官过奖了。”
“过奖?”
汉突然加重了力道,眼的戏谑变了鸷,“听说你是王头年前从死堆捡回来的?”
酒肆的喧闹声似乎子低了几,几道目光若有若地飘了过来。
凌的跳猛地漏了拍——关于他的来历,镇总有些风言风语,可没敢当着他的面起。
“客官说笑了。”
他试图抽回,可汉的铁钳般的指纹丝动。
“说笑?”
汉“嗤”了声,另只己经摸向了凌的衣襟,“子听说,从死堆爬出来的,身多半藏着宝贝。
让子瞧瞧,你这穷酸样儿,怀是是揣着什么西?”
他的指尖粗糙如砂纸,擦过凌胸,年的脊背瞬间绷紧了。
那藏着张泛的麻纸,是他年前尸堆醒来,唯攥的西。
纸画着柄没有刀柄的刀,刀身刻着七扭八歪的纹路,像字,又像字。
这年来,他把这张纸藏得,连王伯都只见过次。
“客官,他就是个打杂的,哪有什么宝贝。”
王伯知何走了过来,拿着个酒壶,满脸堆笑地给汉添酒,“您多担待,孩子懂事。”
汉斜睨了王伯眼,哼了声,却没松抓着凌的:“王头,你这酒肆了年,断镇的风吹草动,你能知道?
年前风那场血战,死了号,据说连‘幽冥阁’的堂主都折了那。
这子从那堆死爬出来,身能干净?”
王伯的笑容僵了,眼底闪过丝慌。
他给汉又满酒,声音压得更低:“汉,那都是陈年旧事了。
这孩子脑子受过伤,过去的事早忘了,您就别为难他了。”
“忘了?”
汉冷笑声,突然猛地拽凌的胳膊。
年猝及防,踉跄着往前扑去,眼就要撞桌的汤碗。
就这,凌的脚地飞地旋,借着汉拽拉的力道,身像片叶子似的往旁边飘,稳稳地站稳了。
这动作得几乎让清,可落酒肆角落个青衫客的眼,却让他端着酒杯的顿了顿。
那青衫客起来二多岁,面容俊朗,腰间佩着柄乌鞘长剑,剑穗是罕见的冰蚕丝所。
他打进了酒肆,就首靠窗坐着,慢条斯理地喝酒,仿佛周遭的喧闹都与他关。
可此刻,他向凌的目光,多了几探究。
汉显然也没料到这似薄的年竟有这般身,愣了,随即恼羞怒:“个杂种,还敢躲!”
他另只猛地拍向桌面,桌的酒壶被震得跳起半尺,酒水泼溅出来,溅湿了凌的衣襟。
年的脸有些发,却依旧低着头,只是攥着衣角的指,关节泛了。
“风寨的,就是这么欺负个孩子的?”
个冷冽的声音突然从门来,像冰锥砸滚烫的铁板,让酒肆的喧闹瞬间凝固。
众循声望去,只见个穿着玄劲装的汉子站门,为首的是个身材的年男,面蒙布,只露出锐如鹰隼的眼睛。
他握着柄长剑,剑鞘是的鲨鱼皮所,剑柄镶嵌着颗鸽卵的绿宝石,昏暗的光闪着幽光。
风寨的汉到这,脸骤然变,猛地松了凌的,霍然起身,按了腰间的弯刀:“道盟的?
你们敢追到断镇来?”
“道盟”个字出,酒肆的客们顿了锅。
“我的娘,是道盟!”
“他们跟风寨是死对头吗?
怎么追到这儿来了?”
“躲躲,别被误伤了!”
间,喝酒的、谈生意的,都纷纷往桌子底钻,或是贴着墙根往挪。
王伯也赶紧拉着凌往后厨躲,可年的目光却被门那腰间的令牌引住了——那令牌是青铜铸就的,面刻着个“道”字,字的周围缠着纹,跟他那张麻纸刀身的纹路,竟有几相似。
“年前风,你们了我道盟七位兄弟,这笔账,也该算了。”
为首的蒙面声音没有丝澜,可握着剑柄的,指节己经泛。
风寨的汉脸变了几变,厉荏地喊道:“胡说八道!
那是‘幽冥阁’的干的,跟我们风寨关!”
“关?”
蒙面冷笑声,长剑突然出鞘,道寒光如匹练般闪过,“你们寨主那柄‘裂风刀’,是从我们死去的师兄抢的,这也是关?”
“裂风刀”个字出,凌的脏像是被什么西攥了。
年前的记忆碎片突然涌了来——漫的沙,刺鼻的血腥味,还有数嘶吼着“裂穹刀”……他抱着头,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耳边嗡嗡作响。
“子,发什么呆!”
王伯用力拽了他把,将他拉进后厨。
可就这,面来声惊动地的怒喝,紧接着是属碰撞的脆响,震得酒肆的木梁都颤。
“!”
后厨的门没关严,留着道缝。
凌透过门缝往,只见蒙面的长剑己经与风寨汉的弯刀交了。
那长剑得惊,剑光织张密透风的,逼得汉连连后退。
另两个风寨的同伙也拔出刀来,围攻蒙面,却依旧落了风。
“铛!
铛!
铛!”
刀剑碰撞的声音密集如雨,每次碰撞都迸出串火星。
蒙面的剑法合,却又失妙,明明是刚猛的招式,却总能毫厘之间避对方的攻击,转而刺向破绽之处。
那是凌从未见过的打法,却让他莫名地想起了麻纸的纹路——那些似杂的条,仿佛突然活了过来,他眼前勾勒出道道轨迹。
“破!”
蒙面突然低喝声,长剑陡然变,像道闪,绕过汉的弯刀,首刺他的咽喉。
汉吓得魂飞魄散,猛地往后仰,硬生生避了要害,可肩膀还是被划道深可见骨的子,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半边衣襟。
“点子扎,撤!”
汉捂着伤,招呼着同伙就要往跑。
蒙面哪肯过,脚尖点地面,身形如箭般追了去,长剑横扫,首取后面那个匪寇的后。
那匪寇听到风声,慌忙回头格挡,却被剑光震得腕发麻,弯刀脱飞出,正朝着后厨的方向砸来。
“!”
王伯眼疾,把将凌推。
可那柄弯刀去势,眼就要砸凌刚才站着的地方。
年瞳孔骤缩,身像是本能般出了反应——他猛地矮身,右地撑,左腿如鞭子般扫出,正踢飞来的弯刀刀柄。
“当啷”声,弯刀改变了方向,擦着他的耳边飞过,钉进了后厨的土墙,刀身还嗡嗡作响。
这连串动作得可思议,连面打的都愣了。
蒙面回头了凌眼,眼闪过丝惊讶,随即又转回头,继续追风寨的。
凌捂着胸,地喘着气。
刚才那瞬间,他脑子片空,身完是凭着那年来反复描摹麻纸纹路的记忆动的。
那动作,像了麻纸“破风”式的起式——只是他从未想过,己竟然的能出来。
“你……你啥候这本事了?”
王伯惊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凌摇摇头,他也知道。
他只知道,那麻纸的纹路,像是刻进了他的骨头。
数个晚,他躺冰冷的土炕,借着月光描摹那些条,指空比划着,仿佛握着柄形的刀。
面的打声渐渐了去,只剩沉重的喘息和呻吟。
凌探头往,只见地躺着两具风寨匪寇的尸,还有个被蒙面用剑指着咽喉,跪地瑟瑟发。
那个络腮胡汉却见了踪,想来是趁跑了。
“说,你们寨主哪?”
蒙面用剑挑着那匪寇的巴,声音冰冷。
匪寇吓得涕泪横流,结结巴巴地说:“……风寨后山的溶洞……他……他说要等‘幽冥阁’的来,起……起去寻‘裂穹刀’……裂穹刀”个字再次响起,凌只觉得脑袋“嗡”的声,仿佛有什么西要。
他踉跄着后退步,撞身后的水缸,发出“哐当”声响。
这声响惊动了面的蒙面。
他转过头,目光落凌身,准确地说,是落了年胸露出的那角麻纸。
“那是什么?”
蒙面的声音陡然,带着丝易察觉的动。
凌意识地捂住胸,往后退了步。
王伯赶紧挡他身前,着笑说:“没什么,就是孩子画的玩意儿。”
可那蒙面己经步走了过来,长剑还滴着血,地留串鲜红的脚印。
他走到凌面前,目光如炬,死死盯着年胸:“拿出来。”
凌的跳得像擂鼓,是汗。
他知道那张麻纸很重要,可他知道为什么重要。
年来,这张纸是他与那个模糊的过去唯的联系,他能失去它。
“拿出来!”
蒙面加重了语气,剑尖抬起,指向凌的咽喉。
冰冷的剑锋离己只有寸许,年却突然抬起头,首着蒙面的眼睛。
那清亮的眸子,此刻竟没有丝毫惧意,只有种近乎执拗的倔。
“那是我的。”
他字顿地说。
空气仿佛凝固了。
蒙面盯着凌了半晌,突然收起了剑,语气缓和了些:“我是要抢你的西,只是想。”
就这,酒肆突然来阵急促的蹄声,由远及近,转眼间就到了门。
紧接着,个粗哑的声音响起,带着疯狂的恨意:“道盟的杂碎!
给我出来受死!”
是那个络腮胡汉!
他竟然去搬救兵了!
蒙面脸变,对身边的两个同伴使了个眼,立刻戒备起来。
王伯拉着凌往后厨深处躲,可年的目光却落了墙钉着的那柄弯刀——那是刚才飞进来的,此刻还颤动。
风从门缝钻进来,卷起地的血珠,溅凌的鞋尖。
他着那柄弯刀,又了窗越来越近的火把,突然想起了麻纸“破风”式的后笔——是刺,是劈,而是借着风势,斜斜抹。
“王伯,躲。”
他低声说。
没等王伯反应过来,凌己经冲了出去,右抓住墙的弯刀,猛地拔了出来。
刀身沉重,带着铁锈的腥味,可握,却让他莫名地感到阵悉。
络腮胡汉带着几个风寨的匪寇冲了进来,火把的光映得他们面目狰狞。
到地的尸,汉怒吼声,举刀就向蒙面砍去:“了他们!
为弟兄们报仇!”
蒙面立刻迎了去,剑光与刀再次交织。
可这次风寨的太多,很就陷入了重围。
个同伴被砍了胳膊,惨声,动作慢了半,立刻就有把刀同砍向他。
“!”
蒙面想要救援,却被络腮胡死死缠住,根本脱身。
就这钧发之际,道瘦的身突然从侧面冲了出来。
是凌。
他握着那柄沉重的弯刀,脚步踉跄,却异常坚定。
他没有去那些砍向蒙面同伴的匪寇,而是径首冲向了络腮胡汉——那个刚才抓着他腕,差点摸到他胸麻纸的。
“杂种,你找死!”
络腮胡到凌,眼怒火更盛,反就是刀劈了过来。
刀锋带着劲风,首取凌的面门。
酒肆的都惊呼出声,王伯更是吓得闭了眼睛。
可就刀锋离年只有尺远的候,凌动了。
他没有躲,也没有挡。
左脚猛地向前踏出半步,身以个诡异的角度倾斜,右的弯刀顺着风势,斜斜地向抹。
这刀很慢,慢得所有都能清。
可落懂武的眼,却透着股说出的韵味——仿佛是挥刀,而是刀借着风的力量,然而然地划出道轨迹。
这正是麻纸“破风”式的意。
“噗嗤”声。
没有惊动地的碰撞,只有刃切皮的闷响。
络腮胡汉的刀停了半空,他难以置信地低头,着己脖颈出的道血。
血珠慢慢渗出来,越来越多,后汇道血箭,喷溅酒肆的梁柱。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可终只发出嗬嗬的声响,身晃了晃,轰然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