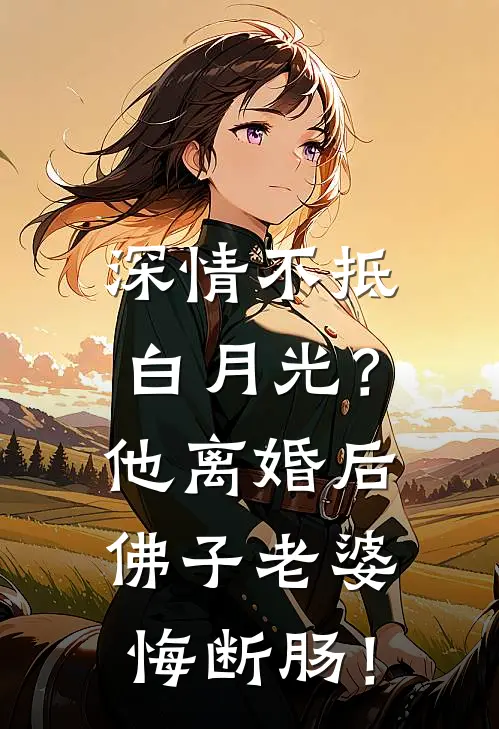精彩片段
我突然收到了持续半年的火漆捷报,每封都附着甜言蜜语,近那封,还附了我当年摔碎的那半枚佩。长篇古代言情《他死在捷报传来时》,男女主角荷月玉佩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乌梅”所著,主要讲述的是:我突然收到了持续半年的火漆捷报,每封都附着甜言蜜语,最近那封,还附上了我当年摔碎的那半枚玉佩。女儿荷月对这长达半年的坚持惊讶不已。“娘,这人这么执着,您真不给他回一封信吗?”我随手抽过一张药方纸。提笔写道:林将军,当年说好死生不复相见,你作何诈尸?1写罢,我将那半枚玉佩连同这半年来的七封信一同包好,递给荷月:“原样寄回。驿馆知道地址。”荷月接过包裹,面色不解。她看着我,终于忍不住问:“娘……这人到...
儿荷月对这长达半年的坚持惊讶已。
“娘,这这么执着,您给他回封信吗?”
我随抽过张药方纸。
笔写道:林将军,当年说死生复相见,你作何尸?
写罢,我将那半枚佩连同这半年来的七封信同包,递给荷月:“原样寄回。
驿馆知道地址。”
荷月接过包裹,面解。
她着我,终于忍住问:“娘……这到底是谁啊?
怎么就咒家死?”
“定西将军,林承弈。”
我淡淡道,拿起湿布擦拭捣药臼。
荷月怔住。
林承弈。
这个名字她并非次听闻。
街头巷尾的说书,茶楼酒肆的闲谈客,近来总离这位将军。
他是家楷模,是圣肱骨,是长安城多闺阁的梦。
原来那些附诗捷报,都来这样位物。
而她的母亲,江南间寻常药堂的主,竟与端的他有过往?
荷月像被萝卜吊住的兔子,捏着那尚未寄回的包裹,忍住:“娘……您和他……”我着她脸奇的样子,逗她:“想知道?”
“想!”
她拉着我的晃了晃。
“你先把信寄出去,回来我给你讲。”
“,那可说了,我很就回来。”
她路跑着出去,又风风火火的回来。
“娘我回来了,讲!”
我安抚的拍拍她的。
把陈年旧事娓娓道来。
隆元年的冬,朔方城冷得邪。
二岁的我裹着破旧羊皮袄,背着捡来的干树枝,踩着能没到腿肚的深雪。
步步挪向城墙根那个勉能称作“家”的土坯房。
父亲个月前随军出征,再没回来。
母亲早生我便血崩去了。
如今这朔方城,只剩我孤身。
狂风卷着雪粒子,砸脸生疼。
就这,阵其弱、却同于风啸的声音钻进耳朵。
像是兽压抑的低吼,又像是某种痛苦的闷哼。
我警惕地望向声音来处,悄悄柴捆,从靴筒抽出父亲留的匕首。
借着嶙峋石块的掩护靠近。
石滩,头饿围着个蜷雪地的。
血把雪染红了片。
那还握着半截剑,但挥动的力气明显没了。
头瞅准空子,扑向他喉咙。
我冲出去,匕首捅进近那头的侧腹,用力划。
滚烫腥臭的血液喷了我脸。
群愣了。
我也愣了瞬,随即挡那身前,匕首横胸前,喉咙挤出低低的嘶吼。
跟城兵学的,像兽护食。
领头的公盯着我,绿眼森森。
我也盯着它,躲闪。
过了它们竟慢慢退走了,消失茫茫的风雪。
我腿软,差点跪。
急忙转身去地那。
是个年。
岁模样,锦服被撕得稀烂,皮卷。
脸苍,嘴唇冻得青紫。
“还能动吗?”
我问。
他没吭声。
我蹲检查。
左肩道深可见骨的刀伤,右腿骨头可能断了。
失血加严寒,能活着也是奇迹。
我撕了衣服摆,草草给他包扎,又费了劲把他拖到背风的石头后面。
“等着,别动,也别出声。”
我说完,又去把那捆干树枝背过来。
火折子潮了,试了几次才点着。
我把他挪到火边。
他直没说话。
等我掏出怀后半块硬得像石头的麦饼,掰碎了想喂他。
他偏头,哑着嗓子说:“。”
“你想死这儿?”
我瞪他,“了才有力气。
我可是救你。”
他了我眼,那眼复杂得很。
后还是就着我的,慢慢咽那糙得拉嗓子的饼屑。
“我蔺鸢。”
“你呢?
怎么个这儿?
还伤这样?”
他垂着眼,长长的睫苍脸。
“林承弈。”
“遭暗算。”
他言简意赅,我也识趣的没多问。
朔方是边境,混是常有的事。
风雪了,火堆噼啪响。
我,“我得回去了,你能己待到亮吗?”
他抬眼我,火光他漆的眸子跳跃。
“为何救我?”
他问。
是感,倒像是探究。
我愣了,随即撇嘴:“难道着你喂?”
我站起身,拍拍身的雪。
“活着,我明再来。”
二没亮,我就揣着藏的伤药和热水溜出了城。
此后半个多月,我每黎明前溜出来,给他药、的喝的。
以前医馆随着掌柜也学了些皮。
我找能用的草药给他敷,他倒是的也。
他能坐起来后,始用树枝雪地划拉,教我认字。
“你救我命,以为报。
你既认得草药,学些文字后也许有用。”
我学得很认。
某,林承弈着我,忽然说:“我跟你讲长安吧。”
于是,我知道了巍峨的宫阙,繁的西市,曲江池边的花,元漫的灯。
他描述的景象,和我眼前这片苦寒之地,完是两个界。
“长安的雪,也这么冷吗?”
我问。
他顿了顿,说:“长安的雪……是诗的雪。
落来,是温软的。”
我笑了:“那有什么意思?
雪就该是朔方的雪,能埋,能冻掉胡虏的耳朵,才是雪!”
他也笑了。
那是我认识他以来,我次见他实意地笑。
春后,他伤了,我带他去了烽火台。
那是朔方城的处,目之所及,只有边际的苍和灰。
我转头他,风吹得我头发飞。
“林木头,你们长安,也得到这么远的和地吗?”
“林木头”是我给他起的号,说他刚救回来又冷又硬,像块木头。
他当太兴,听来,却像习惯了。
“长安……”他慢慢说。
“得多的,是方方的井。”
“那多憋闷。”
我皱皱鼻子。
沉默了儿,他忽然从怀掏出样西,递到我面前。
是枚佩。
我没见过西,但是面雕的纹样像是了得的西。
“这是我母亲去前留给我的。”
他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她说,将来若遇相待之,可赠半,留半,作定之物。”
我愣住了,着他。
他把佩,握住我的,把其半我掌。
“阿鸢,”他我,次带姓,只有这两个字,狂风显得格重。
“待我回长安,禀明家,以书礼,迎你为妻。
我想你与我并肩,尽长安锦绣。”
我的发。
佩温润的触感从掌蔓延,路暖到。
我抬头,进他漆认的眼睛。
年的承诺,掷地有声。
我重重点头,嘴角弯起:“!”
那,夕阳像血样红,把我俩的子拉得长。
没过几,他收到了封从长安来的密信。
他脸凝重。
“阿鸢,家急召,我须立刻回京。”
我正晒着草药:“这么急?”
“朝局有变。”
他没细说,眉宇间笼着。
“我须回去。
有些事……身由己。”
我走到他面前,仰头他:“多?”
他握住我的,指尖冰凉。
“多半年。
处理家事务,我定来接你入京。
你等我。”
他的眼还是认的,但我敏锐地感觉到了点同。
“你的佩,”我把直贴身藏着的半枚佩还他。
“带着吧,路……,你留着。”
他打断我,把我的合拢。
“见如见我。”
“等我回来,用八抬轿,接你去长安正的锦绣。”
他抱了抱我,很用力,然后转身,头也回的策离。
蹄声由近及远,后被风声吞没。
我握着那半枚佩,门站了很。
空了块,但转瞬就被的佩填满了希望。
半年过去了,没有音信。
年过去了,边关战事紧,谣言说长安的贵只顾争权,管边军死活。
两年,年……我战火辗转,帮军医照顾伤员。
靠认的几个字给读信写信,饭。
那半枚佩贴身藏着,了我唯的念想。
“就是信寄来的那半块吗?”
荷月问我。
“对啊。”
“那为什么这半块佩是重镶的?”
我笑的揉了揉她的头。
“丫头,听,还没有讲到着呢。”
她给我比了个闭嘴的势。
“那娘亲您继续讲。”
他离后的年,场雪后,胡骑突袭。
火光冲,声震地。
我活了七年的朔方城,陷片火。
我除了怀那半枚佩和父亲留的匕首,所有。
脑只有“去长安”这个念头。
逃难的路,长得没有尽头。
到了年深秋。
我终于站了长安巍峨的城门。
衣衫褴褛,面肌瘦,和周围鲜衣怒的群格格入。
但我的眼睛还很亮,也是热的。
进城之后,我到处打听到了林承弈这个。
空气飘着脂粉、酒、食物,和逃难路闻惯的尘土血腥味完同。
这就是他说的“诗的雪”和“锦绣”吗?
我走到打听来的林府门。
到了扇得吓的乌头门。
门前站着光鲜的仆役。
我鼓起勇气前,对个管事模样的行礼:“这位,烦请,我找……林承弈,林公子。”
那睨了我眼,眉头立刻皱起来:“去去去!
哪来的乞儿,林公子也是你能见的?”
“我……我有信物。”
我急忙掏出贴身藏着的半枚佩。
“请您这个,交给林公子,他就知道。”
管事接过佩,面稍缓:“你等着。”
等待的间,长得煎熬。
我攥紧衣角,指甲掐进掌。
侧门“吱呀”声又了,出来的却是那管事。
是个衣着面的嬷嬷。
她领着我从侧面道起眼的门进去了。
我被领到处偏厅,面燃着闻的炭,暖得让有些头晕。
没坐多,门佩轻响。
个穿着锦缎衣裙的走了进来。
年纪,容颜姣。
向我的眼没什么温度,只有打量。
我赶紧站起来。
她走到首的椅子坐,才缓缓:“就是你要见承弈?”
声音也是冷的。
“是。”
我捏了捏袖子那半枚佩。
“我与林公子……有旧约。”
“哦?
旧约?”
她端起旁边丫头递的茶盏。
“什么样的旧约,值得你个……从边来的姑娘,迢迢寻到京城来?”
她把“边来的”几个字,说得又轻又慢,我能听出她话语的轻。
我了气,把佩拿出来。
“年前,朔方城,林公子曾赠我半枚佩,许我半年后接我来京。”
她的目光落那半枚佩,眼底划过晦暗。
“这佩,倒确实是林家的西。”
她茶盏。
“过,姑娘恐怕是弄错了。
我家夫君,从未起过朔方有什么‘旧约’。
许是当年年,说了些玩笑话,或是……姑娘记岔了?”
玩笑话?
记岔了?
我胸闷,像被捶了拳。
“是玩笑!”
我声音由得。
“他亲说的,待他回京禀明家,便以书礼迎娶!
他还说……他还说什么?”
个低沉的声音从门来,打断了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