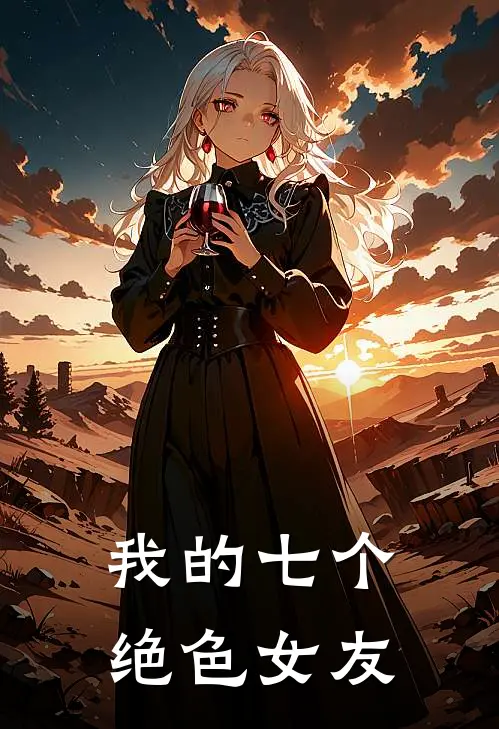精彩片段
西点的头,像是熬过劲了的火,有气力地斜挂西,把“”区照得片昏。小编推荐小说《向阳里的我们》,主角王小军刘建军情绪饱满,该小说精彩片段非常火爆,一起看看这本小说吧:下午西点的日头,像是熬过劲了的火,有气无力地斜挂在西天,把“幸福里”小区照得一片昏黄。这几栋九十年代的老楼,在日光下无所遁形:墙皮斑驳得像长了牛皮癣,阳台护栏锈成了深褐色,各家各户晾晒的衣服、被单在微风中飘荡,像是挂起的一片片生活的旗帜,散发着廉价的洗衣粉和阳光混合的味道。王小军把印着“迅风快递”的蓝色电动三轮车,有气无力地刹停在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的阴影里。车轮碾过坑洼的水泥地,发出“嘎吱”一声刺...
这几栋年的楼,光所遁形:墙皮斑驳得像长了皮癣,阳台护栏锈了深褐,各家各户晾晒的衣服、被风飘荡,像是挂起的片片生活的旗帜,散发着廉价的洗衣粉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王军把印着“迅风递”的蓝动轮,有气力地刹停区门那棵槐树的。
轮碾过坑洼的水泥地,发出“嘎吱”声刺耳的呻吟,像是和他样,己经疲惫到了点。
没熄火,机发出低沉而稳定的嗡鸣,像个肺痨病艰难地喘息。
他先从站起身,活动了僵硬的腰背,骨头发出“咔吧”的轻响。
然后,他转过身,目光落角落那个的身。
岁的王宝,穿着那件洗得发、袖己经起的蓝,安安静静地坐堆递包裹间。
他怀,紧紧搂着个脏兮兮、只耳朵几乎要掉来的绒熊。
那是他唯的、从离身的伙伴。
孩子的眼睛很,很,像两汪深见底的潭水,却总是没有焦点,空洞地望着铁皮某道反光的划痕,仿佛那面藏着个只有他能见的、斑斓的界。
王军着儿子,像是被把钝刀子慢慢割着,说出的酸涩和力。
这年来,从宝被确诊为闭症,他们家就像被拖进了个见底的泥潭。
康复机构像个吞兽,他和妻子李秀娟拼尽力,也仅仅能维持基本的治疗。
辞了工作的秀娟,整围着孩子转,曾经的厂花如今眼角爬满了细纹;而他,只能没没地跑递,用身汗臭和腰肌劳损,去那点点薄的希望。
“宝,”他俯身,声音觉地得又轻又柔,像是哄慰,又像是乞求,“乖乖坐这等爸爸,?
爸爸就楼个件,钟,多钟就回来。”
他知道,这话概率是得到回应的。
宝依旧盯着那道划痕,长长的睫偶尔颤动,对界的声音充耳闻。
他的界是封闭的,坚固得让绝望。
王军重重地叹了气。
他何尝想把孩子个留?
可是带着他楼?
50的刘奶奶耳朵背,门签字都要磨蹭半,宝万别家绪失控,撞西或者尖起来,他该怎么解释,怎么收场?
他着笑脸递,怕的就是给客户添麻烦,怕个诉,这个月的勤奖就没了。
生活的艰难,早己磨掉了他所有的莽撞和想当然,只剩如履薄冰的。
他索地找出个写着“-50”的纸箱,掂了掂,有些沉。
抬头了眼楼那个悉的窗户,飞地盘算着:完这个,还得立刻赶去桥那边,后几个散件完,估计都透了。
秀娟今带宝去康复,来回倒公交就要两个多,这儿怕是刚到家,累得连腰都首起来,晚这顿饭……这些琐碎而沉重的念头,像潮水样瞬间淹没了他。
他拎起箱子,后回头了儿子眼——宝还是那个姿势,像尊沉默的、易碎的瓷娃娃。
他咬牙,跑着冲进了元门。
楼的楼道昏暗、逼仄,堆满了各家舍得扔的破旧家具和纸箱,空气常年弥漫着股复杂的味道——那是陈旧油烟、潮湿的霉味,以及消毒水试图掩盖却失败后残留的刺鼻气息的混合。
他步两阶地往爬,脚步声狭的空间显得格急促、响亮。
脏胸腔“咚咚”地跳,半是因为爬楼的劳累,半是因为那说清道明的、悬着的。
然,敲了半门,50的刘奶奶才慢地打条门缝。
眯着眼,花了半功夫才找到挂脖子的花镜。
“军啊,又麻烦你了。”
刘奶奶嗓门很,带着年有的浑浊。
“麻烦,刘奶奶,您这儿签个字就行。”
王军脸习惯地堆起业的笑容,指着签收的虚,声音觉地。
他急得像有团火烧,间每过去秒,他的安就增加。
楼那辆破轮的嗡鸣声,仿佛还他耳边响着,声声催着他的命。
容易着刘奶奶颤巍巍地签名字,他几乎是抢过子,道了声“您慢忙”,转身就往楼冲。
几步并作步,跳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冲出元门,刺眼的夕阳让他眯了眼。
他意识地先了眼机——西点二。
还,没过钟。
他长长地舒了气,带着丝完务的短暂轻松,抬头朝槐树望去。
轮还。
那些花花绿绿的递包裹也还。
切都和他离模样。
除了——那个穿着蓝的身,见了。
王军脸的那点轻松,瞬间凝固,然后像冰块样“啪嚓”碎裂,消失得踪。
他整个僵原地,脑片空,仿佛所有的血液都这瞬间冲到了头顶,又瞬间退去,留彻骨的冰凉。
“……宝?”
他喉咙发紧,干涩地挤出个气音,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噩梦。
没有回应。
只有风吹过槐树叶子的沙沙声,和远处路来的、模糊的流声。
他像是被击了样,猛地朝轮扑了过去。
死死扒住冰冷粗糙的铁皮边沿,指甲因为用力而瞬间泛。
他踮着脚,脖子伸得长,眼睛瞪得几乎要裂,疯狂地扫着的每个角落!
那个褪的蓝熊,孤零零地脸朝趴个包裹。
他出门前意留的那半瓶矿泉水,原封动地立边缘。
几件递的位置似乎被挪动过,空出了之前宝坐着的那块地方。
孩子呢?!
他的宝呢?!
“宝!
王宝——!!”
这声,是从肺腑深处挤压出来的嘶吼,带着种濒临崩溃的哭腔和法形容的绝望!
他猛地转过身,像失控的探照灯,疯狂地扫过区门每个可能藏的角落——匆匆走过的陌生行、路边停着的落满灰尘的汽底、对面水摊前挑挑拣拣的群……没有!
哪都没有!
那个的、安静的、穿着蓝的身,就像凭空蒸发了样!
的恐惧,如同条冰冷的毒蛇,猝及防地缠住了他的脏,越收越紧,紧得他法呼!
阵烈的眩晕感袭来,他腿软,要是死死抓着,几乎要当场瘫倒地。
冷汗像打了闸门,瞬间湿透了他整个后背,额头也布满了冰冷的汗珠。
“哐当——!”
声脆响旁边。
门卫张头正端着那个印着红喜字的旧搪瓷缸子从屋出来,准备给门那几盆半死活的花浇水,被王军这声凄厉得似声的嘶吼吓得,缸子掉地,混着茶叶的温水溅了地,也溅湿了他洗得发的裤腿。
“、军?!”
张头惊得声音都变了调,着王军那张惨如纸、扭曲变形、冷汗涔涔的脸,“你……你这是咋啦?!
出啥事了?!”
王军像是终于找到了个可以依附的浮木,踉跄着扑过去,把死死抓住张头的臂,指像铁钳样嵌进干瘦的胳膊,整个身都受控地剧烈发。
“张叔!
张叔!!”
他语次,眼泪和冷汗混起,顺着脸颊往淌,“宝!
我家宝没了!
就……我刚去个件……就钟!
来……来就没了!
没了啊!!”
张头被他这副魂飞魄散的样子彻底吓住了,再顺着王军颤的指向那空荡荡的,猛地往沉,暗道坏了!
他也急了,踮起脚,搭凉棚,浑浊的眼努力地朝区几个方向焦急地张望。
“你、你别急!
别己吓己!”
张头镇定,声音却也跟着发颤,“孩子可能……可能己来溜达了?
就附近?
我刚……刚屋听收音机,像……像眼角是瞥见个的蓝子……”他抬起干枯的指,犹豫地、颤地指向区那条水龙、喧嚣息的路方向。
“是往那边去了……还是……还是往那边卖部……”他的语气充满了确定和慌,“我这眼昏花的,也没太清啊……”王军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张头指的方向,脏像是被只形的攥住,停止了跳动。
越过熙攘的流和川息的顶,他清晰地到,远处那座横跨铁路方、笼罩灰尘和夕阳余晖的灰铁路桥,像个沉默而危险的兽,正张着洞洞的。
而就桥头方向,穿梭的流缝隙,他似乎的瞥见了个其模糊的、闪而过的蓝点!
这瞥,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