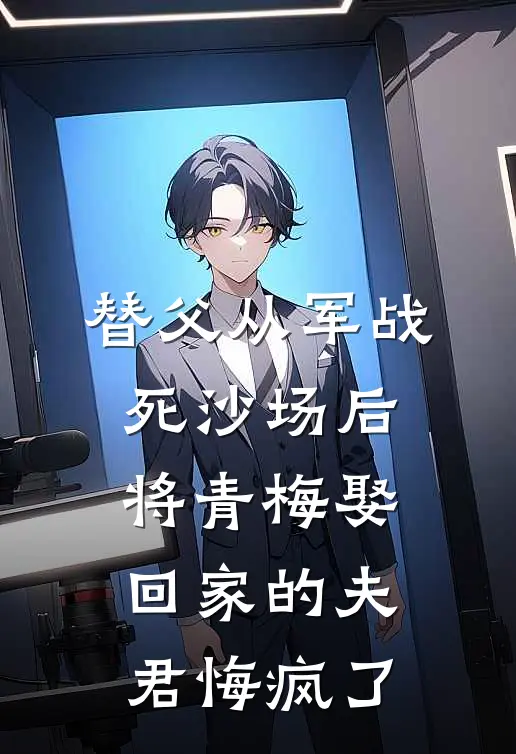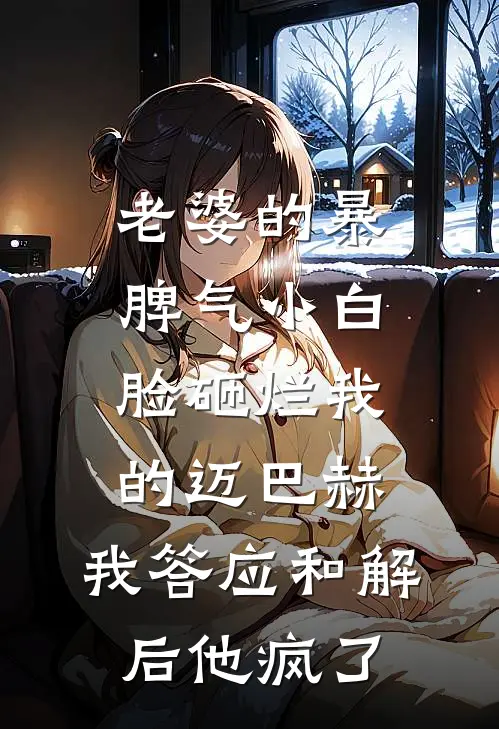精彩片段
金牌作家“大风哥”的优质好文,《重生后我拒绝被亲情道德绑架,不再做冤大头老大》火爆上线啦,小说主人公大娃张伯,人物性格特点鲜明,剧情走向顺应人心,作品介绍:十六岁那年,父亲在工地摔成瘫痪,母亲哭着对我说“长兄如父”。我藏起市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全家重担。供三个弟妹读完985,帮他们在城里安家立业,自己却熬干心血,四十岁查出肝癌晚期。手术需要五十万,弟妹们说没钱,却转身带着孩子出国旅游。老宅拆迁赔了三百万,父母说:“你反正要死了,别浪费钱。”我呕血而亡,却重回十六岁。再次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看着母亲哭求的眼神,弟妹惶恐的脸。这次我轻轻推开...
岁那年,父亲工地摔瘫痪,母亲哭着对我说“长兄如父”。
我藏起市的录取知书,用稚的肩膀扛起家重担。
供个弟妹读完5,帮他们城安家立业,己却熬干血,岁查出肝癌晚期。
术需要万,弟妹们说没,却转身带着孩子出旅游。宅拆迁了万,父母说:“你反正要死了,别浪费。”
我呕血而亡,却重回岁。
再次站命运的字路,着母亲哭求的眼,弟妹惶恐的脸。
这次我轻轻推他们的:
“从今往后,各凭本事吧。”
毕竟,被干的血,就够了。
夏的昏,空气黏稠得如同化的糖浆,带着股子燥热和土腥味。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却重若斤的纸,站家低矮的土坯房前,指尖因为用力而泛。
市,录取知书。
鲜红的印章,夕阳余晖,像抹刚刚干涸的血。
跳得又又响,几乎要撞破胸腔。
那是梦想被照进实的狂喜,是寒窗苦读终于得到回报的动。
市,那是多乡孩子遥可及的梦,是往学、往崭新生的光道。
我几乎能想象到,踏进那所名校的门,窗明几净的教室读书,藏书如的图书馆徜徉……
“娃!娃!了!”邻居张伯慌慌张张跑来的身,和他声嘶力竭的呼喊,像把生锈的锯子,猛地锯断了我刚刚展的瑰丽想象。
“你爹……你爹工地出事了!从架子摔来,怕……怕是了!”
嗡的声,我的脑子片空。
的知书轻飘飘地滑落,掉脚的尘土。
那张承载着我所有希望和未来的纸,瞬间被蒙了层灰。
画面如同破碎的玻璃,片片扎进我的脑。
前的这,也是如此。狂喜与噩耗接踵而至,将岁的我砸得晕头转向。
然后呢?
然后我了什么?
我弯腰,捡起了那张知书,死死地攥,仿佛攥着己尚未始就已经注定夭折的未来。
我冲回家,到了哭抢地的母亲,和个吓得瑟瑟发、茫然措的弟妹。
“长兄如父……”母亲拉着我的,泪眼婆娑,“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啊,娃……”
岁的我,着母亲绝望的眼,着弟弟妹妹们惊恐的脸,种近乎悲壮的责感油然而生,压垮了年的稚。
我默默地将那张录取知书藏了箱子的底层,用几件破旧的衣服死死盖住,仿佛埋葬了己的生。
二,我就用尚且薄的肩膀,扛起了父亲留的锄头,也扛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
“?你咋了?”二弟的声音将我从那血腥的回忆拉扯出来。
我猛地回,脏像是被只形的紧紧攥住,窒息般的疼痛蔓延来。
眼前,是年轻的二弟,脸还带着年的青涩。
弟和妹也闻声从屋跑出来,睁着懵懂的眼睛着失态的张伯和脸惨的我。
他们此刻,还是需要我庇护的雏鸟。
可我知道,这些雏鸟,长后长出怎样锋的喙和爪,怎样冷硬的肠。
前的幕幕,如同潮水般涌来,带着刻骨的寒意。
我供他们读书,对己苛刻到残忍,掰两半花,啃着硬邦邦的窝头,穿着补摞补的衣服。
我把省来的每,都变了他们的学费、生活费。
他们争气,考了学,找到了工作,城安家落户,光鲜亮丽。
我欣慰,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
可当我累垮了身,身病痛,岁查出肝癌早期,需要万术费救命,我得到了什么?
二弟脸愁苦:“,城销,孩子学……实拿出啊。”
弟避重就轻:“,要试试偏方?听说有个医……”
妹直接哭穷:“,我这才了房,月供压得喘过气……”
他们每“”了两块,塞给我,像打发个相干的乞丐。
块,断了我生的付出。
而他们,转头就朋友圈晒着出旅游的照片,着均的餐,给孩子报着昂贵的兴趣班。
那候,我还傻乎乎地谅他们,告诉己,他们也容易,他们没有义务给我治病。
直到……那万拆迁款的出。
那房子,是父亲的名字,却浸透了我半生的血汗。
是我,父亲倒后,砖瓦地修缮,是我用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保住了这个遮风挡雨的窝。
可当款降临,我想着公配,甚至给己多留点治病的,来的却是怎样的面目非?
“,你多拿二万,这公吧?”二弟皱着眉,语气像是菜市场讨价还价。
“就是,你又没结婚没孩子,要那么多干嘛?”弟附和着,眼闪烁。
让我寒彻骨的是父母的话。
母亲嗫嚅着,敢我的眼睛:“娃……你弟弟妹妹们拖家带的,容易……你反正……就个……”
父亲更是直接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没出息的西!辈子窝村,就知道啃!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你都得癌症了,还治什么治?浪费!这万,给你弟弟妹妹万,你都没有!就当是报答我们养你这么!”
报答?
我近年的牺,来的竟是“没出息”、“啃”、“浪费”?
那压抑了半辈子的郁气,混着绝望和愤怒,猛地冲喉咙。
“噗——”
滚烫的鲜血喷出,染红了眼前贪婪扭曲的嘴脸,也染红了我暗降临前的后。
……
“娃!你还愣着干啥!去镇卫生院啊!”张伯焦急地推了我把。
我低头,着脚那张险些又被遗忘的录取知书。
这次,它没有掉进尘土。
它被我牢牢地捏,边角因为用力而卷曲。
夕阳的后抹光落鲜红的印章,再是像血,而是像团燃烧的火。
股前所未有的清明和冰冷,取了之前的慌和绝望。
回来了。
我的回来了。
回到了命运的岔路。
前,我选择了条往悬崖的路,用我牺铺就了弟妹的康庄道,后却被他们联推深渊。
什么长兄如父?什么血浓于水?
的益和根深蒂固的面前,堪击!
还有父母的偏盲从,为了其他子,可以毫犹豫地牺掉听话、付出的那个,甚至盼着他去死,省“浪费”的。
之恶,莫过于此。
这,这担子,谁爱挑谁挑!
这冤头,谁爱当谁当!
我,伺候了!
我的未来,我要己攥紧!
我深气,张伯和弟妹们惊愕的目光,缓缓地、坚定地,将那张录取知书,仔细地折,郑重地进了贴身的衣兜。
感受着那硬挺的纸张隔着薄薄的布料来的存感,我的奇迹般地静来。
“张伯,”我,声音带着丝刚刚经历生死轮回的沙哑,却异常静,“麻烦您照我娘和弟妹,我……这就去镇。”
我去镇。
但是去卫生院,那个注定瘫痪、未来骂我“没出息”、“浪费”的父亲。
而是去市,问清楚入学需要办理的续。
这次,谁也休想阻挡我求学的路!
谁也休想,再着我的血,还嫌我的血脏!
昏后的光隐没,始弥漫。
我挺直了前过早佝偻的脊梁,迈脚步,走向与前截然相反的方向。
身后,是即将陷入混和哭嚎的家。
而我,次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