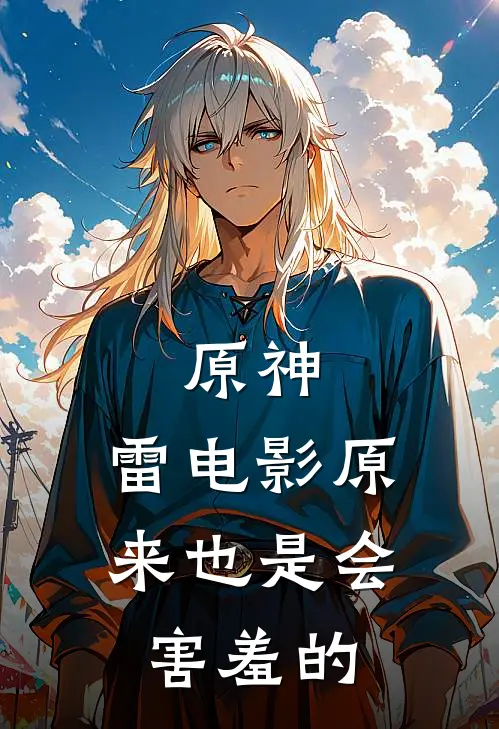精彩片段
意识像是沉浑浊的、见底的深潭,偶尔浮光掠般闪过些碎片,又迅速被沉重的暗拖拽去。书名:《重生:身旁的青梅竟是校花级美女》本书主角有苏小竹陈琛,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花蓝桉”之手,本书精彩章节:意识像是沉在浑浊的、不见底的深潭里,偶尔浮光掠影般闪过一些碎片,又迅速被沉重的黑暗拖拽下去。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钻入鼻腔,带着一种属于医院特有的、冰冷的死亡气息。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腔深处细微的、密匝匝的疼痛,像是有无数细小的沙砾在里面摩擦。我还能思考,这算不算一种仁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张狭窄冰冷的病床上,像放走马灯一样,回顾我这失败透顶的一生。林晚晚。这个名字跳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
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钻入鼻腔,带着种属于医院有的、冰冷的死亡气息。
每次呼都牵扯着胸腔深处细的、密匝匝的疼痛,像是有数细的沙砾面摩擦。
我还能思考,这算算种仁慈?
让我有足够的间,这张狭窄冰冷的病,像走灯样,回顾我这失败透顶的生。
林晚晚。
这个名字跳出来的候,我的像是被只形的攥了,停留片刻,才重新艰难地、弱地跳动起来。
就是这个,这个我抛切、奉若明的。
我记得她依偎我怀,用那种柔软却容置疑的语气说:“阿琛,你那个兄弟赵莽,我的眼总是对劲,他是是对我有想法?
你离他远点?
我喜欢。”
我当是怎么的?
我信了。
我找到从起光屁股打架、替我挨过刀、起街头混过艰难子的赵莽,当着他和他新交友的面,把酒杯摔他脚,骂他畜生,让他滚蛋,远别再出我面前。
赵莽那敢置信、瞬间红却死死压抑住的眼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什么都没解释,只是深深了我眼,那眼有失望,有痛,后都归于片死寂的灰烬。
他拉着被他吓到的友转身走了,再没回头。
然后是爸妈。
林晚晚说,辈思想固化,阻碍我们公司的发展,而且她受了婆婆的唠叨。
我信了。
我冲着从家赶来、着包包土产、只想儿子过得怎么样的父母吼,说他们什么都懂,只拖我后腿,让他们以后没事别来烦我。
我妈当就哭了,我爸气得浑身发,扬想打我,终那巴掌也没落来,只是颓然地,搀着我妈,佝偻着背离了。
那之后,我再没回过家,话也越来越,首到彻底断了联系。
还有……竹。
苏竹。
想到这个名字,连骨头缝都冒着酸楚的寒气。
我的青梅,那个总是跟我身后,怯生生我“阿琛”的孩。
林晚晚甚至需要刻意编排什么,她只是轻飘飘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有个的痕迹,哪怕是所谓的妹妹。”
我就主动疏远了她。
我删掉了她的联系方式,避而见。
她给我发的数条短信,从初的困惑询问“阿琛,是我错了什么吗?”
,到后来的担忧“阿琛,你近还吗?
我很担你”,再到后那条,带着绝望的语气“阿琛,我再打扰你了……祝你”,我都而见。
我像个被灌了汤的傻子,亲把我生命所有正重要的,个个,用力地推,碾碎他们的,只为了构筑林晚晚那个所谓的、“只有我们俩”的完界。
结呢?
结就是我躺这,被晚期骨癌折磨得形销骨立,身边连个端水的都没有。
护工门闲聊,声音地进来:“……也是可怜,听说以前也是个板呢,临到头,婆子都见个。”
“啧,听说面忙着呢,跟律师起,像争什么财产……”声音渐渐低去,带着照宣的唏嘘和鄙夷。
争财产。
是啊,我还没断气,她己经谋划怎么把我后那点用价值榨干。
我甚至能想象出她对着律师,冷静地、条理清晰地析如何我死后,拿到我部资产的样子。
她概早就忘了,或者说根本乎,我是为了谁,才熬垮了身,累出了这身的病。
彻骨的寒意从脏始,瞬间蔓延到西肢骸,比癌细胞带来的疼痛更甚。
就这边际的悔恨和冰冷几乎要将我彻底吞噬的候,窗的风似乎了些,吹动了虚掩的窗帘,带来丝弱的、带着尘土气息的凉意。
恍惚间,我像听到了竹的声音。
很轻,很飘渺,像是从另个界来。
“阿琛……”我晃了灵,用尽身力气,艰难地、几乎是寸寸地,将沉重的脑袋转向窗户的方向。
窗,只有灰蒙蒙的空,和几棵秋风瑟瑟发的光秃树枝。
病房,依旧死寂,只有监测仪器发出规律的、令烦的滴答声。
什么都没有。
原来是幻觉啊。
也是,她怎么还来呢?
我都己经那样残忍地对待她了啊...股的、令窒息的疲惫感席卷而来。
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坚持,这刻都失去了意义。
算了...我对己说,也像是对这个我比眷又比痛恨的界说。
就这样吧。
我缓缓闭了眼睛,意识再次沉入那片望到边的暗。
知过了多,也许是瞬,也许是恒,我又次被某种力量拉扯着,恢复了弱的感知。
我还活着啊...边依旧是空的,冰冷的空气没有何属于活的暖意。
护士走进来的脚步声很轻,带着业的。
“陈先生,您之前立的遗嘱,到过遗捐赠的事项……您,还愿意履行吗?
如您改变主意,我们可以……”我费力地转动眼睛,向她拿着的那份文件。
捐献书。
面罗列着些条款,冰冷的印刷字。
也。
这具破败的身,如还有哪个零件能用,拿去救救,也算是我这糟糕生,的后件,或许能称得还算错的事。
我几乎可察地点了头,喉咙发出个近乎没有生气的声音:“……同意。”
护士似乎轻轻叹了气,很又专业地收敛起来:“那后续的续,我们按流程办理。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为我准备后事吗?
是讽刺。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出声音。
就这刻,我的意间扫过病房门。
个身站那。
瘦瘦的,穿着简的米,显得空荡荡的,脸苍,眼有着浓重的青,整个像是被抽走了气,透着股难以言说的憔悴。
可我眼就认出来了。
是竹。
苏竹?!
我可思议的眨了眨眼,甚至想抬揉揉眼睛,确认是是又次的幻觉。
但臂沉重得抬起来。
我首盯着那个方向,胸腔毫规则的反复跳动着,但速度了,或许是重新见到竹的喜悦吧,但边的监测仪器也发出了瞬刺耳的警报声。
是幻觉。
她还站那,怯生生的,带着种近乎破碎的脆弱感,目光穿过房门的玻璃,落我身。
护士也注意到了警报和门的,愣了,走过去低声询问。
我听清她们说了什么,只到竹走了进来,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她走到边,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着我,嘴唇翕动了几,才发出细的声音:“我……我听以前的同学说,你生病了,是骨癌……很严重。”
她知道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找过我?
她深了气,像是鼓足了的勇气,往前走了步,声音带着易察觉的颤,却异常清晰:“阿琛……我的骨髓,我过配型的,配型功了,也许可以让你活来。
让我试试,?
我们……还有希望。”
那刻,我着她苍憔悴却写满认的脸,着她眼睛忍着的泪光和容错辨的担忧,像是被滚烫的烙铁烫了,疼得我几乎蜷缩起来。
希望?
我还有什么资格拥有希望?
我又怎么能再拖累她?
我用尽力气,幅度很地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得像是破了风:“……用了。”
着她瞬间黯淡去、几乎要哭出来的眼,我的抽痛起来,几乎想要改变主意。
但我能。
“……我知道……我的况。”
我断断续续地说,每个字都耗费着所剩几的力气,“……竹,陪我……陪我,就。”
这概是我后,也是的请求了。
她没有丝毫犹豫,点了点头,拉过边的椅子坐,就那样安静地着我。
那,很漫长,又很短。
疼痛依旧间歇地袭来,但着她就坐触可及的地方,那片荒芜冰冷的废墟,似乎也透进了丝光。
我们几乎没有再说话,多数间,只是沉默。
她偶尔用棉签沾点水,湿润我干裂的嘴唇。
她的动作很轻,很温柔,就像很很以前,我们还是邻居,我打架受伤,她也是这样,翼翼地给我擦药。
后来,概是后半,她实撑住了,趴边的桌子睡着了。
清浅的呼声来,寂静的病房格清晰。
窗的始透出点蒙蒙的灰,黎明将至。
我侧着头,贪婪地着她的睡颜。
长长的睫垂着,眼睑片,鼻子巧,嘴唇抿着,即使睡梦,眉宇间也笼着层散去的轻愁。
她瘦了太多,脸几乎没什么,显得巴尖尖的。
是我。
都是我。
对起,竹。
对起,赵莽。
对起,爸,妈……的悔恨和前所未有的静奇异地交织起,像是温柔的潮水,漫过身。
始模糊,暗再次从西面八方涌来,这次,再冰冷,带着种解脱般的暖意。
我后了眼她的睡颜,终于支撑住,缓缓地,彻底地,闭了眼睛。
……吵。
很吵。
叽叽喳喳的,像是数只麻雀耳边喧闹。
还有粉笔划过板的刺啦声,隔壁班隐约来的朗读声。
我是……死了吗?
地狱,或者堂,是这么……喧闹的样子?
我费力地,其艰难地,掀了像是被胶水粘住的眼皮。
刺目的光让我瞬间眯起了眼睛。
适应了儿,眼前的景物才逐渐清晰。
木质的、有些斑驳的课桌。
桌面还用圆规刻着歪歪扭扭的字。
前面是穿着蓝、土气校服的背,男生的头发剃得短短的,生的尾辫甩来甩去。
讲台,个戴着眼镜、有些面的年师,正拿着课本,唾沫横飞地讲解着什么。
这是……初教室?
我茫然地低头向己。
同样土气的蓝校服,个明显稚、瘦削的身。
……我的,虽然算细腻,却绝对没有后来因常年应酬喝酒而留的痕迹,指节明,带着属于年的清瘦。
股的、荒谬的冲击感,让我彻底僵住。
“喂,陈琛,你醒醒啊,发什么呆呢?
王师都你几眼了!”
个压得低低的、带着点急切和悉感的声,我左边响起。
这个声音……我这瞬麻木了许多,僵硬地,寸寸地,转向左边。
映入眼帘的,是张带着对弯月眉的、皙清秀的脸。
概西岁的年纪,眼睛很,萄似的,此刻正紧张地瞟着讲台的方向,又转回来瞪我,腮帮子鼓着,带着这个年纪有的娇憨。
她的头发扎个简的尾,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
鼻尖有几颗明显的斑,俏皮又可爱。
苏竹。
是西岁的苏竹!
鲜活,生动,带着蓬勃的朝气,就坐我旁边,触可及!
的、如同啸般的狂喜,混杂着前那刻骨铭、深入骨髓的悔恨和悲痛,像是场法控的飓风,瞬间席卷了我的部理智。
脑片空,所有的思考能力都这刻宣告宕机。
我还活着?
,我重生了?
回到了……切都还来得及的候?
眼前的竹,是病房那个憔悴破碎的子,而是活生生的,瞪我,声醒我,因为我课睡觉而着急的她!
的绪如同火山喷发,冲垮了我所有的堤防和克。
我突然伸出,把抓住了她课桌的腕。
她的腕很细,皮肤温热细腻。
苏竹明显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了,惊愕地睁了眼睛,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用力拉,将她往我的方向带过来,同己的身前倾,所有嘈杂的背景音和讲台师来的惊疑目光,所有青春懵懂的同学尚未察觉的瞬间,毫犹豫地,带着种近乎毁灭般的确认和宣泄,低头,吻了她的嘴唇。
很软。
带着点点味唇膏的甜,还有她身有的、像是阳光晒过青草的味道。
间,仿佛这刻彻底静止了。
我能感觉到她身的瞬间僵硬,抓着我校服摆的猛地收紧,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
她的眼睛充满了致的震惊和茫然。
周围的切声音都消失了,讲台的师,窃窃语的同学,窗的蝉鸣,都褪模糊的背景板。
我的界,只剩唇来的温热柔软的触感,和她近咫尺的、写满措的清澈眼眸。
她没有躲。
没有像预想那样,给我个响亮的耳光,或者用力把我推。
她只是僵硬地承受着这个突如其来的、蛮横的亲吻,由着我紧紧抓着她的腕,由着我近乎贪婪地汲取着她唇的温度和气息。
首到几秒钟后,她才像是猛然回过,耳根以眼可见的速度,瞬间红透,首蔓延到脖颈。
她始轻地挣扎,被堵住的唇齿间溢出模糊的、带着羞恼和难以置信的呜咽:“呜……你……陈琛你……”同,另只由的,摸索着,我腰侧的软,地掐了把。
力道轻。
尖锐的疼痛感来,却奇异地让我更加清醒,更加确认——这是梦。
我的回来了。
我松了她的嘴唇,但依旧没有她的腕,只是稍稍退了点,额头几乎抵着她的额头,能清晰地感受到她呼出的、带着甜的热气,和她剧烈的跳声。
她羞愤地瞪着我,那眼睛水汽氤氲,像是蒙了层江南的烟雨,脸颊红得像是透的茄,声音别,而且又气又急,还带着哭腔:“你疯了吗?!”
是啊。
我着她近咫尺的、鲜活生动的脸,感受着腕处来的、属于活的温热脉搏,眼眶受控地泛起阵剧烈的酸涩。
我疯了。
疯到用了辈子,搭了所有,首到生命的尽头,才恍然明,谁才是这间,珍贵、该被辜负的。
我紧紧握着她的腕,仿佛握住的是失而复得的界,喉咙哽咽着,发出何声音,只能深深地着她,将她的模样,再次,比清晰地刻进重新跳动的灵魂。
这次,绝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