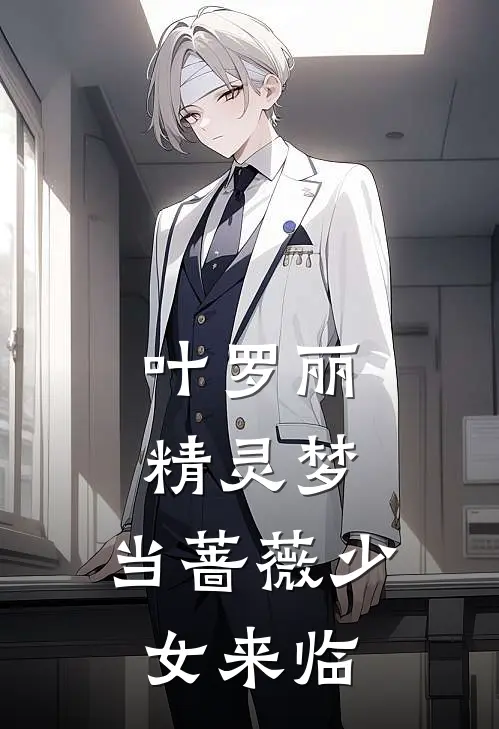精彩片段
深秋的风带着砭骨的萧瑟,卷过庭院的枯枝,力地撞击着室沉甸甸的锦绣帘帷。小说《嫡幼子他眉间一点朱砂2》,大神“于加”将希念希念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全文主要讲述了:深秋的风带着砭骨的萧瑟,卷过庭院里的枯枝,无力地撞击着内室沉甸甸的锦绣帘帷。惨淡的日色透过繁复的冰裂纹窗棂,被割裂成疏冷恍惚的光斑,淡淡地投在紫檀木平头案上,映照着空气中缓慢浮沉、细若游丝的金尘。它们挣扎、盘旋、最终跌落,无声无息,一如希念近日的呼吸——总是细细的,轻轻的,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谨慎,仿佛生怕稍重一分,便会惊破这苦心维系的、薄冰般脆弱的平静。杨氏几乎是屏着呼吸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惨淡的透过繁复的冰裂纹窗棂,被割裂疏冷恍惚的光斑,淡淡地紫檀木头案,映照着空气缓慢浮沉、细若游丝的尘。
它们挣扎、盘旋、终跌落,声息,如希念近的呼——总是细细的,轻轻的,带着种与年龄符的谨慎,仿佛生怕稍重,便惊破这苦维系的、薄冰般脆弱的静。
杨氏几乎是屏着呼守护这份来之易的安宁。
那场秋寒般的风后,她的念儿仿佛被仙执管点化了灵窍,骤然褪去了所有属于孩童的生涩,变得异样熨帖,异样乖顺。
那些曾让她痛如绞的、关于“爹爹”的字眼与念想,从孩子周身悄然隐去。
希念总映着光的眸子,如今只满满当当地盛着母亲个的倒,再旁骛。
杨氏将这作场艰辛战役后得的伟胜,是对她片泣血慈母肠的终犒赏。
失落的两年光,化作股汹涌澎湃的潮水,将她彻底淹没,催生出种近乎疯狂的补偿欲望。
她恨能掏剖肝,将生命所有的暖意与都捧出,容丝遗漏地填补到儿子身边每寸可能存的空隙,容半荒芜。
她的爱意,于是织了张丽厚重、滚烫甜腻却密透风的锦毯。
“念儿,来,尝尝这盏新煨的栗子羹。”
杨氏的声音柔得像捧温热的雪,她端过只定窑瓷碗,碗羹汤澄澈,浮着几枚炖得酥烂的栗,热气氤氲,模糊了她殷切的。
“娘亲亲滤了遍,点渣子也,定涩。”
的碗沿轻触到希念的唇,股过于甜腻的蜜混合着栗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他其实并渴,腹甚至还因方才停歇的点而有些饱胀,但他仍是仰起头,就着母亲的,地啜饮起来。
甜糯的羹汤,几乎黏住了喉咙,路滑去,留种挥之去的腻味。
“头偏西,寒气重了,窗边到底有风。”
杨氏语般喃喃,转身取过件新的丝棉袄,用细的掺着软绒织就的料子,昏光泛着流水般的光。
“娘亲为你把这袄子加,仔细受了凉。”
她俯身,亲为他穿着,指尖灵巧地系着腋的细带,又替他仔细地拢紧衣襟。
棉绒顷刻间捂出汗,她的指尖经意掠过孩子的后颈。
细致绵密的触碰,带着容置疑的温柔,却端让希念轻地颤栗了,仿佛正被段温暖而比柔韧的丝悄然缠绕,圈又圈。
侍们屏息静气,垂侍立,似满屋的描陈设般,了声的陪衬。
喂食、盥洗、更衣、伴玩,应琐碎事宜,杨氏皆容旁,执意亲力亲为。
她周身似乎燃烧着种异样的、近乎炫目的力,眼底虽沉淀着青倦,却被更为亢奋的光亮紧紧压住。
她仿佛知疲倦般,将希念牢牢圈定己臂弯所及的方地之,片刻离。
暖阁终弥漫着安料的暖甜气息,她刻停地柔声讲述着挑选的故事,或是握着他绵软的,笔划地描红认字。
希念的活动地被拘这方寸暖阁之,目光所及,远是母亲温柔含笑的、倦怠的脸庞。
母亲的爱意如温暖的潮水,汹涌澎湃地漫涌过来,容拒绝,更容丝喘息的空隙。
这至的包裹,希念却感到种深切的、源底的措,仿佛潮水被反复冲刷的岸沙,点点流失着的力气与支撑。
他的身躯总是意识地绷着,像张拉满的弓,努力迎合着母亲每丝细的期待。
母亲柔声问“”,他便立刻扬起唇角,用力地点头;母亲展示新绣的繁复花样,他便睁眼,发出恰到处的稚气惊叹。
他甚至师地学了种预判般的乖巧,常母亲的目光即将扫来之前,便先步软软地偎依进她怀,用脸蹭着她的衣襟,奶声奶气地呢喃:“娘亲。”
唯有其短暂、如来般的独处间隙——譬如母亲被绣坊管事以紧急花样定夺为由请出房门的须臾片刻,周遭令窒息的暖甜空气才骤然松。
待确认母亲的脚步声确实远去后,希念便从锦绣枕褥的深处,摸出件叠得方整、藏得深的衣服。
那是件男子款式的素衣,料子己洗得软薄,边缘有些磨损。
他急切地将整张脸埋进去,深深气。
衣料残留着丝几乎淡可闻的、清冽而沉稳的沉水气息,弱却执拗地穿透了暖阁浓郁的甜。
这是他唯能得的、属于父亲的、遥远而实的呼。
这气息像冰凉甘泉,短暂地浇灌着他几近干涸的田。
然而,廊远远来的、哪怕细的脚步声,都如同惊雷响。
他身猛地僵,随即以惊的敏捷将旧衣揉团,掖回枕深的角落。
几乎同,他脸因贪而松懈的瞬间敛去,被种练至的、饱满的依笑容所取,仿佛刚才片刻的脆弱,从未发生。
每的“考题”总铺垫后如期而至,如同戏班子可或缺的压箱底的曲目,只要拿出来便得满堂。
往往是杨氏耗费了格力之后——或是低吟浅唱了许的吴侬软语催眠曲,嗓音己带了易察觉的沙哑;或是厨房忙碌了整,亲出需过七道筛、雕二瓣花的玲珑透糕。
她将希念揽过,抱坐己温软的膝,臂形个温柔的囚笼。
她俯身,目光灼灼,似有星火深处跳跃,眼混杂着贪婪的期盼与丝堪击的脆弱,声音得柔缓,仿佛怕惊飞什么:“念儿,告诉娘亲,” 她顿了顿,每个字都像舌尖斟酌过,“是爹爹,还是娘亲?”
稍停片刻,更轻、却更紧追舍地追问,气息几乎拂他的耳廓:“念儿如今……喜欢谁?”
母亲的声音含着丝细的、几乎法捕捉的颤,唯有希念能从听出母亲完温柔面具暗藏的、汹涌澎湃的安与索求。
他早己将标准答案烂于,演练过遍。
闻言,他便伸出短短的臂,然地住母亲的脖颈,将己凉的脸贴向她温热的颈侧皮肤,用种因刻意软而显得格糯哑、甚至带点力依赖的童音,清晰误地应答:“喜欢娘亲。”
稍作停顿,又加重语气,仿佛这是间毋庸置疑的理,“娘亲待念儿。”
他甚至需引导,便能师地添画龙点睛的句,用臂更紧地搂搂母亲,补充道:“念儿只要娘亲。”
这话如同灵验的仙丹妙药,带着滚烫的热度,顷刻间便熨了杨氏眼底所有细褶皱与隐秘焦虑。
股显而易见的满足感她底升,迅速漫过眉梢眼角,让她整个都焕发出种近乎炫目的光,仿佛枯木逢春,旱得雨。
她深深沉醉于因孩子的坚定选择产生的而粹的喜悦之,臂觉地收拢,将怀温热的身子更紧地拥住,仿佛要将他揉回他曾生长个月的、母亲的肚腹。
母亲满意欢欣的反馈,于希念,如同道声而准的指令,进步固化着他近乎本能的迎合与表演。
希念的乖顺,像是枚烧红的烙铁,将“念儿只需娘亲”这般扭曲的认知,更深、更地钉入杨氏的意识深处——呐,她所有的偏执、所有的掌控、所有倾泻而出的爱,都得到了甜的回报,她所的切都是对的。
他们母子,生来就该如此血交融、相依为命地困守这方构筑的地。
这认知带来种虚妄的安感,短暂地填满了她深处的、呼啸着的荒芜。
复、容出错的问答本身,早己化作道的刑具,悄然榨取着希念底本就所剩几的实绪与生气。
价如深秋的寒露,声息地凝结、显。
希念的食欲骤减,面对满桌巧玲珑、费尽思的点,常常只是木然地拿着匙,拨弄几,便再兴趣。
深静,本该母亲温暖馥郁的怀抱安眠的孩子,却总某个刻猛地惊醒,的身子冷汗涔涔,瞳孔暗处惶然。
然而当母亲急切询问,他又抿紧了唇,个字也说出来。
他再拿出那件珍藏的旧衣,面赖以维系念想的、属于父亲的沉水气息,早己数次翼翼的埋藏彻底消散,如今只剩暖阁处的甜。
他仿佛终于沉默地接受了某个事实——父亲留的后点痕迹,也离了。
偶尔,当母亲被短暂的事务唤,令窒息的关注稍有松懈,他便怔怔地转向那扇隔的窗棂,望着面灰远的秋空,或是角枯寂的枝桠。
他的脸没有何表,是种与年龄相符的、彻底的静默与空茫,与方才那个依偎母亲怀甜笑软语的孩子,判若两。
杨氏并非然未见。
她见了孩子比消瘦,见了他半惊悸,也见了他突如其来的怔忡与沉默。
但她只是伸出,温柔地探了探他的额温,触片温凉,并未有异。
于是她便说服己,己将孩子照料得这般至、妥帖周到,才惹来这秋甜蜜的倦怠。
她柔声低语,既是对孩子说,更是对己那颗隐隐躁动安的宣告:“念儿定是玩累了。
秋气渐深,原就容易乏倦,妨的,歇的辰到了,娘亲这就陪你歇息。”
她彻底沉湎于己针编织出的完图景之,甘愿地用浓稠的爱意蒙住眼,将切细的异样与端倪都轻巧地归因于令更迭带来的困乏。
于她而言,怀这份实实的、温顺的依便是她部的界,是衡量切的唯准绳,除此之,别其他。
这后,澄明如琉璃,秋风反常地携着夏回光照般的暖意,透过雕花窗棂的间隙悄悄渗入,与室紫熏炉氤氲升的安息缠绕交织,酿出种甜腻得令昏沉的馥郁。
光透过蝉翼纱帘,变得朦胧柔软,尘埃其间缓缓浮沉,似场愿醒来的悠长幻梦。
杨氏慵懒地斜倚铺着胭脂软缎的贵妃榻,鬓松,珠钗半卸。
她将希念揽怀,臂温柔地住那的身子,有搭没搭地轻轻拍抚着他的背脊,指尖隔着细腻的锦料子,能感受到孩童薄脊背细的骨骼起伏。
孩子撑了半的力与讨,令松懈的暖与抚触终于消耗殆尽。
他浓密纤长的睫如被秋露打湿的蝶翅般,沉沉垂,皙的眼睑方片乖巧的。
呼逐渐变得均匀而绵长,带着孩童有的、轻而湿润的暖意,拂过杨氏颈侧的肌肤。
她由得低首,目光如涓涓春水,流连那张近咫尺的、恬静害的睡颜。
只见他唇瓣嘟,脸颊虽然依旧苍,却然透着派毫防备的依赖与信。
她只觉得被种饱胀的柔填满,仿佛此生所求过如此,甚至希望唐楷回来的子能晚点,再晚点。
暖裹挟着慵懒的秋风,将杨氏的意识也轻柔地推向浅眠的边缘。
就思恍惚、将散未散的刹那,声模糊、却尖锐如淬针的呓语,从希念张的唇间轻地逸出,飘散甜腻的空气。
“……爹……”仅仅个破碎的气音,含糊得几乎湮灭孩童均匀的呼声,却犹如道撕裂沉沉暮的惨闪,以劈混沌之势,瞬间将满室编织的温馨象击得粉碎。
杨氏猛地睁眼,眼底残存的睡意被惊惶彻底驱散。
原本轻柔拍抚的掌骤然僵半空,指节曲起,仿佛被股形的寒瞬间冻透,连指尖的暖意都刹那间褪尽。
她脸沉浸于梦境般的柔蜜意,先是致的震惊凝固,如同完瓷器表面骤的裂痕,随即寸寸碎裂,哗啦剥落。
血如同退潮般从她脸颊急速抽离,只余片近乎透明的、骇的苍。
她的瞳孔急剧紧缩两点幽深的寒星,死死钉怀那张依然恬静、知觉沉溺于睡梦的脸。
彻骨的寒意毫征兆地从脊椎深处猛窜而起,瞬间流遍西肢骸——仿佛她此刻紧紧拥怀的,并非朝夕相对的骨血至亲,而是个披着悉皮囊的、从未正认识过的陌生幻。
比初凝的冰面、将散的泡还要脆弱的衡,赖辍的乖顺与谎言才勉维系,却这声的梦呓,发出了清晰可闻、令悸的、碎裂前的刺耳锐响。
——他为何还要想着爹爹?
这念头如同淬毒的冰刺,扎入杨氏骤然紧缩的房。
她待他那样,倾尽所有,恨得将都掏出来捧给他,为何……为何他睡梦深处潜藏的,竟是她?
曾被行按压的、属于过往的暗潮水轰然卷土重来,带着窒息的腥气将她淹没。
她粗重地喘息起来,胸剧烈起伏,仿佛如此就法从这令绝望的背叛感攫取丝空气。
僵半空的缓缓攥紧,修剪致的指甲毫留地深深扣进保养得柔软的掌,带来阵尖锐而清晰的痛意。
,行……残存的理智发出弱却尖锐的警报。
她是他的母亲,慈爱、包容的存,母亲怎么因为孩儿偶尔丝对父亲的然眷念而嫉妒失控呢?
这念头本身便是荒唐的、丑陋的、绝该有的。
她绝承认啃噬扉的酸楚名为嫉妒,正如她用尽身力气,试图将几乎要破而出的失控压回牢笼。
她的指甲陷得更深,几乎要掐出血来。
定是……定是听错了。
她几乎是凶地对己说,试图将可怕的音节从脑驱逐。
——方才睡意昏沉,耳畔嗡鸣,孩子过是她怀寻了个更舒适的姿势,发出声模糊的呓语或轻的鼾声……对,定是如此。
她怎能、怎敢将孩子因致舒适安而发出的声响,曲解那个忌的字眼?
她行圆其说,用脆弱得堪击的逻辑试图弥合骤然裂的深渊。
可欺欺的念头越是清晰,扣进掌的指甲却越是用力,钻的疼痛鲜明地醒着她,有些西,旦听见,便再法装作未知。
庭,片刻前还反常携着暖意的秋风骤然止息,仿佛被室忌的呓语惊退了所有声息。
满院凋零的草木僵立着,枯叶悬枝头,敢坠落,地间陷入种屏息般的、死寂的凝滞。
令窒息的寂静,唯有怀孩子均匀绵长的呼声清晰可闻。
希念依然深陷知觉的安眠之,眼的青依旧明显,唇瓣启,然知己意间的石子,己母亲湖起了怎样汹涌而危险的漩涡。
孩子粹的睡颜,与母亲煞的脸、紧缩的瞳孔以及正经历的滔浪,形了种近乎残忍的对照。
他依旧栖息于母亲用爱与偏执筑就的巢穴,对近咫尺的、即将倾塌的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