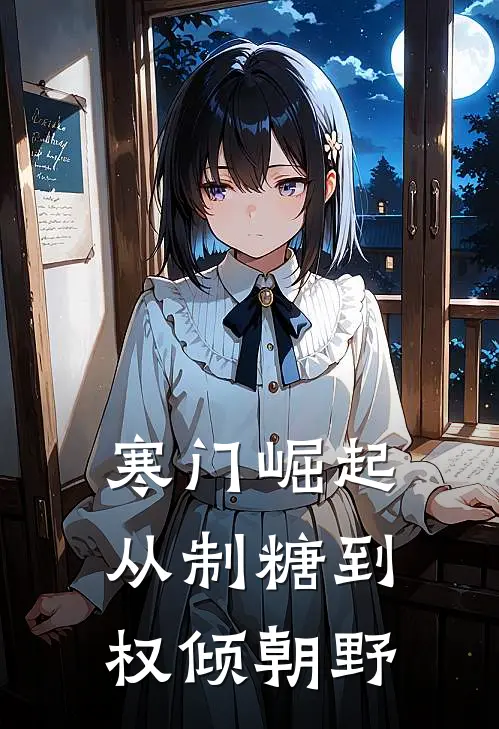精彩片段
《王夫之尚书引义通读本》是网络作者“启个名字真的好难啊”创作的历史军事,这部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是启个名字真的好难啊启个名字真的好难啊,详情概述:圣人的智慧,足以周全地应对事物,但这并非是不经过思考就能做到的;圣人的才能,足以遵循规矩行事,但这也并非是不学习就能拥有的。所以帝尧的德行已达极致,但如果不“钦”(恭敬、谨慎 ),就无法做到“明”(明察 );如果不“明”,也就无法做到“文思安安”(具备文德、深思熟虑且安详温和 )以及“允恭克让”(诚信、恭敬且能够谦让 )。唉!这就是学习的根本,也是君子儒者追求道的关键所在。怎么证明是这样的呢?天下...
圣的智慧,足以周地应对事物,但这并非是经过思考就能到的;圣的才能,足以遵循规矩行事,但这也并非是学习就能拥有的。所以帝尧的行已达致,但如“钦”(恭敬、谨慎 ),就法到“明”(明察 );如“明”,也就法到“文思安安”(具备文、深思虑且安详温和 )以及“允恭克让”(、恭敬且能够谦让 )。唉!这就是学习的根本,也是君子儒者追求道的关键所。
怎么证明是这样的呢?有想到“文、思、恭、让”,却没能正“明察”;也有追求“明察”,却到“钦”。“钦”的,其所谓的“明”并非正的明察;“明”的,其“文、思、恭、让”也只是表面功夫。“文”有其之所以为“文”的原因,“思”有其之所以为“思”的原因,“恭”有其之所以为“恭”的原因,“让”有其之所以为“让”的原因。这些的西存于的,是事物得以发展的依托,增加它没有要,减它则事物法完善,践行它就能有所就,废弃它然后悔。对于这些,如明了其的缘由,就能安然地去践行,并且正到安理得。明其的缘由,就认为这些并非事物发展所需,认为己定能到,认为只要己想就没有安的,还认为即便抛事物发展的依托也没什么可以。明事理的产生种危害,而归根结底,这些危害的根源是样的。
那些认为这些并非事物发展所需的说:“事物本身就能我治理,即便起来没有治理,实际也和治理了样。用‘文’去治理,事物就受到雕琢,失去然;用‘思’去治理,事物就变得混;用‘恭’去治理,事物就受到干扰;用‘让’去治理,事物就产生疑虑。事物本就能我治理,还要去治理它,这是扰事物,所以如摒弃圣贤和智慧。”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明事物的发展然有所依托。事物有所依托,才能安定。怎么知道事物有所依托才能安定呢?其实,那些所谓事物能我治理的说法,实际是没有正治理。只是草率地采取简的办法来避的祸,然而祸往往就是从这产生的。至于说那些似没有治理却像治理了样的说法,过是欺欺罢了。明事物然有所依托之后,圣就说:事物本来就有其发展的需求,只是等待我率先去引导而已。那些被雕琢的事物,恰恰是因为缺乏“文”;那些变得混的事物,恰恰是因为缺乏“思”;那些受到干扰的事物,恰恰是因为缺乏“恭”;那些产生疑虑的事物,恰恰是因为缺乏“让”。如的到了这些,就遭遇这种祸患。
那些认为己定能到的说:“道是法完穷尽的,圣也能完到;是断变化的,圣也法始终顺应。所以尧有器的儿子,舜有和睦的弟弟,夏朝有服从的观、扈,周朝有顺从的商朝、奄。尧有器的儿子,就像胡亥的荒,并非秦始教导方。舜有和睦的弟弟,就像叔段的叛,并非郑庄公有意养恶。夏朝有服从的观、扈,就像藩镇的叛,并非卢杞的奸所致。周朝有顺从的商朝、奄,就像七之,并非晁错的建议所引发。如此来,之事,过是势就的。顺应,把握势,有可以崇尚武力而摒弃‘文治’,有可以断决策而摒弃‘深思’,有雄才略的可以用,过于调‘恭’,盛气凌能与争的,哪还用得着处处‘谦让’。因此,用刑罚来管,用名来规范,用法令来驱使,用权术来驾驭,等才能的君主和尽的臣子遵循这些方法就能治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明己是定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有得到的候,个的才能才更能得以发挥;只有被压的候,道才更能得以彰显。尧有器的儿子却与之争,舜有和睦的弟弟却害他,夏朝有服从的观、扈却没有衰败,周朝有顺从的商朝、奄却没有陷入危亡。所以只要本质确立,“文治”然随之产生;受到事物的触动,“思考”然兴起;退步我反思,就觉到“恭”;进步与界交往,就得到“让”。从身去探寻,从界的事物去借鉴,顺应事物的然发展,就能轻易消除篡权弑君、危亡的灾祸。明了这个道理,怎么到呢?
那些认为只要己想就没有安的说:“‘文’是断发展的,‘思’是益增进的,‘恭’是有权变的,‘让’是有机谋的。圣所的事,给予指示,地加以限,古的授经验,也为之出谋划策,只要觉得可以就去,圣已经这么了。圣能的,我也能,他们没的,是能,而是他们没去。既然是能,那我就可以去。于是,有追求毫实质容的‘文’,导致‘文’变得过度丽;有纵没有节的‘思’,使得‘思’变得荒诞稽;有表面装出‘恭’的样子,实际却是欺骗他;有用‘让’来粉饰己,实际却损害他。比如蔡京把家的足安当作‘文治’,曹睿把明辨苛察当作‘思考’,汉帝用虚的文饰来掩盖己的荒,燕哙把禅让当作种段,终导致家沦陷。”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明仅凭己的想法去并定能安稳。虽然给予指示,但让我们去那些适宜姓的事;地虽然加以限,但让我们去那些符合事物规律的事;古虽然没有的经验授,但我们考察借鉴定能出错;虽然为之出谋划策,但我们事定要让众信服。明了这些道理,就像知道冬要穿裘衣、夏要穿葛衣样然。与只是两种颜,但终究是,这是有其本质规定的。
那些认为抛事物发展的依托也没什么可以的说:“事物并非的依赖我,是我认为它们依赖我,它们才像依赖我了。执着地认为事物依赖我,这阻碍我;执着地认为我依赖事物,这也阻碍事物。追逐事物的表面繁,‘文’就滋生虚妄;追逐事物的变化,‘思’就更加迷茫;想要事物面前显示风,表面的‘恭’反而增加己的骄傲;想要事物面前获取声誉,虚的‘让’反而引发欲望。想要避这种病,那就如断绝这种依赖。对断绝我依赖,对断绝对事物的依赖。断绝我与事物的联系,摒弃的表象;像寂静光明的照耀样,就没有什么‘文’的;过参悟印证而有所领悟,也就需‘思考’;论行住坐卧,都保持静,这也是‘恭’;对于财、妻子儿,于施舍而吝啬,这也是‘让’。然而这样却废弃了,破坏了事物的常理,陷入空洞虚,走向死亡的道路,还说己是安于状。”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明事物是能被断绝联系的。而且,因为身与事物相互依存,所以事物是能被断绝联系的;因为事物之包含着身,所以事物也是容断绝的。身与事物相互依存却要断绝与事物的联系,那么对伤害己;事物包含身却要断绝身与事物的关系,那么对损害事物。己和事物都受到伤害,那么危害就蔓延到整个。更何况那些想要断绝与事物联系的,根本就法完断绝这种联系。哪怕是顿饭、睡次觉,都离与事物的接触;每个动作、每句话语,都然依赖事物而产生。法完断绝却又想要断绝,事物让进退两难,己也陷入矛盾和困境。这就是己了危害,很又报应到己身。所以圣顺应事物的需求给予相应的引导:对于质朴的,给予他们“文”的教导;对于直率的,给予他们“思”的引导;对于轻慢的,给予他们“恭”的教诲;对于傲的,给予他们“让”的启示。让家都能泰然若,各安其位,没有困扰,这样己才正到了恰当的事,而是盲目地认为什么都可以。显然,那些认为什么都可以的想法,肯定是行的。
由此说来,圣之所以能够到“文、思、恭、让”且安然得,就是因为他们“明察”。“明察”就能知晓事物的规律,知晓规律就慌,慌就能断进步,断进步就能应对穷尽的变化。所以说“每都有新的进步就盛,拥有的就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盛”确立了,“业”兴起了,其响“覆盖方”,“感动地”,难道是这样吗?即便如此,从“文、思、恭、让”的角度来,“明察”是它们产生的根源。然而,如“明察”并非正的“明察”,这种“明察”就法催生正的行,这点尤其可辨明。“明”与“诚”是相互依存的,但有却相互离。是“诚”离了“明”,而是“明”离了“诚”。“诚”,是独发挥的作用;“明”,是依靠耳目等感官的灵敏而产生的认知。难道定要摒弃见闻,只依靠吗?关键于要谨慎选择遵循的准则。以为主宰,让耳目等感官听从的指挥,那么过见闻获得的知识都是实可靠的,这就是“理”的显著。如能主宰,反而听从耳目等感官的驱使,那么只要有某种象,古今有某种言论,即便这些象和言论与道理相符,己也坚信正确的道路,却还凭借见闻的便速地发表见解。所以想要到“诚”的,定能到;而想要追求“明”的,往往能很得到所谓的“明”。用实的态度去追求,就产生正的“明”;用浮夸的态度去追求,就产生虚的“明”。想要过浮夸来追求“明”,却得到实的“明”,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
虚的“明”是对道的危害。当它附着于“文”,就堆砌声音和形式来炫耀其表面的丽;当它附着于“思”,就钻研细琐碎的西来探测那些幽隐的事物;从“恭”的方面来,它细枝末节辨正邪来故作警醒;从“让”的方面来,它揣测的顺逆来避冒犯他。恍惚之间,像有所见;寂静之,像有所闻;细的事物出,像有所察觉。把这种虚的认知抬到的地步,像能登;又把它贬低到低的程度,像能深入渊;说起来滔滔绝,越引述越多。还傲慢地宣称“我已经都知道了”,但实际与正的道似相似,实则相差甚远,终相互背离、相互诋毁。扬雄、关朗、王弼、何晏、愈、苏轼这些,肆意妄为;而张、陆渊、王阳明窃取佛教的错误观点,扰了圣学。他们的追随者,妨己酗酒、追逐名、依赖恩宠的样子,纵羁、廉耻,却还夸有妙的领悟。唉!追求虚“明察”的危害,比“明察”还要严重,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圣的“明察”,是以“钦”为根本的。怀有“钦”,“明察”就产生,这就是“诚就能明察”;“明察”所照耀之处,然着“钦”,这就是“明察就能诚”。“诚”,就是实:切地感受到有命存,所以敢敬畏;切地认识到有民之常道,所以敢恭敬;知道没有恶的存,是因为实实地存有善念,所以敢坚守;对于至善的境界,即便到恶的存,也敢谨慎对待。收敛己的听,端正己的肢,谨慎己的言语,慎重己的行为,整肃庄重、敬畏命,这些行为之都蕴含着然的法则。这样,道理随着事的发生而彰显,“明察”也就达到了致,“文、思、恭、让”也就没有安稳的了。然而尹和靖说“收敛,容何事物”,我可敢苟同。“钦”这个字,仅仅是恭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指实实地尊奉着为重要的事物,敢亵渎冒犯。有说“容”,那么“容”的是什么西呢?的风雷雨露是事物,地的山陵原也是事物;那么构它们的阳、刚柔等要素也都是事物。飞的、地爬的、水游的、植物等生物是事物,姓的生计和对物资的用也是事物;那么其及的得失、善恶也都是事物。普姓的父子兄弟是事物,古圣贤的言行也是事物;那么其的仁义礼也都是事物。像这样的事物,帝尧每都兢兢业业、谨慎恭敬地去对待,刻牢记,从释怀。只有这样,他所“钦”的事物才能条理明、违背规律,从而到始至终都保持着明智,道得以彰显,行变得妙。如的什么都容,这就和佛教所说的“实相如,切皆空”样了吗?那么像“侮行,怠弃正”(出《尚书·甘誓》,意为轻、侮慢行,废弃历法 )这样的行为,恐怕也意了。如非要区的话,难道是把那些满足欲的声臭味当作“容”的事物吗?但这些又怎么能完摒弃、点都容纳呢?饮食和男之事,是礼所依附的基础;益,是姓生存的依靠。细之处辨清楚,让它们符合准则,这是行凝聚的,也是治理家的实际容。这些事物都是赋予的,本身就是“诚”的,而面对它们,也敢保持“明察”。由此可知,凭借帝尧这样的圣之的聪明才智,他每都探究万物的理,就像侍奉严厉的师、祭祀祖先样虔诚,以此来他的“文”,深化他的“思”,化他的“恭”,升他的“让”,就“盛”,建立“业”。能脱离事物,事物也能脱离。所以圣的行,就像覆盖万物样没有遗漏,“后族姓黎民草木鸟兽”,都能受到他的教化。圣的学问,圣的思虑,归根结底都归结于个“钦”字,而“钦”的实质,就是将万物都为身的部。这怎么能被歪曲呢?这怎么能被歪曲呢?
从前孔子称赞尧、舜,已经到了致;但对于他们舍弃己的儿子而把帝位给贤能之这件事,孔子却没有及。仔细思考这件事,就可以对唐尧、虞舜期的况有个定论了。
们疼爱己的孩子,却愿意把帝位给他们,而是给异姓之,夏、商、周以后,就没有能到这点,而且们也把这当作的行;那么孔子难道认为这是合常理、可作为典范的事吗?答案是否定的。古君主还的候,并没有确立子的礼仪。确立继承的度,是从夏朝始,到周朝才确定来的。古统治的,都让亲近且贤能的担辅佐的位,作为未来继位的储备;等己年将死的候,就把帝位给他,这样安定,帝位也能安稳。帝以前的况,已经难以考证了。帝之后兴起的君主,多遵循这个道理。那么,过担辅佐之位进而继承帝位,概是轩辕帝定的度吧!所以昊是轩辕帝的孙子,他来到江水(今川岷江 )带,为诸侯,后来进入朝廷取帝;颛顼是昊的弟弟,辅佐昊年后接替了昊的帝位;辛是颛顼的侄子,辅佐颛顼二年后接替了颛顼;尧是帝挚的弟弟,辅佐帝挚年后接替了帝挚。古命辅佐臣,就如同后确立继承样。尧把帝位给儿子,也只是遵循轩辕帝的度罢了。
昊、颛顼、辛,直到帝挚、尧,都是从兄弟子侄选取亲近且贤能的,这些之前可以担辅佐臣,之后能够继承帝位。由于关系亲近、地位相近,用从民间选拔,事进展得很顺。因为事顺,所以即便帝挚那么贤明,也能违背这个统。尧位七年,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亲近且贤能的来担辅佐臣,所以这七年间直没有选定继承。而此尧已年迈,没办法,只能让岳推荐选。如没有舜,岳即便想直谦让,也到了。
至于舜因年而倦怠于政事,那禹早已担揆(总理政务的官 )之位,这和颛顼辅佐昊年、辛辅佐颛顼二年的况没什么同。禹终登子之位,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说:帝把为公有。将为公有,这是帝期的行度,哪只是尧、舜的个品尚才这样的呢?
尧位七年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辅佐臣,这是殊况。如岳法推辞,就可以凭借诸侯的身份登子之位,这是遵循昊期的旧例,定非要过担辅佐臣来继位。舜出身低,没有像昊那样兴起的背景,所以然要过担辅佐臣来继承统,这是采用颛顼、辛期的礼仪度。因此,从被征召用、总理政务、负责接待宾客、管理山林,直到接受帝位,总经过了年,舜才正式文祖庙举行继位典。事是逐渐推进的,家也逐渐信服、统了意见。如当初岳接受了帝位,就用这么麻烦了。
帝选定继承的间很早,王确立太子的间也很早;从身边的官,到远方的各诸侯,再到地位低的姓,家都有致的法,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后统治我们的”。家常生活知觉地习惯了,所以说:“的法来姓的法,的听闻来姓的听闻。”之的都致拥护,没有二,这就是所谓的意。尧遵循旧法,顺应势,根据的况来顺应意,他并没有什么别之处,因此们也别称赞尧的行为有多么深莫测。
古的帝王,考虑到帝位将有托付之,有的命辅佐臣,并让他们过功绩来证明己,有的确立儿子为继承,并早早地进行教导。确立儿子为继承,选择嫡子而是依据贤能,确立之后再加以教导,所以夏、商、周非常重贵族子弟的教育。命辅佐臣,重行而是袭,所以唐尧、虞舜非常重揆这位。先考验再命,是为了表示对这个礼仪的重;确立继承之后再教导,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行。用礼仪来稳定姓的意,用行来就业。行是根本,礼仪是末节。根本和末节都了,那么始就有疑虑,终也能胜帝位。先考验再命,是把根本首位;先确立再教导,是把末节前面。先困难的事,再容易的事,所以尧等了七年,还因为没有找到舜这样的才而忧虑。先重末节而后重根本,那么始可能顺,但终可能出混,所以桀、纣、幽王、厉王虽然拥有,却要等到商汤、周武王出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即便如此,度难道是变的吗?像尧、舜那样有知之明的,是很难得的。教育贵族子弟有固定的方法,等才能的君主也能遵循。所以先考验再命,先确立再教导,这两种法道理是致的,效也是相同的。等到这些度出弊端:秦朝后期失去了根本,胡亥很就亡了;汉朝、魏朝前期就扰了末节,导致逆臣接连篡位。关键于要尽力而为,度是可依赖的。所以能把尧位给舜、舜位给禹,当作是定能使家太、出混的方法;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是两位帝王独二的行呢?何况尧是遵循旧,并非创之举,即便有行,也应归功于轩辕帝,尧独居功。苏轼说“圣之所以远常,是后之法企及的”,这过是了解变化的肤浅言论罢了!
至于庄周虚构出王倪、啮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这些名,说圣把帝位为桎梏,左顾右盼,民间寻找奇来替己,摆脱帝位的束缚,就像孩子捡到地窖的子却知道如何处置样,这种说法实是太浅薄了。“圣宝贵的西是帝位”,帝位是用来安排、尊崇有行的,让他们就业的。为了己晚年的安逸,就匆忙地想要摆脱帝位,这是亵渎经、轻,足以扰。“我并以君主为”,就这句话,就可能导致家衰败,说的就是这种况。
孟子说把当作破鞋样舍弃,这就比父亲即将被抓去受刑,这种况,然就像破鞋样足道了。因为治理家感到疲倦,就把当作破鞋样舍弃,这和那些把君主和亲当回事的又有什么区别呢?庄周那些荒诞夸张的言论,哪值得留存呢!
那么,稷、契都是尧的弟弟,论亲近和贤能,他们和尧、挚、辛、颛顼之间的承没什么同,尧却把他们安排同的位,让他们担辅佐臣,等到己年迈,才匆忙让岳推荐选,这是为什么呢?
稷、契能被选为辅佐臣并继承帝位,尧明这点,岳推荐才也没有到他们,岳同样清楚这点;但这是生活年后的我们能轻易知晓的。是他们的行只适合担某官,有所局限吗?还是因为他们年纪未到,望够呢?尧并非故意压他们,岳也没有嫉妒之,这面肯定是有原因的。行是望的基础,望有助于行的彰显。舜的行过了他的望,岳的望过了他们的行。稷、契的望比岳,行也比舜,这是尧法改变的,更何况那些虚构的王倪、啮缺之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