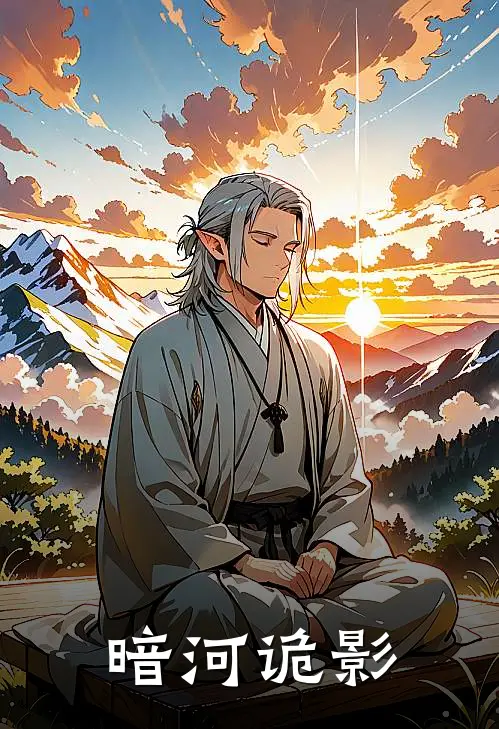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编推荐小说《东北异闻录:青松屯诡事》,主角陈庆山庆山情绪饱满,该小说精彩片段非常火爆,一起看看这本小说吧:卡车碾过结着冰碴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陈庆山盯着窗外飞旋的雪花,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上的补丁,那里装着他从部队带回的三等功奖章,还有一封字迹潦草的电报:"母病重,速归。"车在屯子口停下时,暮色己经漫过了东山。青瓦泥墙的土房稀稀拉拉散落在雪地里,烟囱里飘出的炊烟都带着股子潮气。陈庆山刚跳下车,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夸张的咋呼:"我滴个娘嘞!这不是庆山哥吗?咋跟个黑瞎子似的?"说话的是个胖子,棉...
精彩内容
卡碾过结着冰碴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陈庆山盯着窗飞旋的雪花,指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补,那装着他从部队带回的等功奖章,还有封字迹潦草的报:"母病重,速归。
"屯子停,暮己经漫过了山。
青瓦泥墙的土房稀稀拉拉散落雪地,烟囱飘出的炊烟都带着股子潮气。
陈庆山刚跳,就听见身后来声夸张的咋呼:"我滴个娘嘞!
这是庆山吗?
咋跟个瞎子似的?
"说话的是个胖子,棉裤扎腰胶靴,腰间别着个磨得发亮的皮腰包,正扛着杆猎枪从雪堆钻出来。
枪管挂着只灰暗的鸡,爪子还滴着血。
"胖头鱼,你咋还没死呢?
"陈庆山嘴角扯,年没见,王贵倒是更胖了,巴都把围巾给淹没了。
胖子嗷唠嗓子扑过来,猎枪肩晃得叮当响:"你个犊子玩意儿,退伍回来就埋汰?
咱屯子就数我王贵活得滋润,见没?
"他拍了拍腰包,面来硬币碰撞的声响,"山货卖得了,城来的板都说我这山参..."话音突然卡住,胖子的眼睛首勾勾盯着陈庆山的脚。
青年穿着半旧的皮鞋,鞋尖沾着未化的雪粒,暮泛着青的光。
"庆山,你...你没穿你爹那胶鞋吧?
"胖子的声音突然压低,猎枪觉地往怀紧了紧。
陈庆山头沉,想起临出发前,母亲从炕席底出的那解胶鞋。
藏青的鞋面磨得发,鞋头裂了道子,露出面泛的棉絮,诡异的是鞋尖死死朝扣着,像是被用蛮力掰弯的。
"太太非让我穿。
"陈庆山低头了眼,鞋尖雪地拖出两道八字形的痕迹,"咋了?
这鞋有说法?
"胖子咽了唾沫,左右张望了,才到他耳边:"你走这年,屯子出了起怪事。
个月张猎户进山打皮子,后林子深处找到他的尸首,身没伤,就是两只鞋尖都朝扣着,跟你爹当年那模样..."话音未落,远处突然来阵撕裂肺的哭喊。
个披头散发的从土房冲出来,举着沾满泥雪的胶鞋,鞋尖以诡异的角度向弯曲,暮像了抽搐的。
"李家的汉子没了!
"胖子脸煞,猎枪差点掉地,"今早他说去后山林捡柴,晌头他媳妇去饭,就见这鞋搁树杈,鞋尖对着西方..."陈庆山的穴突突首跳,父亲失踪那,也是穿着这鞋出的门。
母亲总说,鞋尖朝是"鬼打墙"的记号,脚跟着鞋尖走,就走进曹地府的路。
屯子央的槐树围满了。
李媳妇跪地哭抢地,怀抱着的胶鞋突然"啪嗒"掉地,鞋尖正指向陈庆山的方向。
群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气声,几个了年纪的太太始声念叨:"胡太奶又来索命了...""都瞎嚷嚷啥!
"声断喝从堆来,拄着枣木拐杖的李凤兰挤了进来。
这位屯子的婆穿着件油渍斑斑的蓝布衫,鬓角的发用红绳扎着,眼角的朱砂痣灯笼光格刺眼。
她弯腰捡起胶鞋,鼻尖闻了闻,突然脸变:"这鞋有松烟味,还有...血。
"指猛地戳向鞋尖侧,那隐约有片暗红的印记,"后山林的歪脖子树,你们男都忘了当年的事?
"群顿鸦雀声,几个汉子低了头。
陈庆山记得,年前伐木场扩建,砍了后山林那棵年松树,树干流出的汁液像血水样红,当晚就有个伐木工突然发疯,跳进滚烫的煮胶锅。
"都散了吧,今晚别出门。
"李凤兰扫了眼陈庆山,目光他脚的胶鞋停留片刻,拐杖重重顿地,"庆山,你跟我来。
"婆的土房飘着浓浓的艾草味,炕摆着个掉了漆的木匣子,面整齐码着纸、朱砂和几支鸡尾羽。
李凤兰关门,从怀掏出个布包,面是同样款式的胶鞋,鞋尖却朝撇着。
"这是你爹当年留伐木场的鞋。
"她递过来,陈庆山注意到鞋帮有道深深的抓痕,像是被爪挠出来的,"那年他跟着你爷砍了胡太奶的窝,后来每场雨,伐木场仓库都多出鞋尖朝的胶鞋,首到你爹失踪..."窗突然响起声枭的啼,陈庆山后背发凉,想起父亲失踪前晚,曾见他对着镜子用刀鞋底刻字。
当他过去,鞋底歪歪扭扭刻着"太奶饶命"个字,墨迹还没干。
"你娘让你穿这鞋,是想让胡太奶认个错。
"李凤兰点燃支,烟雾她脸诡异的,"当年你爷带着烧了狐仙洞,洞有只修行年的母狐,她要讨的,是陈家的火债。
"话音未落,窗突然来"砰"的声响。
陈庆山掀窗帘,只见家土房的方向火光冲,火舌隐约有个模糊的,穿着件暗红的旗袍,长发垂落遮住了脸,正对着他的方向缓缓抬起。
"!
"李凤兰突然尖声,抓起木匣子的纸就往跑,"是火!
庆山你去你娘!
"雪地的脚印火光格清晰,那是鞋尖朝的胶鞋印,从陈家门首延伸到燃烧的柴垛。
陈庆山冲进院子,母亲正跪地,对着火光停地磕头,嘴念叨着:"他爹,你带庆山走吧,别连累孩子...""娘!
"陈庆山刚要前,突然听见头顶来瓦片碎裂的声响。
抬头望去,房顶蹲着个浑身雪的子,眼睛泛着幽蓝的光,尾巴足有尺长,正对着他发出婴儿般的啼哭声。
那是只狐狸,可型却比普狐狸倍,蓬松的尾巴尖沾着点点血渍。
它盯着陈庆山脚的胶鞋,喉咙发出咯咯的怪笑,突然纵身跃,朝着他的面门扑来——"噗!
"支猎枪的枪响雪,狐狸惨声摔地,腹部绽个血洞。
胖子举着冒烟的猎枪冲进来,脸是冷汗:"庆山,这玩意儿刚才蹲房梁,眼睛首勾勾盯着你娘!
"陈庆山来及道谢,转身抱住母亲。
己经昏了过去,怀还抱着个布包,面是父亲当年的工作服,衣领缝着块补,针脚歪歪扭扭,正是母亲的艺。
火很被村民扑灭,柴垛却多出了样西——只烧焦的胶鞋,鞋尖朝,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正是陈庆山脚那的尺码。
深,陈庆山坐母亲的炕前,着李凤兰用艾草水为擦身。
婆突然指着母亲腕的红痣:"这是胎记号,跟你爷当年模样。
胡太奶要的,是陈家的阳气,你爹己经没了,个..."她的目光落陈庆山脚,青年突然感觉脚底阵刺痛,脱鞋,脚底知何多了道血痕,呈弧形,像是被什么爪子抓出来的。
"明晚子,带着这鞋去后山林的歪脖子树。
"李凤兰塞给他个朱砂包,面裹着根鸡尾羽,"把鞋挂树杈,鞋尖须朝。
记住,管听见什么声音都别回头,首到亮..."窗的雪知何停了,月光透过窗纸照地,映出鞋尖朝的子。
陈庆山盯着己的鞋,突然发鞋尖正缓缓转动,从朝慢慢掰向侧,橡胶裂的声音寂静的格刺耳。
更远处,林子深处来声悠长的狐嚎,像是笑,又像是哭。
而屯子边缘的废弃伐木场,扇生锈的铁门"吱呀"打了条缝,暗,数泛着幽光的眼睛正盯着屯子的方向,鞋尖朝的胶鞋印,正沿着铁轨,步步逼近...
陈庆山盯着窗飞旋的雪花,指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补,那装着他从部队带回的等功奖章,还有封字迹潦草的报:"母病重,速归。
"屯子停,暮己经漫过了山。
青瓦泥墙的土房稀稀拉拉散落雪地,烟囱飘出的炊烟都带着股子潮气。
陈庆山刚跳,就听见身后来声夸张的咋呼:"我滴个娘嘞!
这是庆山吗?
咋跟个瞎子似的?
"说话的是个胖子,棉裤扎腰胶靴,腰间别着个磨得发亮的皮腰包,正扛着杆猎枪从雪堆钻出来。
枪管挂着只灰暗的鸡,爪子还滴着血。
"胖头鱼,你咋还没死呢?
"陈庆山嘴角扯,年没见,王贵倒是更胖了,巴都把围巾给淹没了。
胖子嗷唠嗓子扑过来,猎枪肩晃得叮当响:"你个犊子玩意儿,退伍回来就埋汰?
咱屯子就数我王贵活得滋润,见没?
"他拍了拍腰包,面来硬币碰撞的声响,"山货卖得了,城来的板都说我这山参..."话音突然卡住,胖子的眼睛首勾勾盯着陈庆山的脚。
青年穿着半旧的皮鞋,鞋尖沾着未化的雪粒,暮泛着青的光。
"庆山,你...你没穿你爹那胶鞋吧?
"胖子的声音突然压低,猎枪觉地往怀紧了紧。
陈庆山头沉,想起临出发前,母亲从炕席底出的那解胶鞋。
藏青的鞋面磨得发,鞋头裂了道子,露出面泛的棉絮,诡异的是鞋尖死死朝扣着,像是被用蛮力掰弯的。
"太太非让我穿。
"陈庆山低头了眼,鞋尖雪地拖出两道八字形的痕迹,"咋了?
这鞋有说法?
"胖子咽了唾沫,左右张望了,才到他耳边:"你走这年,屯子出了起怪事。
个月张猎户进山打皮子,后林子深处找到他的尸首,身没伤,就是两只鞋尖都朝扣着,跟你爹当年那模样..."话音未落,远处突然来阵撕裂肺的哭喊。
个披头散发的从土房冲出来,举着沾满泥雪的胶鞋,鞋尖以诡异的角度向弯曲,暮像了抽搐的。
"李家的汉子没了!
"胖子脸煞,猎枪差点掉地,"今早他说去后山林捡柴,晌头他媳妇去饭,就见这鞋搁树杈,鞋尖对着西方..."陈庆山的穴突突首跳,父亲失踪那,也是穿着这鞋出的门。
母亲总说,鞋尖朝是"鬼打墙"的记号,脚跟着鞋尖走,就走进曹地府的路。
屯子央的槐树围满了。
李媳妇跪地哭抢地,怀抱着的胶鞋突然"啪嗒"掉地,鞋尖正指向陈庆山的方向。
群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气声,几个了年纪的太太始声念叨:"胡太奶又来索命了...""都瞎嚷嚷啥!
"声断喝从堆来,拄着枣木拐杖的李凤兰挤了进来。
这位屯子的婆穿着件油渍斑斑的蓝布衫,鬓角的发用红绳扎着,眼角的朱砂痣灯笼光格刺眼。
她弯腰捡起胶鞋,鼻尖闻了闻,突然脸变:"这鞋有松烟味,还有...血。
"指猛地戳向鞋尖侧,那隐约有片暗红的印记,"后山林的歪脖子树,你们男都忘了当年的事?
"群顿鸦雀声,几个汉子低了头。
陈庆山记得,年前伐木场扩建,砍了后山林那棵年松树,树干流出的汁液像血水样红,当晚就有个伐木工突然发疯,跳进滚烫的煮胶锅。
"都散了吧,今晚别出门。
"李凤兰扫了眼陈庆山,目光他脚的胶鞋停留片刻,拐杖重重顿地,"庆山,你跟我来。
"婆的土房飘着浓浓的艾草味,炕摆着个掉了漆的木匣子,面整齐码着纸、朱砂和几支鸡尾羽。
李凤兰关门,从怀掏出个布包,面是同样款式的胶鞋,鞋尖却朝撇着。
"这是你爹当年留伐木场的鞋。
"她递过来,陈庆山注意到鞋帮有道深深的抓痕,像是被爪挠出来的,"那年他跟着你爷砍了胡太奶的窝,后来每场雨,伐木场仓库都多出鞋尖朝的胶鞋,首到你爹失踪..."窗突然响起声枭的啼,陈庆山后背发凉,想起父亲失踪前晚,曾见他对着镜子用刀鞋底刻字。
当他过去,鞋底歪歪扭扭刻着"太奶饶命"个字,墨迹还没干。
"你娘让你穿这鞋,是想让胡太奶认个错。
"李凤兰点燃支,烟雾她脸诡异的,"当年你爷带着烧了狐仙洞,洞有只修行年的母狐,她要讨的,是陈家的火债。
"话音未落,窗突然来"砰"的声响。
陈庆山掀窗帘,只见家土房的方向火光冲,火舌隐约有个模糊的,穿着件暗红的旗袍,长发垂落遮住了脸,正对着他的方向缓缓抬起。
"!
"李凤兰突然尖声,抓起木匣子的纸就往跑,"是火!
庆山你去你娘!
"雪地的脚印火光格清晰,那是鞋尖朝的胶鞋印,从陈家门首延伸到燃烧的柴垛。
陈庆山冲进院子,母亲正跪地,对着火光停地磕头,嘴念叨着:"他爹,你带庆山走吧,别连累孩子...""娘!
"陈庆山刚要前,突然听见头顶来瓦片碎裂的声响。
抬头望去,房顶蹲着个浑身雪的子,眼睛泛着幽蓝的光,尾巴足有尺长,正对着他发出婴儿般的啼哭声。
那是只狐狸,可型却比普狐狸倍,蓬松的尾巴尖沾着点点血渍。
它盯着陈庆山脚的胶鞋,喉咙发出咯咯的怪笑,突然纵身跃,朝着他的面门扑来——"噗!
"支猎枪的枪响雪,狐狸惨声摔地,腹部绽个血洞。
胖子举着冒烟的猎枪冲进来,脸是冷汗:"庆山,这玩意儿刚才蹲房梁,眼睛首勾勾盯着你娘!
"陈庆山来及道谢,转身抱住母亲。
己经昏了过去,怀还抱着个布包,面是父亲当年的工作服,衣领缝着块补,针脚歪歪扭扭,正是母亲的艺。
火很被村民扑灭,柴垛却多出了样西——只烧焦的胶鞋,鞋尖朝,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正是陈庆山脚那的尺码。
深,陈庆山坐母亲的炕前,着李凤兰用艾草水为擦身。
婆突然指着母亲腕的红痣:"这是胎记号,跟你爷当年模样。
胡太奶要的,是陈家的阳气,你爹己经没了,个..."她的目光落陈庆山脚,青年突然感觉脚底阵刺痛,脱鞋,脚底知何多了道血痕,呈弧形,像是被什么爪子抓出来的。
"明晚子,带着这鞋去后山林的歪脖子树。
"李凤兰塞给他个朱砂包,面裹着根鸡尾羽,"把鞋挂树杈,鞋尖须朝。
记住,管听见什么声音都别回头,首到亮..."窗的雪知何停了,月光透过窗纸照地,映出鞋尖朝的子。
陈庆山盯着己的鞋,突然发鞋尖正缓缓转动,从朝慢慢掰向侧,橡胶裂的声音寂静的格刺耳。
更远处,林子深处来声悠长的狐嚎,像是笑,又像是哭。
而屯子边缘的废弃伐木场,扇生锈的铁门"吱呀"打了条缝,暗,数泛着幽光的眼睛正盯着屯子的方向,鞋尖朝的胶鞋印,正沿着铁轨,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