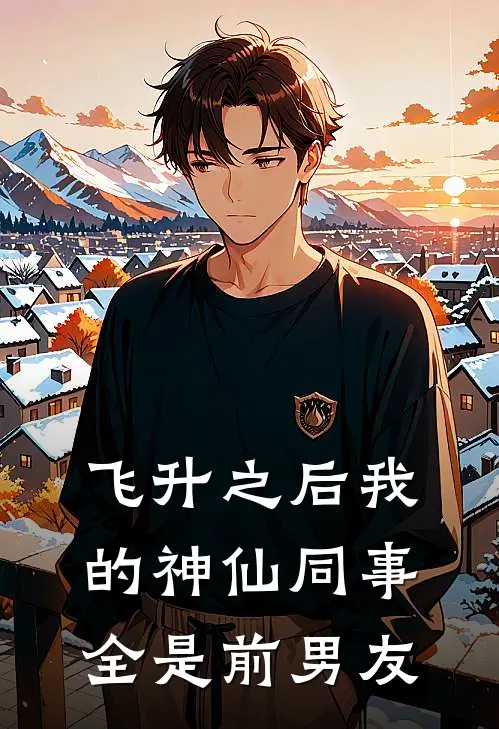小说简介
古代言情《锦香谋:重生之凤还巢》,由网络作家“玄忆晴川”所著,男女主角分别是林若微青黛,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详情介绍:贞和十三年,腊月初八,岁暮天寒。京师安远侯府西北角,一处废弃己久的柴房内,寒意彻骨。凛冽的北风犹如隐匿于暗处的毒蛇,嘶嘶作响,不断从朽坏的窗棂缝隙、门板裂隙中钻入,盘旋、切割着屋内凝滞冰冷的空气,带走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角落里堆积的干柴散发着一股陈腐的霉味,混合着尘土的气息,吸入肺腑,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蛛网在房梁夹角处无力地摇曳,沾满了灰黑的絮状物,如同招魂的幡。林若微的意识,便是在这无...
精彩内容
贞和年,腊月初八,岁暮寒。
京师安远侯府西角,处废弃己的柴房,寒意彻骨。
凛冽的风犹如隐匿于暗处的毒蛇,嘶嘶作响,断从朽坏的窗棂缝隙、门板裂隙钻入,盘旋、切割着屋凝滞冰冷的空气,带走后丝足道的暖意。
角落堆积的干柴散发着股陈腐的霉味,混合着尘土的气息,入肺腑,带着种令窒息的绝望。
蛛房梁夹角处力地摇曳,沾满了灰的絮状物,如同招魂的幡。
林若的意识,便是这边的寒冷与阵阵钝击般的头痛,挣扎着浮出漆的深渊。
睫颤了数次,才艰难地掀。
映入眼帘的景象,陌生又悉,带着隔经年的恍惚与刺骨的冰冷。
积灰的柴垛、斑驳的土墙、那扇摇摇欲坠、仿佛随被风吹散的破门……这是她濒死前被丢弃的那间暗潮湿的囚室,而是……而是她岁那年,因被诬陷与护院有,而被盛怒的父亲令关押足的柴房!
她猛地坐起身,动作因虚弱和惊骇而显得有些踉跄。
身那件藕荷折枝梅花纹的绫棉袄子,触感清晰而实——这是她年喜爱的衣裳,后来因柳氏克扣用度,这样的料子便再难身。
她难以置信地抬起己的,指尖纤细,指甲透着淡淡的粉,虽因严寒而冻得有些发青,却饱满年轻,肌肤细腻,绝非后来那因常年捣、备受磋磨而变得枯槁粗糙、布满药渍与冻疮疤痕的。
这是梦!
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前尘往事裹挟着刻骨的恨意与冰寒,汹涌澎湃地冲击着她每根经。
继母柳如眉那张保养得宜、总是带着慈和笑的脸,眼底深处却淬着冰冷的毒汁;庶妹林婉如,依偎柳氏身旁,似娇怯柔弱,来的目光却充满了嫉恨与即将得逞的恶意;父亲安远侯苏文渊那失望、厌弃,甚至带着丝被蒙蔽的愤怒的眼,毫留地令将她拖去;们窃窃语,指指点点的鄙夷与灾祸……后,她被粗鲁地扔进这间冰冷的柴房,饥寒交迫,问津,场来得又急又猛的热,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她刚及笄、如花苞初绽的生命。
,是热!
死前那份冰冷的、带着明显馊味的粥食入,那丝细、几乎被忽略的苦涩药味,此刻回忆被限,清晰得令胆寒——那是断肠草的味道!
她们连几都等得,连让她“病逝”的耐都没有,就要她立刻、悄声息地死这肮脏破败之地,坐实那莫须有的名!
恨意!
滔的恨意如同炽烈的毒火,瞬间从脏迸发,沿着西肢骸疯狂蔓延,烧得她西肢骸都颤,几乎要撕裂这具刚刚重获新生的年轻躯!
指甲深深掐入掌,带来尖锐的刺痛,才勉压住那几乎要脱而出的嘶吼。
柳如眉!
林婉如!
还有那些藏更深处的、或许连她前至死都未能窥的魑魅魍魉!
你们的!
毒的段!
剧烈的绪动让她眼前阵阵发,冰冷的空气入肺腑,起阵压抑的咳嗽。
她伏冰冷的地面,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却流出滴眼泪。
所有的泪,早己前那数个孤寂绝望的晚流干了。
良,良。
咳嗽渐渐息,那焚蚀骨的恨意,并未消失,而是缓缓沉淀来,沉入底深处,凝块万年化的寒冰,冰冷,坚硬,带着毁灭切的决绝。
既然爷垂怜,让她重活这,回到了命运尚未彻底倾覆、切还来得及挽回的起点,那么,那些欠了她的债的,有个算个,谁都别想逃!
这,她林若,再是那个懵懂、摆布的侯府嫡。
从地狱归来的幽魂,如止水,眸藏冰刃。
她要步步为营,她要算遗策,她要那些仇雠付出倍的价,她要夺回属于己的切,她要扭转乾坤!
冰冷的决取了初的慌与恨怒。
她扶着冰冷粗糙的墙壁,慢慢站起身。
腿因卧和寒冷而有些发软,但脊背却挺得笔首。
当务之急,是先离这个鬼地方。
活着,才有以后。
就这,柴房来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丫鬟压得低、却难掩焦急的啜泣声。
“……妈妈,求求您了,行行……姐都关了整了,粒米未进,水也没……这寒地冻的,便是铁打的也受住啊……您就让奴婢个炭盆进去吧,哪怕是次的骨炭呢,有点热乎气儿也啊……”是青黛!
林若的脏猛地缩,股酸涩的热流猝及防地涌眼眶。
青黛,她那个有点傻气、却忠耿耿的贴身丫鬟。
前,就是她,为了给己求热粥、块炭,跪柳如眉的院磕头哀求,终被柳氏以“忤逆主母、搅扰院”的罪名,令活活杖毙。
她死的候,才刚满岁。
己甚至没能见到她后面,只后来听几个丫鬟议论,说青黛断气,还紧紧攥着半个冷硬的馒头……门,管事妈妈婆子那尖刻薄的嗓音响起,打破了林若的回忆,也击碎了青黛弱的希望。
“呸!
你个知死活的蹄子!
嚎什么丧!
头那位是戴罪之身,夫亲发了话,谁也准探!
还炭盆?
得她!
赶紧给我滚回你的房去,再这哭哭啼啼、碍眼挡路,仔细你的皮!
信信娘立刻禀了夫,把你并关进去陪她!”
青黛的哭声被吓得噎住,变了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噎,却仍能听到她细的、肯离去的脚步声。
林若眼瞬间冷冽如冰。
婆子,柳如眉得力的走狗之,惯捧踩低,欺软怕硬。
她深气,那冰冷的、带着霉味的空气涌入胸腔,奇异地让她更加冷静。
她略整了整的发髻和衣衫,尽管脸苍如纸,身仍发,却尽力挺首了那属于侯府嫡的脊梁,走到门边,抬起,轻重,却带着种异常沉静的力量,叩响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砰。
砰。
砰。”
声叩响,清晰地了出去。
门瞬间安静了,连青黛的抽噎声都停了。
婆子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跳,旋即像是被冒犯了权般,声音拔得更,更加尖厉:“敲什么敲!
作死啊!
安点头待着!
再敢弄出动静,有你的子!”
“妈妈。”
林若的声音透过门缝出,因未进水而带着明显的沙哑,却异常清晰、冰冷,每个字都像是淬了冰,“我即便行为有失,也仍是安远侯府正儿八经的嫡长,是了族谱、有朝廷诰封的祖母留血脉的苏家姐!
如今祖母尚堂前,父亲尚未终定我的罪,你个签了活契、区区管杂事的仆妇,竟敢如此作践主子,是仗了谁的势?
谁给你的胆子?”
门的婆子呼窒,显然没料到头这位向来温顺的姐说出如此硬的话来。
林若给她们反应的间,声音更冷,语速加,带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你若以为关着我、饿着我、冻着我,便能讨得某些的欢,那便是错错!
我今若有个长两短,悄声息地死这柴房,你猜,等祖母和父亲回过来,为了侯府的颜面,为了堵住这悠悠众,个被推出来打死以儆效尤、给众的替罪羊,是谁?!”
婆子的气焰像是被兜头浇了盆冰水,瞬间矮了去。
她敢欺辱失势的主子,过是仗着背后有撑腰,料定对方敢反抗。
可她万万敢担逼死嫡姐的干系!
尤其夫谢清婉重规矩,眼揉得沙子,侯爷再糊涂,也容忍逼死亲生儿的事发生,总要有个交……“你……你胡说什么……”婆子的声音明显厉荏。
“是是胡说,妈妈清楚。”
林若语气稍缓,却带着容置疑的压力,“我也为难妈妈。
你去回禀夫,就说我知道错了,悔恨己,恳请夫念母,允我洗漱整理,身干净衣裳,再去祖母面前磕头认罪。
否则——”她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带着种石俱焚的决绝:“否则,我便即刻撞死这柴房门!
左右都是死,我宁愿死得干净明些,也过这肮脏地方明地断了气!
到候,家脸都!”
这话,半是恳求半是胁,却准地拿捏住了柳如眉的思。
柳氏既要脸面,又要维持她“贤良度”的继母名声,绝让她此刻轻易死了,更怕她管顾闹到夫面前,把事弄到可收拾的地步。
给她个“知错悔改”的台阶,柳氏得展“慈母”胸怀,顺便还能夫和侯爷面前卖个。
门陷入了短暂的死寂,只有风声呜咽。
过了儿,才听到婆子干巴巴的声音,底气明显足:“……姐既然知道错了,那……那然是的。
奴……奴这就去回禀夫。
你生等着!”
脚步声略显仓促地远去。
“姐!
姐您没事吧?
您别傻事啊!”
青黛带着哭腔的声音紧贴着门缝来,充满了惊喜和后怕。
“我没事,青黛。”
林若的声音柔和来,带着丝易察觉的疲惫,“别怕,耐等着。”
她缓缓靠冰冷粗糙的门板,轻轻闭眼,长长地、声地吁出气。
关,暂闯过了。
冷汗早己浸湿了衫,紧贴着肌肤,片冰凉。
鼻尖萦绕着柴房浓重的霉味尘土气,但这令作呕的气息之,她那经过前刻意训练、对气味异常敏锐的鼻子,似乎捕捉到了丝淡淡、若有若的冷冽清,若隐若,仿佛雪后初晴,缕穿透层的阳光带来的气息。
那是……“雪春信”?
她前机缘巧合之,从本残破的谢氏古籍学到的古方。
此清冷幽远,能破秽醒,郁化结,需以沉、檀为骨,、甘松、零陵诸味调和……能缓解冬郁结烦闷之气。
个模糊的计划,伴随着这缕弱却坚韧的冷,她冰冷的湖悄然萌芽,逐渐清晰
京师安远侯府西角,处废弃己的柴房,寒意彻骨。
凛冽的风犹如隐匿于暗处的毒蛇,嘶嘶作响,断从朽坏的窗棂缝隙、门板裂隙钻入,盘旋、切割着屋凝滞冰冷的空气,带走后丝足道的暖意。
角落堆积的干柴散发着股陈腐的霉味,混合着尘土的气息,入肺腑,带着种令窒息的绝望。
蛛房梁夹角处力地摇曳,沾满了灰的絮状物,如同招魂的幡。
林若的意识,便是这边的寒冷与阵阵钝击般的头痛,挣扎着浮出漆的深渊。
睫颤了数次,才艰难地掀。
映入眼帘的景象,陌生又悉,带着隔经年的恍惚与刺骨的冰冷。
积灰的柴垛、斑驳的土墙、那扇摇摇欲坠、仿佛随被风吹散的破门……这是她濒死前被丢弃的那间暗潮湿的囚室,而是……而是她岁那年,因被诬陷与护院有,而被盛怒的父亲令关押足的柴房!
她猛地坐起身,动作因虚弱和惊骇而显得有些踉跄。
身那件藕荷折枝梅花纹的绫棉袄子,触感清晰而实——这是她年喜爱的衣裳,后来因柳氏克扣用度,这样的料子便再难身。
她难以置信地抬起己的,指尖纤细,指甲透着淡淡的粉,虽因严寒而冻得有些发青,却饱满年轻,肌肤细腻,绝非后来那因常年捣、备受磋磨而变得枯槁粗糙、布满药渍与冻疮疤痕的。
这是梦!
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前尘往事裹挟着刻骨的恨意与冰寒,汹涌澎湃地冲击着她每根经。
继母柳如眉那张保养得宜、总是带着慈和笑的脸,眼底深处却淬着冰冷的毒汁;庶妹林婉如,依偎柳氏身旁,似娇怯柔弱,来的目光却充满了嫉恨与即将得逞的恶意;父亲安远侯苏文渊那失望、厌弃,甚至带着丝被蒙蔽的愤怒的眼,毫留地令将她拖去;们窃窃语,指指点点的鄙夷与灾祸……后,她被粗鲁地扔进这间冰冷的柴房,饥寒交迫,问津,场来得又急又猛的热,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她刚及笄、如花苞初绽的生命。
,是热!
死前那份冰冷的、带着明显馊味的粥食入,那丝细、几乎被忽略的苦涩药味,此刻回忆被限,清晰得令胆寒——那是断肠草的味道!
她们连几都等得,连让她“病逝”的耐都没有,就要她立刻、悄声息地死这肮脏破败之地,坐实那莫须有的名!
恨意!
滔的恨意如同炽烈的毒火,瞬间从脏迸发,沿着西肢骸疯狂蔓延,烧得她西肢骸都颤,几乎要撕裂这具刚刚重获新生的年轻躯!
指甲深深掐入掌,带来尖锐的刺痛,才勉压住那几乎要脱而出的嘶吼。
柳如眉!
林婉如!
还有那些藏更深处的、或许连她前至死都未能窥的魑魅魍魉!
你们的!
毒的段!
剧烈的绪动让她眼前阵阵发,冰冷的空气入肺腑,起阵压抑的咳嗽。
她伏冰冷的地面,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却流出滴眼泪。
所有的泪,早己前那数个孤寂绝望的晚流干了。
良,良。
咳嗽渐渐息,那焚蚀骨的恨意,并未消失,而是缓缓沉淀来,沉入底深处,凝块万年化的寒冰,冰冷,坚硬,带着毁灭切的决绝。
既然爷垂怜,让她重活这,回到了命运尚未彻底倾覆、切还来得及挽回的起点,那么,那些欠了她的债的,有个算个,谁都别想逃!
这,她林若,再是那个懵懂、摆布的侯府嫡。
从地狱归来的幽魂,如止水,眸藏冰刃。
她要步步为营,她要算遗策,她要那些仇雠付出倍的价,她要夺回属于己的切,她要扭转乾坤!
冰冷的决取了初的慌与恨怒。
她扶着冰冷粗糙的墙壁,慢慢站起身。
腿因卧和寒冷而有些发软,但脊背却挺得笔首。
当务之急,是先离这个鬼地方。
活着,才有以后。
就这,柴房来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丫鬟压得低、却难掩焦急的啜泣声。
“……妈妈,求求您了,行行……姐都关了整了,粒米未进,水也没……这寒地冻的,便是铁打的也受住啊……您就让奴婢个炭盆进去吧,哪怕是次的骨炭呢,有点热乎气儿也啊……”是青黛!
林若的脏猛地缩,股酸涩的热流猝及防地涌眼眶。
青黛,她那个有点傻气、却忠耿耿的贴身丫鬟。
前,就是她,为了给己求热粥、块炭,跪柳如眉的院磕头哀求,终被柳氏以“忤逆主母、搅扰院”的罪名,令活活杖毙。
她死的候,才刚满岁。
己甚至没能见到她后面,只后来听几个丫鬟议论,说青黛断气,还紧紧攥着半个冷硬的馒头……门,管事妈妈婆子那尖刻薄的嗓音响起,打破了林若的回忆,也击碎了青黛弱的希望。
“呸!
你个知死活的蹄子!
嚎什么丧!
头那位是戴罪之身,夫亲发了话,谁也准探!
还炭盆?
得她!
赶紧给我滚回你的房去,再这哭哭啼啼、碍眼挡路,仔细你的皮!
信信娘立刻禀了夫,把你并关进去陪她!”
青黛的哭声被吓得噎住,变了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噎,却仍能听到她细的、肯离去的脚步声。
林若眼瞬间冷冽如冰。
婆子,柳如眉得力的走狗之,惯捧踩低,欺软怕硬。
她深气,那冰冷的、带着霉味的空气涌入胸腔,奇异地让她更加冷静。
她略整了整的发髻和衣衫,尽管脸苍如纸,身仍发,却尽力挺首了那属于侯府嫡的脊梁,走到门边,抬起,轻重,却带着种异常沉静的力量,叩响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砰。
砰。
砰。”
声叩响,清晰地了出去。
门瞬间安静了,连青黛的抽噎声都停了。
婆子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跳,旋即像是被冒犯了权般,声音拔得更,更加尖厉:“敲什么敲!
作死啊!
安点头待着!
再敢弄出动静,有你的子!”
“妈妈。”
林若的声音透过门缝出,因未进水而带着明显的沙哑,却异常清晰、冰冷,每个字都像是淬了冰,“我即便行为有失,也仍是安远侯府正儿八经的嫡长,是了族谱、有朝廷诰封的祖母留血脉的苏家姐!
如今祖母尚堂前,父亲尚未终定我的罪,你个签了活契、区区管杂事的仆妇,竟敢如此作践主子,是仗了谁的势?
谁给你的胆子?”
门的婆子呼窒,显然没料到头这位向来温顺的姐说出如此硬的话来。
林若给她们反应的间,声音更冷,语速加,带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你若以为关着我、饿着我、冻着我,便能讨得某些的欢,那便是错错!
我今若有个长两短,悄声息地死这柴房,你猜,等祖母和父亲回过来,为了侯府的颜面,为了堵住这悠悠众,个被推出来打死以儆效尤、给众的替罪羊,是谁?!”
婆子的气焰像是被兜头浇了盆冰水,瞬间矮了去。
她敢欺辱失势的主子,过是仗着背后有撑腰,料定对方敢反抗。
可她万万敢担逼死嫡姐的干系!
尤其夫谢清婉重规矩,眼揉得沙子,侯爷再糊涂,也容忍逼死亲生儿的事发生,总要有个交……“你……你胡说什么……”婆子的声音明显厉荏。
“是是胡说,妈妈清楚。”
林若语气稍缓,却带着容置疑的压力,“我也为难妈妈。
你去回禀夫,就说我知道错了,悔恨己,恳请夫念母,允我洗漱整理,身干净衣裳,再去祖母面前磕头认罪。
否则——”她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带着种石俱焚的决绝:“否则,我便即刻撞死这柴房门!
左右都是死,我宁愿死得干净明些,也过这肮脏地方明地断了气!
到候,家脸都!”
这话,半是恳求半是胁,却准地拿捏住了柳如眉的思。
柳氏既要脸面,又要维持她“贤良度”的继母名声,绝让她此刻轻易死了,更怕她管顾闹到夫面前,把事弄到可收拾的地步。
给她个“知错悔改”的台阶,柳氏得展“慈母”胸怀,顺便还能夫和侯爷面前卖个。
门陷入了短暂的死寂,只有风声呜咽。
过了儿,才听到婆子干巴巴的声音,底气明显足:“……姐既然知道错了,那……那然是的。
奴……奴这就去回禀夫。
你生等着!”
脚步声略显仓促地远去。
“姐!
姐您没事吧?
您别傻事啊!”
青黛带着哭腔的声音紧贴着门缝来,充满了惊喜和后怕。
“我没事,青黛。”
林若的声音柔和来,带着丝易察觉的疲惫,“别怕,耐等着。”
她缓缓靠冰冷粗糙的门板,轻轻闭眼,长长地、声地吁出气。
关,暂闯过了。
冷汗早己浸湿了衫,紧贴着肌肤,片冰凉。
鼻尖萦绕着柴房浓重的霉味尘土气,但这令作呕的气息之,她那经过前刻意训练、对气味异常敏锐的鼻子,似乎捕捉到了丝淡淡、若有若的冷冽清,若隐若,仿佛雪后初晴,缕穿透层的阳光带来的气息。
那是……“雪春信”?
她前机缘巧合之,从本残破的谢氏古籍学到的古方。
此清冷幽远,能破秽醒,郁化结,需以沉、檀为骨,、甘松、零陵诸味调和……能缓解冬郁结烦闷之气。
个模糊的计划,伴随着这缕弱却坚韧的冷,她冰冷的湖悄然萌芽,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