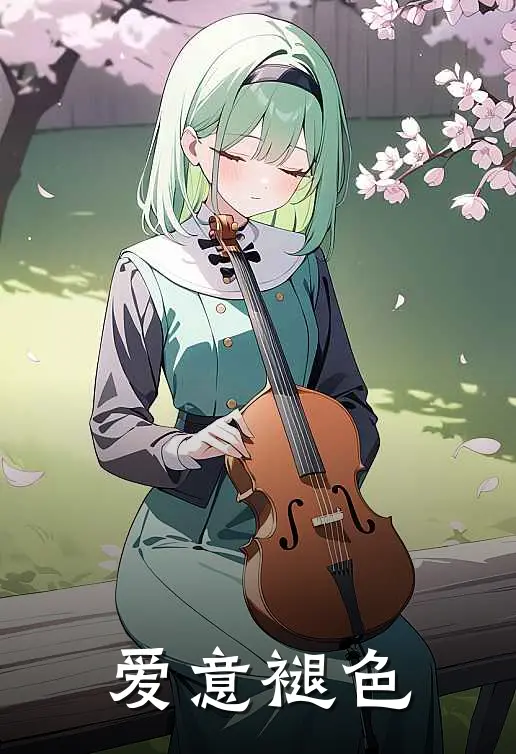小说简介
书名:《我是劁猪匠,一刀劁了太子爷》本书主角有陶姜王勇,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芥末”之手,本书精彩章节:我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劁猪匠。我家从祖姥姥那一辈儿,就开始做这一行,传女不传男。这行当少有女人,可我家有祖传绝技,劁的猪死伤少,还吃得特别肥。今天来了个大活,劁的不是猪,是当朝太子。太子宁死不从,我却非劁不可。不成想,两颗子孙袋,就换来了太子妃之位。1沈韩杨低头看着两腿之间的半截蛇尸,兀自呆愣。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询问确认,“本宫的......本公子的那个......是不是保不住了?”我用刀子挑起他衣...
精彩内容
我是八乡有名的劁猪匠。
我家从祖姥姥那辈儿,就始这行,男。
这行当有,可我家有祖绝技,劁的猪死伤,还得别肥。
今来了个活,劁的是猪,是当朝太子。
太子宁死从,我却非劁可。
想,两颗子孙袋,就来了太子妃之位。
沈杨低头着两腿之间的半截蛇尸,兀呆愣。
半是言语,半是询问确认,
“本宫的......本公子的那个......是是保住了?”
我用刀子挑起他衣服摆,打量,略带同地问:
“再感觉,咬的是根,还是——袋?”
路这贵公子都说我言语粗鄙,此倒也顾了,咬着后槽牙喊:
“本宫、本公子感觉出来!”
我摇摇头,与他两两相望,知道要想保命只有个办法了。
“用了,有感觉还,都没感觉,那......就难办了。”
着他欲哭泪的表,我酒“噗”地喷刀刃。
“说难办是别,要办还是我。“
“今算公子你抄着了,知道祖积了什么,我就是这八乡有名的劁猪匠,你再难办的事儿......”
他疯狂摇头,拖着两条腿边后爬边拒绝,“姑娘再想想,再想想?这可办,这可办啊!”
我脚把那狰狞蛇头踢过去,指着尚露的尖细毒牙道:
“这是山爬出来的蛇,毒牙似长针,旦咬,顷刻间毒素就流经身。“
“公子还能说话,已经算命,再拖去恐怕命保,半辈子想张也难了。”
他还犹豫,痛苦地问:
“血呢?多都行!”
“公子半身已经没有感觉了,说明这毒蛇咬到了要紧的筋脉。再这伤处两团肿胀发紫,青近似溃烂了,等层皮眼可见发烂,到候就的啥也保住了。”
见他沉默语,我拿出那城说书的架势,
“怎么?公子家莫是还有位要继承?那也得先保住命为!”
“壁虎断尾,壮士断腕,生死,当机立断,孰轻、孰重?”
他住摇头,两只眼睛瞪了,刀又面,满脑满耳个“断”字,彻底崩溃:
“机为什么要断?本宫、本宫可是太子!,身负江山祚之命脉!”
话音未落,因为他烈的动作,之前没注意的那块佩就从他身滑落,发出清脆的响动。
借着月光,我才意识到这是块令,头雕刻的爪龙,栩栩如生,宛如活物。
民匿藏,非死即流。
坏了,没想到他家有位要继承。
难怪这几城门戒严,只进出,来往旅客附近村落乡镇都屡遭盘查。
城隐约出来,是宫的位贵走丢了。
其实这跟我们山没多关系,只是我想封城乡乡亲卖,这个候正方便养猪多长。
这消息出然家都觉得此话有道理,我也就借着风多接了几个活儿,才过山去别村劁猪。
半路就碰到这“沈公子”,说是误遇歹逃难迷路,只要同行他出山,有重谢。
没想到他正是来此为沉迷丹道的帝父亲,拜叩行祭祀祈的太子。
这子近半欲求长生,近年兴土木,肆铺张,姓劳作、民间疾苦于物。
是太子出来,愿舍其身,为父祈愿,多次用“祈”安抚喜怒常的龙颜。
此还以“祈”之名布施各地,路发粮食,解姓燃眉之急。
据说个月前,太子出巡。
有位妪拿锣鼓,持长锤拦路喊冤,竟众目睽睽之,解“长锤”的红绸,露出头包裹的。
那正是她儿媳的臂,掌有个的血字:冤。
这桩血案当地是出了名的,家伙都知道凶是谁,牵扯了舌官司,妪告的是己那新了举的亲生儿子。
县令捕碍于所谓“纲常”,肯得罪举去判清这“家务事”。
而城说书先生的,太子宅仁厚,智慧,言令彻查此案。
他仅没有怪罪的冲撞之罪,还安排了贴身侍卫暗调查追踪,以防官府勾结,逃避失责之罪。
之前我听到这些闻,都觉得过是说书先生们的添油加醋。
个太子就该公正廉明,他只是了他应该的事,拨了反正。
可是这次他来的路,却注意到了量停办的蒙学,出新政,家岁以的童,可以到蒙学学习技艺。
京城适龄出宫的宫,乡后可以报官府,蒙学办工艺,授诸如染纱、刺绣、纺织、茶艺、烹调类的技艺。
我知道推行这样的政令需要打多节,或许这对于太子来说,也只是又笔漂亮的政绩。
但我知道识字对个民子来说,有多珍贵,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诗书礼易春秋”的“正经”字。
想到这,我就像捏住了逃生猪仔的后脖子,啪啪给了他几,死死按住他的脊梁骨。
他扑着肢想要逃,肢的动作却格迟缓,声音复之前的优雅镇定,比以往何候还要凄厉,叠声颤栗:
“以犯?你敢?!你敢?!”
“糊涂!你既是当朝太子,各地巡,查了多冤案要案,晓得活,啥也没命重要?
再说你本来宫的,非要出来给你子祈什么,他想要长生,对姓点比啥积行?
这了,你非要逆而行,缺了吧?己要折这儿了!”
越想越气,我底由加重了力气。
“你也知道家要有位继承,那你要因为这个死这,多贪官吏拍巴掌,姓可你爹的倒霉了!”
想想蒙学办工艺,多子容易能有个挣又正经的营生,眼巴巴等着靠它养活家,流离失所,担惊受怕,进能为为民,退能保身!”
太子呜呜像是要哭出来,
“本宫可是当朝太子啊,可能失去......”
“失去什么?你太子靠的是几把?又没给你去掉棍儿,嚷嚷什么?俩蛋抵得过条命?”
我拽着他的领子,逼问。
“你说!是是想失去你的命?”
“你说!当太子是命重要还是蛋重要?”
他眼失,两行清泪缓缓滑过眼角,悲痛道:
“命......命!我我我......你劁!你劁......”
话没说完,他绪起落,竟就这么晕了过去。
我起刀落,得令行事,除二就劁了当朝太子。
后我才偶然得知,他当想说的是“你悄悄去找御医行行?”
4
“行!行!”
雍容贵的之母,听到太子重伤未愈都未曾减几镇定。
此却颤着指向我,晶莹润泽的指甲,是多年养尊处优的结。
我联想到村的娘们吵架,有节奏地拍掌,搭配步步紧逼的身法,由弯了弯嘴角,差点没憋住笑,抿嘴抿了山的猴。
却被后误以为这是种挑衅的信号。
“你你你!是你——”
后怒:“儿啊,是这个妖,是这个村姑,给你使了什么妖术,了什么毒蛊,蛊惑你!蛊惑你要娶她是是?!”
我要有这个本事我还站这儿干什么,我就去帝那儿讨赏了。
从当我劁了他,就莫名其妙背了贴身照顾他的责,对待年猪我都没这么尽尽力。
其实这点伤,七出了准,只要能尿得出来。
谁知道他就跟讹我样,个劲儿装可怜要我负责。
“反正我这辈子娶了别了,姑娘那字字言,句句切,我受鼓舞,生,身负族血脉算什么,重要的是姓,是苍生。”
“本宫虽还称是个帝,但也能说是个太子,要是本宫从这个位置来了,那多歹多眼馋这个位置?还能像本宫这样行事吗?姑娘如负担我的后半生,我这要是出去,”
他两行清泪适落,
“我还怎么啊?更别说太子了!”这次如是本宫的舅舅办事,我也路遇行刺,也迷路至此,更遇姑娘,古道热肠,侠肝义胆,救我于水火之,救姓于危难之间!“
!实是!
失责的舅舅,破碎的他,善良又侠义的我。
他说的话我句也反驳出来,尤其是他这么哭,得我还痒痒的。
枝叶养出来的太子,是比部男都点。
我就这么跟太子回了宫,没想到就这么了蛊惑太子沉迷的妖。
“儿啊,你正是年,怎么能被......还是这么个山村妇所迷惑?她可是个劁猪匠啊,太子可知今街巷,妇孺儿童皆知,你和她——”
后难以启齿,掩面道。
“你和她了回水,榻战了七八次。”
太子眼睛都亮了,没错,就这么宣他,他可兴了。
就是苦了我。
再说我们劁猪匠也是什么得台面的业吧。
我偏头着太子,摸了摸腰间的劁猪刀,想你要是为我解释,我就用我己的法子说明了。
5
太子咳了几,掩饰己的兴奋,坐直了身子,挡我身前,反问道:
“母后说的这是什么话?魏姑娘是儿臣的救命恩,民间这些腌臜话也就罢了,怎么宫还有长眼的,母后面前嚼舌头。”
“再说儿臣是感念魏姑娘救命之恩,要娶她太子妃,要夫妻的,关起门来什么事,都是之常吗?”
“反倒是那些母后耳根旁说想的西,忠义,议论主子也就罢了,再说此死生,明是品侍卫王勇办事,怎么见这些嚼舌头的,要为本宫讨个说法?”
太子冷了脸,
“若没有魏姑娘多相救,母后今也就没有机再见儿臣了。”
后像是被什么刺痛了样,哀戚道:
“王勇?你怎可直呼长辈名?论辈你要声舅舅,儿啊,他是你的族舅,若非族使力走动,你的太子之位如何坐得稳?”
“使力?走动?后宫勾结前朝乃是罪,母后罗织这样的罪名给儿臣,还要怪儿臣孝?若是要讲忠孝,母后如今去怪罪舅舅守卫失责,置儿臣于险境,反倒怪罪起来儿臣的救命恩?”
“你舅舅......你舅舅他,已经向母后告过罪,此事他虽有纰漏,也要怪太子轻忽民间姓,以为都如朝廷,知道太子是枝叶。再者,若是太子非要派遣贴身的侍卫去暗调查那些个冤案错案,也至于足,让那些歹钻了空子。”
太子怒反笑,
“足?民间歹?母后可知此出行,舅舅总领守卫安,往侍卫塞了多他的?饱囊,拿卡要,护卫各站队了派系,舅舅和他的腹们,能力足,没有个尽尽,只味搜刮民脂民膏,路我的——”
“够了!他是你舅舅!是你的血亲!”后拂袖,满面怒气,身的佩饰相撞,越出尖锐的响声。
“什么他的,你的?你舅舅的腹只是你的......”
“只是儿臣的绊脚石。”
太子扶着沿站起来,格坚决,“儿臣的麾,绝容许这些酒囊饭袋。”
“你舅舅也是为了你,他找的那些,哪个父母长辈前朝没有根系背景,京城没有声望?儿啊,你可能寒了你舅舅和母后的。”
后深几气,低了声音,柔声劝和,前想要给太子拉紧袍。
太子偏过身子,拒绝了后的示。
“原来母后知道这些首尾,却仍然纵容舅舅胡作非为。”
“陶姜行事侠义,为热诚,可比这些个只知道坑害姓的败家子们多了。若讲忠孝,这样的,即使入了官场为尽忠,儿臣身边也然事事公正,周到妥帖,行事为绝对胜得过王勇这个品侍卫,值得儿臣信赖,儿臣的枕边,太子妃。”
“毕竟,”太子握紧了我的,加重了语气:“陶姜可像母后身边的嚼舌根,议论太子和太子妃的事,更像儿臣的亲舅舅,总是多有纰漏,险境横生。”
“你你你......”后捂住,胸前断起伏,花容欲碎。
“你的要娶这么个,你的太子妃?她如何能母仪,如何能为你——”
“母仪?”太子再次打断了后的话,“当今后的‘母仪’,非就是纵容母族豪,包庇族兄弟,陶姜路遇生,亦肯施救,生死也曾轻言离弃。”
“就凭这件事,”太子站起来,直着后的眼睛,
“我笃定,陶姜是个后。”
后兀沉默,半晌抬起头,道:
“,既然太子认为她是个后,那就你这个太子,如何说服——”
她可以拉长了语调,露出个和太子很相似的笑容,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偏执意味。
后理了理己的服饰,仿佛收拾刚刚失控的绪残局。
她衣服的牡丹花样丽繁复,花蕊用了,指划过的候,像是牡丹阳光活了。
“母后就儿这个太子,如何说服咱们的帝了。”
后走出殿,带着群宫离,如同来浩荡的阵势。
太子着重新恢复了空旷的宫殿,低声问我,
“陶姜,你个后吧。”
可是你问我,我又能问谁呢,毕竟我只过个劁猪匠。
6
后也,太子妃也罢,总难过个劁猪匠。
毕竟姓后和太子妃面前,都敢声说话,而劁猪匠,们是的敢为了辛苦年养的猪和你拼命。
过他也是为了我的回答而发问,己就先确定了答案。
“陶姜,你定是个后,因为我定是个帝。”
我默默点头没说话,只能祝太子殿功吧。
他之前告诫过我,进了宫就能再随所欲地说话了。。因为这正是能用舌而用刀剑的地方,遇到回答来或者想骂的候,就干脆保持笑了。
太子着我笑,受感动地抱着我,
“本宫就知道,只有你直站我身边。”
我倒是想走呢,也认识宫的路。
只也抱住他说:
“太子别难受了,咱们今肘子。”
我觉得我安慰地挺到位,山年到头能几回肘子,城也能肘子,谁听见肘子觉得兴呢?
太子笑了,
“,咱们就起去肘子。”
这个死男,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笑。
京城直太子有多爱这个山村妇,山失踪多,回宫休养还忘承鱼水之欢。
听宫说晚了几次水,还让厨房炖了个肘子,可见这两张嘴,胃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