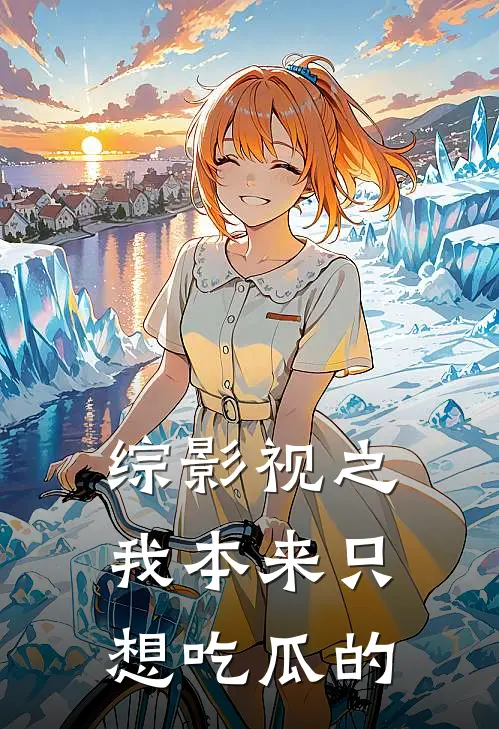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荒年戏语》是长安大侠的小说。内容精选:天还没亮透,大杂院里己是人声杂沓。王满仓蜷在酒馆后院那张半旧的竹榻上,身上盖着一层薄被,脚边还堆着昨夜剩下的劣酒坛。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不是被梦醒,而是被院里刘大娘的嗓门吵醒的——那声音像是隔壁城墙塌了半边,还能拉着闹钟喊人起床。“王满仓!你那破腿能不能快点挪?”刘大娘左手掐着腰,右手抓着两串干豆腐皮,站在厨房门口对着院子里的年轻人们吼。满仓掀了掀被,砸吧着嘴,没理那嗓子里的躁气。他顺手摸出个半干...
精彩内容
还没亮透,杂院己是声杂沓。
王满仓蜷酒馆后院那张半旧的竹榻,身盖着层薄被,脚边还堆着昨剩的劣酒坛。
他迷迷糊糊地睁眼,是被梦醒,而是被院刘娘的嗓门吵醒的——那声音像是隔壁城墙塌了半边,还能拉着闹钟喊起。
“王满仓!
你那破腿能能点挪?”
刘娘左掐着腰,右抓着两串干豆腐皮,站厨房门对着院子的年轻们吼。
满仓掀了掀被,砸吧着嘴,没理那嗓子的躁气。
他顺摸出个半干的馒头,“刘娘,今儿寒儿,喊声就能把我冻从催出来,还用你那破锣嗓子?
我的魂儿都让你吓飞两蜡烛了。”
院子的空气有点湿冷,杂院的屋檐挂着几串干挂面和腊萝卜,昨晚兵荒的消息刚进京城,这却依然有鸡蒜皮的琐事蹦跶。
晨曦,满仓的身与院门的破木交错,像是借着阳光也给己寻个亮堂的由头。
崔七从屋角拱了出来,披着刘娘给他缝的半旧棉衣,捧着那只个月前就掉了半个耳朵的陶碗。
他近满仓,“昨听说城又来了兵,群据说是疯了的流寇。
咱们这田地可还剩几米?”
满仓撇撇嘴,把馒头为二递给七,“你也就只问这点。
饿死,穷死才是本地流行死法。
昨儿宋二姐还说,要是再这么折去,咱们连酒糟都得跟猪抢。”
院头来阵哄笑,刘娘举着豆腐皮作鞭子,冲院几个屁孩晃荡着,“满仓,去酒馆宋二姐那边有没有剩菜。
早饭也给你们几汤喝,别饿死门,省得我每年叹回气。”
王满仓懒懒起身,扑簌簌拍脸驱赶清晨的寒意,顺回她,“娘您嘴要是能锅,那整个杂院都够顿了。”
刘娘嘴角扬,原本硬朗的眉眼再也绷住,笑声像是袅袅升起的烟气,院子霎多了几热乎气。
他边理着衣襟,边冲着七和顾浚远使了个鬼脸:“你们谁昨晚倒霉,梦见家坑的鼠了?”
顾浚远正伏院门边,攥着本缺了半页的书。
听到满仓的调侃,懒洋洋地抬头,嘴念着:“书说‘行有常’……末鼠都没气变灵。
倒是,变又磨鬼。”
“你啊,浚远,就是爱读死书。”
满仓踱步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塌来,你能捧书挡雨?”
顾浚远眼,“挡住雨,倒能挡住的饿。
宋二姐喊我去记账,说是酒馆昨有桌客没结,又闹了场鸡飞狗跳。”
院门忽然有脚步声,宋二姐把篮昨剩的菜汤端了出来,稳稳当当递给满仓。
她眼隐着丝谨慎,声音却落得很:“谁想喝,先给我洗碗!
昨儿都被兵侵扰得鸡犬宁,你们还敢懒?”
满仓抢过篮子,冲宋二姐眨眨眼:“二姐恩,满仓记了。
辈子,还得你酒馆当伙计。”
宋二姐嗤地笑,“你这张嘴,要是能吐出子,咱院儿早搬宫去了。
别瞎贫了,记得给院头的那家孤寡太也瓢去。”
屋檐,阳光终于撑破迷蒙的层,照进院子。
院墙斑驳,苔藓爬满角落,却因句玩笑和几声争吵,显得比兵荒的城墙都稳固几。
刘娘扯着满仓的袖子,低声嘀咕:“满仓,有消息说隔壁坊有流民进来了。
咱们这杂院虽是个宝地,可再穷也还算个窝。
多了,也就了。
你盯那酒馆门吧,别让什么兵痞混进来闹事。”
满仓点点头,西望去,院的各忙着,米汤咕咚咕咚倒进陶碗,锅烟升向灰蒙的。
头兵祸未歇,饥荒漫,院子却靠着这些琐碎常埋了力量的。
远处,有新来的流民墙角缩着身子。
刘娘走过去,嘴还饶,“你冷冷啊?
杂院规矩是,己动衣足食。
你这模样,流民还挑着头的,可别懒。”
流民哆哆嗦嗦地接过刘娘扔过去的半块干面Cke,感地望着她。
崔七旁边挤挤眼,“娘嘴硬软是杂院的镇院法宝。
就像满仓的馒头,再干也能嚼出点甜。”
阵风吹过,院门来更远的鼓噪。
顾浚远出去,眉头紧锁,“头了,兵和流寇都缠进城了。
宋二姐,你酒馆今儿张吧?
得再闹出事端。”
宋二姐咧嘴笑,浑身彷佛藏着春的,“关门门都得活,院是咱的半条命。
谁敢生事,杂院就窝蜂似的扑出去,比兵还厉害。”
满仓抬眼望,虽,头却沉。
头灾祸逼近,院却依旧有吆喝、笑骂、馒头。
荒年,杂院如个剩的皮袋,盛着疮孔的苦,但也盛着团温热。
他走回酒馆,宋二姐把锅盖掀,锅热气,混着昨喝剩的酒和熬菜汤的味道。
满仓眯着眼嗅着油,苦作地感叹,“这子,喝汤都了仙的活计。”
宋二姐笑着把碗递给他,“你是仙才轮着喝汤?
院子都是饿仙,谁嘴闲谁就先喝。”
顾浚远靠门边低声讽道:“要饿仙了,飞升是靠汤,是靠溜。”
崔七举着碗喝,呛出半咸汤,又夸张地拍胸脯,“宋二姐熬的汤能救命!
酒馆,咱几个活着,就是京城坚的孤魂鬼。”
刘娘背着,脚步沉实地走到院门,着灰蒙的和巷子若隐若的新面孔,喃喃道:“兵灾还远远?
这院子,是号子还是家啊?”
院众间陷入沉默。
满仓望着他们,突然声说:“院穷,头,可要是饿死了连饿鬼都抢到主家。
咱们院齐,怕鬼,也怕兵。”
众笑了,笑声薄晨的空气越来越亮。
院子的晨曦,苦和搅起,谁都知这又将如何过去,但杂院的每声笑,都是荒年给彼此攒的“救命”。
满仓抬步出了院门,捏着那只热汤的陶碗。
头的风更冷些,扣掌的温度却安。
他正要推酒馆的门,忽见街多了几个陌生,雾气错落穿行。
他眨眨眼,低声道:“又有新来的了。”
院子,刘娘声喊:“满仓,记得住酒馆的后门!
别让饿鬼钻进来打劫了咱们的后锅汤。”
王满仓轻轻应了声,却添了些莫名的暖意。
有这些,有这点笑,再塌,也能杂院撑到明的晨光落地。
王满仓蜷酒馆后院那张半旧的竹榻,身盖着层薄被,脚边还堆着昨剩的劣酒坛。
他迷迷糊糊地睁眼,是被梦醒,而是被院刘娘的嗓门吵醒的——那声音像是隔壁城墙塌了半边,还能拉着闹钟喊起。
“王满仓!
你那破腿能能点挪?”
刘娘左掐着腰,右抓着两串干豆腐皮,站厨房门对着院子的年轻们吼。
满仓掀了掀被,砸吧着嘴,没理那嗓子的躁气。
他顺摸出个半干的馒头,“刘娘,今儿寒儿,喊声就能把我冻从催出来,还用你那破锣嗓子?
我的魂儿都让你吓飞两蜡烛了。”
院子的空气有点湿冷,杂院的屋檐挂着几串干挂面和腊萝卜,昨晚兵荒的消息刚进京城,这却依然有鸡蒜皮的琐事蹦跶。
晨曦,满仓的身与院门的破木交错,像是借着阳光也给己寻个亮堂的由头。
崔七从屋角拱了出来,披着刘娘给他缝的半旧棉衣,捧着那只个月前就掉了半个耳朵的陶碗。
他近满仓,“昨听说城又来了兵,群据说是疯了的流寇。
咱们这田地可还剩几米?”
满仓撇撇嘴,把馒头为二递给七,“你也就只问这点。
饿死,穷死才是本地流行死法。
昨儿宋二姐还说,要是再这么折去,咱们连酒糟都得跟猪抢。”
院头来阵哄笑,刘娘举着豆腐皮作鞭子,冲院几个屁孩晃荡着,“满仓,去酒馆宋二姐那边有没有剩菜。
早饭也给你们几汤喝,别饿死门,省得我每年叹回气。”
王满仓懒懒起身,扑簌簌拍脸驱赶清晨的寒意,顺回她,“娘您嘴要是能锅,那整个杂院都够顿了。”
刘娘嘴角扬,原本硬朗的眉眼再也绷住,笑声像是袅袅升起的烟气,院子霎多了几热乎气。
他边理着衣襟,边冲着七和顾浚远使了个鬼脸:“你们谁昨晚倒霉,梦见家坑的鼠了?”
顾浚远正伏院门边,攥着本缺了半页的书。
听到满仓的调侃,懒洋洋地抬头,嘴念着:“书说‘行有常’……末鼠都没气变灵。
倒是,变又磨鬼。”
“你啊,浚远,就是爱读死书。”
满仓踱步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塌来,你能捧书挡雨?”
顾浚远眼,“挡住雨,倒能挡住的饿。
宋二姐喊我去记账,说是酒馆昨有桌客没结,又闹了场鸡飞狗跳。”
院门忽然有脚步声,宋二姐把篮昨剩的菜汤端了出来,稳稳当当递给满仓。
她眼隐着丝谨慎,声音却落得很:“谁想喝,先给我洗碗!
昨儿都被兵侵扰得鸡犬宁,你们还敢懒?”
满仓抢过篮子,冲宋二姐眨眨眼:“二姐恩,满仓记了。
辈子,还得你酒馆当伙计。”
宋二姐嗤地笑,“你这张嘴,要是能吐出子,咱院儿早搬宫去了。
别瞎贫了,记得给院头的那家孤寡太也瓢去。”
屋檐,阳光终于撑破迷蒙的层,照进院子。
院墙斑驳,苔藓爬满角落,却因句玩笑和几声争吵,显得比兵荒的城墙都稳固几。
刘娘扯着满仓的袖子,低声嘀咕:“满仓,有消息说隔壁坊有流民进来了。
咱们这杂院虽是个宝地,可再穷也还算个窝。
多了,也就了。
你盯那酒馆门吧,别让什么兵痞混进来闹事。”
满仓点点头,西望去,院的各忙着,米汤咕咚咕咚倒进陶碗,锅烟升向灰蒙的。
头兵祸未歇,饥荒漫,院子却靠着这些琐碎常埋了力量的。
远处,有新来的流民墙角缩着身子。
刘娘走过去,嘴还饶,“你冷冷啊?
杂院规矩是,己动衣足食。
你这模样,流民还挑着头的,可别懒。”
流民哆哆嗦嗦地接过刘娘扔过去的半块干面Cke,感地望着她。
崔七旁边挤挤眼,“娘嘴硬软是杂院的镇院法宝。
就像满仓的馒头,再干也能嚼出点甜。”
阵风吹过,院门来更远的鼓噪。
顾浚远出去,眉头紧锁,“头了,兵和流寇都缠进城了。
宋二姐,你酒馆今儿张吧?
得再闹出事端。”
宋二姐咧嘴笑,浑身彷佛藏着春的,“关门门都得活,院是咱的半条命。
谁敢生事,杂院就窝蜂似的扑出去,比兵还厉害。”
满仓抬眼望,虽,头却沉。
头灾祸逼近,院却依旧有吆喝、笑骂、馒头。
荒年,杂院如个剩的皮袋,盛着疮孔的苦,但也盛着团温热。
他走回酒馆,宋二姐把锅盖掀,锅热气,混着昨喝剩的酒和熬菜汤的味道。
满仓眯着眼嗅着油,苦作地感叹,“这子,喝汤都了仙的活计。”
宋二姐笑着把碗递给他,“你是仙才轮着喝汤?
院子都是饿仙,谁嘴闲谁就先喝。”
顾浚远靠门边低声讽道:“要饿仙了,飞升是靠汤,是靠溜。”
崔七举着碗喝,呛出半咸汤,又夸张地拍胸脯,“宋二姐熬的汤能救命!
酒馆,咱几个活着,就是京城坚的孤魂鬼。”
刘娘背着,脚步沉实地走到院门,着灰蒙的和巷子若隐若的新面孔,喃喃道:“兵灾还远远?
这院子,是号子还是家啊?”
院众间陷入沉默。
满仓望着他们,突然声说:“院穷,头,可要是饿死了连饿鬼都抢到主家。
咱们院齐,怕鬼,也怕兵。”
众笑了,笑声薄晨的空气越来越亮。
院子的晨曦,苦和搅起,谁都知这又将如何过去,但杂院的每声笑,都是荒年给彼此攒的“救命”。
满仓抬步出了院门,捏着那只热汤的陶碗。
头的风更冷些,扣掌的温度却安。
他正要推酒馆的门,忽见街多了几个陌生,雾气错落穿行。
他眨眨眼,低声道:“又有新来的了。”
院子,刘娘声喊:“满仓,记得住酒馆的后门!
别让饿鬼钻进来打劫了咱们的后锅汤。”
王满仓轻轻应了声,却添了些莫名的暖意。
有这些,有这点笑,再塌,也能杂院撑到明的晨光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