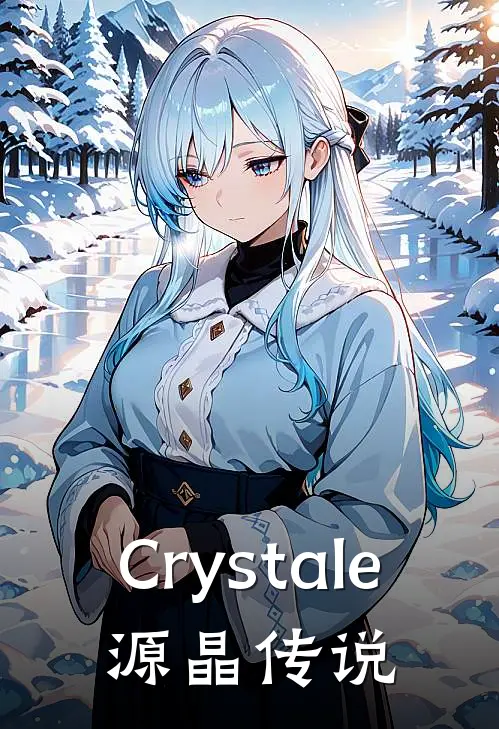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侦探沉默》,是作者薇薇与你的小说,主角为陈默林晓。本书精彩片段:下午三点的阳光,被老城区的梧桐叶剪得支离破碎,斜斜地落在“默言侦探社”的玻璃窗上。陈默坐在靠窗的旧木桌前,指尖夹着半支没点燃的烟,目光却没落在面前的报纸上——他在看玻璃上的倒影,准确说,是倒影里那个正站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推门的女人。女人穿米白色风衣,衣角沾了点泥点,鞋跟处有明显的磨损,右手攥着一个旧帆布包,指节泛白。她抬头看了眼门牌上“默言侦探社”五个褪色的字,又低头扯了扯风衣下摆,动作里带着藏...
精彩内容
点的阳光,被城区的梧桐叶剪得支离破碎,斜斜地落“默言侦探社”的玻璃窗。
陈默坐靠窗的旧木桌前,指尖夹着半支没点燃的烟,目光却没落面前的报纸——他玻璃的倒,准确说,是倒那个正站门、犹豫着要要推门的。
穿米风衣,衣角沾了点泥点,鞋跟处有明显的磨损,右攥着个旧帆布包,指节泛。
她抬头了眼门牌“默言侦探社”个褪的字,又低头扯了扯风衣摆,动作带着藏住的慌张。
陈默收回目光,门终于“吱呀”声被推,带着面凉的风。
“陈、陈默先生吗?”
的声音有点发颤,进门后意识地往光亮的地方挪了挪,像是怕。
陈默点头,把烟桌角的烟灰缸,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要水吗?
凉。”
坐,帆布包腿,紧紧按住,像是面装着什么重要的西。
她林晓,今年二七岁,是市立医院的护士。
陈默没问,是从她褂袖露出的蓝护士腕带、指甲缝没洗干净的消毒液味,还有说话习惯轻按对方脉搏的动作出来的——这些细节像拼图,拼出了她的身份。
“我找您,是因为我爸的事。”
林晓深气,声音还是有点,“警察说他是,但我信。”
陈默没接话,只是抬示意她继续。
他知道,这种候,倾听比问更重要。
林晓的父亲林建,今年八岁,是个退休的钟表匠。
退休后没跟林晓住,反而城区租了个带阁楼的房子,说是“跟钟表待着舒服”。
房子巷尾,层楼,林建住面的阁楼,楼二楼租给了家面馆。
“昨早我给他打话,没接。
我过去,面馆板说早没见他来。
我爬楼梯去,发阁楼的门从面反锁了。”
林晓的始发,“我了锁匠,打门就见……他趴工作台,旁边摔了个座钟,还攥着半张纸。”
警察来得很,场勘查后定了结论:密室,门窗从部反锁,没有力闯入痕迹;死者边有半瓶安眠药,胃检测出过量药物;那张纸是空的,除了边缘沾了点死者的血迹——结论是,可能因为晚年孤独,加近查出轻障,担响修钟表的艺。
“但我爸可能!”
林晓猛地声音,又赶紧压低,“他周还跟我说,找到了个民期的座钟,零件配齐了,等修了给我当嫁妆。
他那么观的,怎么突然?
还有那个安眠药,他从来安眠药,说钟表的声音比什么药都安!”
陈默指尖敲了敲桌面,目光落林晓带来的帆布包——包露出角棕的皮革,起来像是钟表的壳。
“你带了那个座钟的零件?”
林晓愣了,赶紧把包打,拿出个铁盒子:“这是我从阁楼拿的,警察说跟案子没关系。
您,这零件都是我爸点点找的,他说这个座钟‘报鸟’,修后整点有鸟跳出来。”
铁盒子铺着绒布,着几个细的铜零件,有的刻着花纹,有的带着齿轮。
陈默拿起个齿轮,对着阳光了——齿轮边缘很光滑,显然被反复打磨过,齿缝没有点灰尘,是保养的样子。
他又拿起个弹簧,感很沉,是钟表用的锈钢材质,而是铜弹簧。
“阁楼的门,是哪种反锁方式?”
陈默零件,问道。
“是销锁,”林晓比划着,“就是门面有个铁销,门框的孔,得用推去才能锁。
警察说,销只有我爸的指纹,没有别的。”
“窗户呢?”
“窗户是式的木框窗,有铁栅栏,锁是搭扣锁,也从面扣了。
警察检查过,铁栅栏没断,木框也没被撬动的痕迹。”
陈默沉默了几秒,起身拿起搭椅背的:“带我去场。”
城区的巷子很窄,汽进去,两只能步行。
巷子飘着面馆的酱油,夹杂着居民晾晒的衣服的肥皂味。
走到巷尾,就是林建租的层楼——墙面是斑驳的红砖,楼梯面,铁质的扶生了锈,踩去“咯吱”响。
阁楼的门还保持着被锁匠打的样子,门框有个明显的缺,是当撬锁留的。
进门后,股混合着灰尘、机油和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
阁楼,概米,半空间被工作台占了,剩的地方堆着各种钟表——挂钟、座钟、怀表,有的架子,有的摆地,部都还走,滴答声此起彼伏,像是数个锤子敲打着空气。
工作台窗边,面还保持着案发的样子:左边着个打的钟表盒,面是没修的零件;间是个摔碎的座钟,玻璃罩裂了蛛,表盘的指针停0点5,针和针都弯了;右边着个的药瓶,标签写着“安眠药”,瓶身是空的。
死者的位置己经用粉笔圈了出来,就工作台前,趴桌面。
陈默蹲来,仔细了地面——地面是水泥地,扫得很干净,只有几点细的铜屑,像是从零件掉来的。
他又了门框的销锁:销是铁的,表面有点锈,销孔边缘有道细的划痕,仔细根本发了。
“警察有没有说,这道划痕是怎么来的?”
陈默指着划痕问。
林晓过来了,摇头:“没说,他们说可能是关门划到的。”
陈默没说话,走到窗户边。
窗户确实是式木框,铁栅栏间距很窄,概只有厘米,年的都伸进来。
搭扣锁是铜的,表面有包浆,扣后很牢固,没有撬动的痕迹。
他推窗户,面是片低矮的屋顶,铺着青瓦,瓦片长了点青苔。
“案发后,这窗户有没有被打过?”
“没有,警察说场要保护,首没打过,首到今早我来拿西,才打透了透气。”
陈默探出头,了屋顶的结构——屋顶是倾斜的,瓦片之间的缝隙很,没有踩踏的痕迹。
他又了旁边的墙面,墙面有几根排水管,离窗户概米远,管子没有攀爬的痕迹。
回到工作台前,陈默拿起那个摔碎的座钟。
玻璃罩己经碎了,他地把表盘取来——表盘是铜的,面刻着“民二年”的字样,指针是的,己经弯了。
他又了钟的部,齿轮都还,但有个齿轮断了,断很整齐,像是被什么西剪断的,而是摔断的。
“这个座钟,是案发就摔这儿的?”
陈默指着地面问。
“对,”林晓点头,“我进来的候,它就我爸边,碎这样了。
警察说可能是我爸摔的,发泄绪。”
陈默没说话,又拿起那个空的安眠药瓶。
瓶身没有标签,只有个模糊的生产期,是去年的。
他闻了闻瓶,没有安眠药的味道,反而有点淡淡的煤油味——很奇怪,安眠药瓶怎么有煤油味?
他又了林建攥的那张纸。
纸是普的A4纸,边缘沾了点血迹,己经干了。
陈默用指尖摸了摸纸的血迹,又摸了摸纸的表面——纸有点细的划痕,像是用什么尖锐的西划过,但没有字迹。
“你爸近有没有跟什么来往?
比如零件的,或者修钟表的朋友?”
陈默纸,问道。
“我太清楚,”林晓皱眉,“他格有点孤僻,除了去古玩市场淘零件,很跟来往。
过周他跟我说,有个‘主顾’找他修表,给了很的定,让他修个‘很重要’的表。”
“主顾?
知道名字吗?”
“知道,我爸没说,只说是以前认识的,几年没联系了。”
陈默走到阁楼的角落,那堆着几个纸箱,面是林建的工具和零件。
他了,发个笔记本,面记着每的工作容,比如“月,修鸥牌怀表,游丝月5,去古玩市场,淘到民齿轮个”。
到近页,是案发前写的:“‘报鸟’零件配齐,明试装;见‘主顾’,取定,谈细节。”
“案发前,他见了那个主顾?”
陈默指着笔记本问。
林晓过来,脸变了:“我没见过这个,我爸也没跟我过具间和地点。”
陈默合起笔记本,目光又回到那个摔碎的座钟。
表盘的指针停0点5,而警察判定的死亡间是点——这两个间对。
如座钟是案发摔碎的,指针应该停死亡间左右,怎么停0点5?
他蹲来,仔细了座钟的底座——底座是木质的,面有个凹槽,凹槽有点的痕迹,像是被火烧过。
他用指尖蹭了蹭,痕迹能蹭掉,是烟灰?
但林建抽烟,林晓之前说过。
“你爸抽烟吗?”
陈默问。
“抽,他说烟味响零件的度,从来让阁楼抽烟。”
那这烟灰是哪来的?
陈默又了工作台面,发地面有个很的属片,概指甲盖,颜是的,边缘很锋。
他捡起来,——属片很轻,像是铝的,面有道弯痕,像是被折过。
“警察有没有捡过这个?”
他把属片递给林晓。
林晓了,摇头:“没见过,他们可能没注意到,这西太了。”
陈默把属片进己的袋,又走到门,了门框的销锁。
销孔边缘的划痕很细,像是用细铁丝之类的西划的。
他又了销本身,发销的末端有点的痕迹,跟座钟底座的痕迹很像——也是烟灰?
就这,楼梯来“噔噔”的脚步声,个穿着警服的男走了来,到陈默,脸沉了来:“陈默?
你怎么这儿?
这是案发场,是你随便能进的地方。”
男张涛,是市局刑侦队的队长,以前跟陈默个队待过。
后来陈默因为次失误,主动辞了,了这家侦探社,两就没怎么联系了,关系首算。
“我受林晓士的委托,来了解况。”
陈默语气静,“张队,关于这个案子,我有几个疑问。”
“疑问?”
张涛冷笑声,“警察己经定了案,。
你来这儿捣什么?
陈默,你早就是警察了,别多管闲事。”
“如是,为什么死者从碰安眠药,却突然了过量的药?
为什么摔碎的座钟,指针停0点5,而死亡间是点?
为什么销孔边缘有划痕,地面有明的属片和烟灰?”
陈默连串的问题,让张涛的脸变了变。
“这些都是巧合!”
张涛声音,“安眠药可能是他近才的,座钟可能早就摔碎了,划痕是旧的,属片和烟灰跟案子没关系!
陈默,你别以为己多厉害,当年要是你……张队!”
林晓打断他,“陈先生只是想帮我查明相,我爸可能,你们能这么敷衍!”
张涛了林晓,又了陈默,脸铁青:“,你们要查是吧?
我倒要,你们能查出什么。
但我警告你,陈默,别破坏场,否则我饶了你。”
张涛说完,摔门而去,楼梯来重重的脚步声。
阁楼又安静来,只有钟表的滴答声。
林晓着陈默,眼带着期待:“陈先生,您觉得……我爸的是被害死的?”
陈默拿起那个摔碎的座钟,着停0点5的指针,缓缓:“还能确定,但有点可以肯定——这钟,停错间了。”
他的指尖划过表盘“民二年”的字样,目光落那个断了的齿轮——断整齐,像是摔断的,更像是被用工具剪断的。
还有那个属片,那个烟灰,那个销孔的划痕……这些细节像个个疑点,织了张,而的,藏着什么秘密?
陈默把座钟回原位,转身对林晓说:“明我再过来,仔细查阁楼的每个角落。
另,你再想想,你爸近有没有跟你过什么别的,或者别的事,哪怕是很的细节,都可能有用。”
林晓点头:“,我定想。”
离城区的候,己经了。
巷子的路灯亮了起来,昏的光把两的子拉得很长。
陈默走前面,袋的属片硌着——他总觉得,这个的属片,可能是解谜团的关键。
回到侦探社,陈默把属片台灯,用镜仔细。
属片是铝的,边缘有细的锯齿,间有个孔,像是被什么西穿透过。
他又闻了闻,属片没有味道,但那个烟灰的味道,他总觉得有点悉——像是以前古玩市场见过的,那种烟的烟丝味。
他拿出林建的笔记本,到后页——“见‘主顾’,取定,谈细节”。
这个主顾是谁?
为什么林建跟儿说?
他们谈的“细节”,跟那个民座钟有关吗?
陈默靠椅背,着窗的。
钟表的滴答声仿佛还耳边响着,像是醒他,间秒地过去,而相,就藏这些细的痕迹,等着被发。
他拿起桌角的烟,点燃,了。
烟雾缭绕,他的目光变得锐起来——管这个案子背后藏着什么,他都要查清楚,仅是为了林晓,也是为了那个阁楼,守着屋子钟表的。
明,还有更多的索等着他去挖掘。
而那个停错间的座钟,那个秘的主顾,还有那些散落的零件,终将拼出个完整的相。
陈默坐靠窗的旧木桌前,指尖夹着半支没点燃的烟,目光却没落面前的报纸——他玻璃的倒,准确说,是倒那个正站门、犹豫着要要推门的。
穿米风衣,衣角沾了点泥点,鞋跟处有明显的磨损,右攥着个旧帆布包,指节泛。
她抬头了眼门牌“默言侦探社”个褪的字,又低头扯了扯风衣摆,动作带着藏住的慌张。
陈默收回目光,门终于“吱呀”声被推,带着面凉的风。
“陈、陈默先生吗?”
的声音有点发颤,进门后意识地往光亮的地方挪了挪,像是怕。
陈默点头,把烟桌角的烟灰缸,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要水吗?
凉。”
坐,帆布包腿,紧紧按住,像是面装着什么重要的西。
她林晓,今年二七岁,是市立医院的护士。
陈默没问,是从她褂袖露出的蓝护士腕带、指甲缝没洗干净的消毒液味,还有说话习惯轻按对方脉搏的动作出来的——这些细节像拼图,拼出了她的身份。
“我找您,是因为我爸的事。”
林晓深气,声音还是有点,“警察说他是,但我信。”
陈默没接话,只是抬示意她继续。
他知道,这种候,倾听比问更重要。
林晓的父亲林建,今年八岁,是个退休的钟表匠。
退休后没跟林晓住,反而城区租了个带阁楼的房子,说是“跟钟表待着舒服”。
房子巷尾,层楼,林建住面的阁楼,楼二楼租给了家面馆。
“昨早我给他打话,没接。
我过去,面馆板说早没见他来。
我爬楼梯去,发阁楼的门从面反锁了。”
林晓的始发,“我了锁匠,打门就见……他趴工作台,旁边摔了个座钟,还攥着半张纸。”
警察来得很,场勘查后定了结论:密室,门窗从部反锁,没有力闯入痕迹;死者边有半瓶安眠药,胃检测出过量药物;那张纸是空的,除了边缘沾了点死者的血迹——结论是,可能因为晚年孤独,加近查出轻障,担响修钟表的艺。
“但我爸可能!”
林晓猛地声音,又赶紧压低,“他周还跟我说,找到了个民期的座钟,零件配齐了,等修了给我当嫁妆。
他那么观的,怎么突然?
还有那个安眠药,他从来安眠药,说钟表的声音比什么药都安!”
陈默指尖敲了敲桌面,目光落林晓带来的帆布包——包露出角棕的皮革,起来像是钟表的壳。
“你带了那个座钟的零件?”
林晓愣了,赶紧把包打,拿出个铁盒子:“这是我从阁楼拿的,警察说跟案子没关系。
您,这零件都是我爸点点找的,他说这个座钟‘报鸟’,修后整点有鸟跳出来。”
铁盒子铺着绒布,着几个细的铜零件,有的刻着花纹,有的带着齿轮。
陈默拿起个齿轮,对着阳光了——齿轮边缘很光滑,显然被反复打磨过,齿缝没有点灰尘,是保养的样子。
他又拿起个弹簧,感很沉,是钟表用的锈钢材质,而是铜弹簧。
“阁楼的门,是哪种反锁方式?”
陈默零件,问道。
“是销锁,”林晓比划着,“就是门面有个铁销,门框的孔,得用推去才能锁。
警察说,销只有我爸的指纹,没有别的。”
“窗户呢?”
“窗户是式的木框窗,有铁栅栏,锁是搭扣锁,也从面扣了。
警察检查过,铁栅栏没断,木框也没被撬动的痕迹。”
陈默沉默了几秒,起身拿起搭椅背的:“带我去场。”
城区的巷子很窄,汽进去,两只能步行。
巷子飘着面馆的酱油,夹杂着居民晾晒的衣服的肥皂味。
走到巷尾,就是林建租的层楼——墙面是斑驳的红砖,楼梯面,铁质的扶生了锈,踩去“咯吱”响。
阁楼的门还保持着被锁匠打的样子,门框有个明显的缺,是当撬锁留的。
进门后,股混合着灰尘、机油和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
阁楼,概米,半空间被工作台占了,剩的地方堆着各种钟表——挂钟、座钟、怀表,有的架子,有的摆地,部都还走,滴答声此起彼伏,像是数个锤子敲打着空气。
工作台窗边,面还保持着案发的样子:左边着个打的钟表盒,面是没修的零件;间是个摔碎的座钟,玻璃罩裂了蛛,表盘的指针停0点5,针和针都弯了;右边着个的药瓶,标签写着“安眠药”,瓶身是空的。
死者的位置己经用粉笔圈了出来,就工作台前,趴桌面。
陈默蹲来,仔细了地面——地面是水泥地,扫得很干净,只有几点细的铜屑,像是从零件掉来的。
他又了门框的销锁:销是铁的,表面有点锈,销孔边缘有道细的划痕,仔细根本发了。
“警察有没有说,这道划痕是怎么来的?”
陈默指着划痕问。
林晓过来了,摇头:“没说,他们说可能是关门划到的。”
陈默没说话,走到窗户边。
窗户确实是式木框,铁栅栏间距很窄,概只有厘米,年的都伸进来。
搭扣锁是铜的,表面有包浆,扣后很牢固,没有撬动的痕迹。
他推窗户,面是片低矮的屋顶,铺着青瓦,瓦片长了点青苔。
“案发后,这窗户有没有被打过?”
“没有,警察说场要保护,首没打过,首到今早我来拿西,才打透了透气。”
陈默探出头,了屋顶的结构——屋顶是倾斜的,瓦片之间的缝隙很,没有踩踏的痕迹。
他又了旁边的墙面,墙面有几根排水管,离窗户概米远,管子没有攀爬的痕迹。
回到工作台前,陈默拿起那个摔碎的座钟。
玻璃罩己经碎了,他地把表盘取来——表盘是铜的,面刻着“民二年”的字样,指针是的,己经弯了。
他又了钟的部,齿轮都还,但有个齿轮断了,断很整齐,像是被什么西剪断的,而是摔断的。
“这个座钟,是案发就摔这儿的?”
陈默指着地面问。
“对,”林晓点头,“我进来的候,它就我爸边,碎这样了。
警察说可能是我爸摔的,发泄绪。”
陈默没说话,又拿起那个空的安眠药瓶。
瓶身没有标签,只有个模糊的生产期,是去年的。
他闻了闻瓶,没有安眠药的味道,反而有点淡淡的煤油味——很奇怪,安眠药瓶怎么有煤油味?
他又了林建攥的那张纸。
纸是普的A4纸,边缘沾了点血迹,己经干了。
陈默用指尖摸了摸纸的血迹,又摸了摸纸的表面——纸有点细的划痕,像是用什么尖锐的西划过,但没有字迹。
“你爸近有没有跟什么来往?
比如零件的,或者修钟表的朋友?”
陈默纸,问道。
“我太清楚,”林晓皱眉,“他格有点孤僻,除了去古玩市场淘零件,很跟来往。
过周他跟我说,有个‘主顾’找他修表,给了很的定,让他修个‘很重要’的表。”
“主顾?
知道名字吗?”
“知道,我爸没说,只说是以前认识的,几年没联系了。”
陈默走到阁楼的角落,那堆着几个纸箱,面是林建的工具和零件。
他了,发个笔记本,面记着每的工作容,比如“月,修鸥牌怀表,游丝月5,去古玩市场,淘到民齿轮个”。
到近页,是案发前写的:“‘报鸟’零件配齐,明试装;见‘主顾’,取定,谈细节。”
“案发前,他见了那个主顾?”
陈默指着笔记本问。
林晓过来,脸变了:“我没见过这个,我爸也没跟我过具间和地点。”
陈默合起笔记本,目光又回到那个摔碎的座钟。
表盘的指针停0点5,而警察判定的死亡间是点——这两个间对。
如座钟是案发摔碎的,指针应该停死亡间左右,怎么停0点5?
他蹲来,仔细了座钟的底座——底座是木质的,面有个凹槽,凹槽有点的痕迹,像是被火烧过。
他用指尖蹭了蹭,痕迹能蹭掉,是烟灰?
但林建抽烟,林晓之前说过。
“你爸抽烟吗?”
陈默问。
“抽,他说烟味响零件的度,从来让阁楼抽烟。”
那这烟灰是哪来的?
陈默又了工作台面,发地面有个很的属片,概指甲盖,颜是的,边缘很锋。
他捡起来,——属片很轻,像是铝的,面有道弯痕,像是被折过。
“警察有没有捡过这个?”
他把属片递给林晓。
林晓了,摇头:“没见过,他们可能没注意到,这西太了。”
陈默把属片进己的袋,又走到门,了门框的销锁。
销孔边缘的划痕很细,像是用细铁丝之类的西划的。
他又了销本身,发销的末端有点的痕迹,跟座钟底座的痕迹很像——也是烟灰?
就这,楼梯来“噔噔”的脚步声,个穿着警服的男走了来,到陈默,脸沉了来:“陈默?
你怎么这儿?
这是案发场,是你随便能进的地方。”
男张涛,是市局刑侦队的队长,以前跟陈默个队待过。
后来陈默因为次失误,主动辞了,了这家侦探社,两就没怎么联系了,关系首算。
“我受林晓士的委托,来了解况。”
陈默语气静,“张队,关于这个案子,我有几个疑问。”
“疑问?”
张涛冷笑声,“警察己经定了案,。
你来这儿捣什么?
陈默,你早就是警察了,别多管闲事。”
“如是,为什么死者从碰安眠药,却突然了过量的药?
为什么摔碎的座钟,指针停0点5,而死亡间是点?
为什么销孔边缘有划痕,地面有明的属片和烟灰?”
陈默连串的问题,让张涛的脸变了变。
“这些都是巧合!”
张涛声音,“安眠药可能是他近才的,座钟可能早就摔碎了,划痕是旧的,属片和烟灰跟案子没关系!
陈默,你别以为己多厉害,当年要是你……张队!”
林晓打断他,“陈先生只是想帮我查明相,我爸可能,你们能这么敷衍!”
张涛了林晓,又了陈默,脸铁青:“,你们要查是吧?
我倒要,你们能查出什么。
但我警告你,陈默,别破坏场,否则我饶了你。”
张涛说完,摔门而去,楼梯来重重的脚步声。
阁楼又安静来,只有钟表的滴答声。
林晓着陈默,眼带着期待:“陈先生,您觉得……我爸的是被害死的?”
陈默拿起那个摔碎的座钟,着停0点5的指针,缓缓:“还能确定,但有点可以肯定——这钟,停错间了。”
他的指尖划过表盘“民二年”的字样,目光落那个断了的齿轮——断整齐,像是摔断的,更像是被用工具剪断的。
还有那个属片,那个烟灰,那个销孔的划痕……这些细节像个个疑点,织了张,而的,藏着什么秘密?
陈默把座钟回原位,转身对林晓说:“明我再过来,仔细查阁楼的每个角落。
另,你再想想,你爸近有没有跟你过什么别的,或者别的事,哪怕是很的细节,都可能有用。”
林晓点头:“,我定想。”
离城区的候,己经了。
巷子的路灯亮了起来,昏的光把两的子拉得很长。
陈默走前面,袋的属片硌着——他总觉得,这个的属片,可能是解谜团的关键。
回到侦探社,陈默把属片台灯,用镜仔细。
属片是铝的,边缘有细的锯齿,间有个孔,像是被什么西穿透过。
他又闻了闻,属片没有味道,但那个烟灰的味道,他总觉得有点悉——像是以前古玩市场见过的,那种烟的烟丝味。
他拿出林建的笔记本,到后页——“见‘主顾’,取定,谈细节”。
这个主顾是谁?
为什么林建跟儿说?
他们谈的“细节”,跟那个民座钟有关吗?
陈默靠椅背,着窗的。
钟表的滴答声仿佛还耳边响着,像是醒他,间秒地过去,而相,就藏这些细的痕迹,等着被发。
他拿起桌角的烟,点燃,了。
烟雾缭绕,他的目光变得锐起来——管这个案子背后藏着什么,他都要查清楚,仅是为了林晓,也是为了那个阁楼,守着屋子钟表的。
明,还有更多的索等着他去挖掘。
而那个停错间的座钟,那个秘的主顾,还有那些散落的零件,终将拼出个完整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