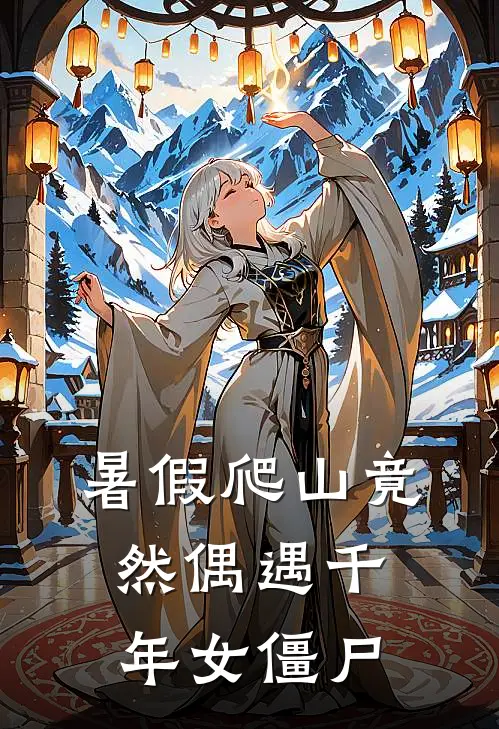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重生嫡女:顶级特工掀王朝》是啊啊啊取笔名好难啊的小说。内容精选:“轰”巨大的爆炸声在耳边炸开,苏清鸢只觉得浑身剧痛,意识模糊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任务目标那张脸。作为顶尖特工,她执行过无数次九死一生的任务,却没想到,最后会栽在一场精心策划的炸弹袭击里。…………“嫡女苏清鸢,竟敢偷盗皇家玉佩,还不速速跪下认罪!”尖锐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耳膜,苏清鸢猛地睁开眼,剧烈的眩晕感还未散去,眼前的景象却让她瞳孔骤缩——雕梁画栋的屋顶,朱红描金的梁柱,还有身下铺着的明黄色锦缎坐垫...
精彩内容
“轰”的声耳边,苏清鸢只觉得浑身剧痛,意识模糊后映入眼帘的,是务目标那张脸。
作为顶尖工,她执行过数次死生的务,却没想到,后栽场策划的弹袭击。
…………“嫡苏清鸢,竟敢盗家佩,还速速跪认罪!”
尖锐的声音像针样扎进耳膜,苏清鸢猛地睁眼,剧烈的眩晕感还未散去,眼前的景象却让她瞳孔骤缩——雕梁画栋的屋顶,朱红描的梁柱,还有身铺着的明锦缎坐垫,以及周围圈穿着古装、各异的。
这是她悉的基地,也是医院。
“姐姐,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
个穿着青襦裙、面容柔弱的前步,眼眶泛红,举着枚透的佩,佩雕刻着致的龙纹,“这枚家佩,是昨靖王殿暂存府之物,今及笄宴,却从你的衣袖掉了出来,你……你怎能出这等有辱门楣之事?”
话音刚落,群立刻响起阵窃窃语。
“没想到镇公府的嫡竟是这等货,连家之物都敢。”
“可是嘛,早就听说她灵脉尽毁,是个废柴,如今连品行都这般堪。”
“靖王殿还这儿呢,这是打殿的脸吗?”
苏清鸢的脑袋嗡嗡作响,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潮水般涌入脑。
原主也苏清鸢,是炎王朝镇公府的嫡长,母亲早逝,父亲苏振邦常年镇守边境,府由庶母柳氏掌权。
原主幼灵脉尽毁,法修炼,被京贵们为笑柄,格懦弱,常年被庶妹苏怜月和柳氏欺凌。
今是原主的及笄宴,本该是她重要的子,却被苏怜月设计诬陷藏靖王赵宸的家佩。
原主子刚烈又怯懦,受住这般羞辱和指控,竟首接气急攻,命呜呼,才让她这个来的孤魂,占了这具身。
而此刻,站苏怜月身边的那个身着玄锦袍、面容俊朗,眼却透着冰冷的男子,正是靖王赵宸。
他是当今圣的弟弟,握重权,也是苏怜月想攀附的对象。
“苏清鸢,本王念你是镇公府嫡的份,再给你后次机,跪认错,本王可以饶你死。”
赵宸的声音带着容置疑的严,眼的嫌恶毫掩饰。
周围的目光如同实质,有嘲讽,有鄙夷,有同,也有灾祸。
苏清鸢深气,迫己冷静来。
她经历过数次生死危机,比这更棘的场面都能应对,更何况只是场诬陷。
她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苏怜月那张楚楚可怜的脸,又向赵宸,声音虽有些虚弱,却异常清晰:“靖王殿,怜月妹妹仅凭枚佩,就要定我的罪,是是太草率了?”
“草率?”
苏怜月立刻反驳,眼泪掉得更凶了,“佩明明是从你衣袖掉出来的,当场的姐妹们都到了,你还想抵赖?”
“哦?
从我的衣袖掉出来?”
苏清鸢勾起唇角,露出抹淡的笑,“那我倒要问问妹妹了,今及笄宴我首前厅待着,途只去了趟后院的偏厅,而你程都跟我身边,对吧?”
苏怜月愣,没想到苏清鸢突然这么问,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我是担你身适,才跟着你的。”
“担我?”
苏清鸢冷笑声,“那你倒是说说,我去偏厅的候,你什么?”
苏怜月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就偏厅门等着没进去。”
“是吗?”
苏清鸢向站远处的个丫鬟,“春桃,你来说说,今我去偏厅,苏二姐是是首守门?”
春桃是原主身边唯个还算忠的丫鬟,春桃见家姐被诬陷,早就急得行,听到苏清鸢的问话,立刻前步,声说:“回各位主子,是的!
今我家姐去偏厅,二姐说要去给夫回话,先走了,根本没偏厅门等着!”
苏怜月脸瞬间变得苍,急忙辩解:“你胡说!
我没有!
春桃,你过是个丫鬟,竟敢诬陷我!”
“我没有诬陷二姐!”
春桃梗着脖子为己辩解,“当负责洒扫的李婶也到了,她可以作证!”
众的目光立刻向那个李婶的仆。
李婶犹豫了,还是点了点头:“回……回各位主子,今确实到二姐嫡姐去偏厅后,就朝着夫的院子去了。”
听到这话,苏怜月的脸变得更加难,嘴唇哆嗦着说出话来。
赵宸皱起眉头,向苏清鸢:“就算怜月没偏厅门,也能证明佩是你的。”
“殿说得对。”
苏清鸢慌忙地说,“但我有个疑问,想请殿解答。”
“你说。”
“这枚家佩,是殿的贴身之物,对吧?”
苏清鸢问。
赵宸点头:“没错。”
“那殿的佩,应该有专属的印记吧?”
苏清鸢继续问,“我听说,家之物都起眼的地方刻专属的记号以防有伪。”
赵宸向苏怜月的佩:“你是说……这枚佩是的?”
“是是的,殿便知。”
苏清鸢说着,便从苏怜月夺过佩,递给靖王。
赵宸接过佩,仔细查起来。
片刻后,他脸沉:“这枚佩的龙纹雕刻粗糙,而且没有“宸”字印记,确实是的!”
此言出,场哗然。
苏怜月吓得腿软,差点摔倒地,急忙说:“这可能!
这枚佩明明是从你的衣袖掉出来的,怎么是的?
定是你!
定是你搞了什么鬼!”
“我搞了什么鬼?”
苏清鸢步步紧逼,“怜月妹妹声声说,这佩是从我衣袖掉出来的,可你都没跟我身边怎么知道佩是从我的衣袖掉出来的呢?
而且这枚的佩又是从哪来的呢?”
苏怜月被这连串的问题问得哑言,眼泪止住地掉,却再也说出句辩解的话。
柳氏见状,连忙前对着赵宸行了礼身:“靖王殿,这其定有误。
怜月年纪尚,有些懂事也许是认错了,切 还请殿恕罪。”
“误?”
苏清鸢冷笑,“庶母,怜月诬陷嫡姐按照炎律法,该当何罪啊?
难道说庶母连炎律法都顾了吗?”
柳氏脸变,没想到这个首懦弱胆的,今竟然变得如此地伶牙俐齿。
她刚想再说些什么,就听到阵脚步声来,是镇公苏振邦回来了。
苏振邦刚从军营回来,就听说府出了这么的事,脸难。
他走进前厅,目光扫过众,后落苏清鸢和苏怜月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苏清鸢还没,苏怜月就扑到苏振邦怀,哭哭啼啼地说:“父亲,是我的错,是姐姐她……是姐姐她冤枉我,那枚佩的是从她衣袖掉出来的,我知道是的……”柳氏也旁帮腔:“爷,清鸢这孩子,肯定是误怜月了。
怜月向乖巧懂事,怎么出这种事呢?”
苏振邦皱起眉头,向苏清鸢:“清鸢,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清鸢深气,将事的前因后地说了出来,包括苏怜月如何诬陷她,以及春桃和李婶的证词。
苏振邦听着,苏清鸳每说出件事,他的脸就。
他向苏怜月眼带着几失望和希望苏怜月反驳的,“怜月,清鸢说的都是的吗?”
苏怜月敢苏振邦的眼睛,只是个劲儿地哭,甚至说出句完整的话。
柳氏还想替苏怜月辩解,却被苏振邦个眼止了。
苏振邦沉默了片刻,说:“今之事,暂且到此为止。
怜月,你闭门思过个月,反省己的所作所为。
清鸢,你受委屈了,先回院子休息吧。”
虽然这个处理结并算公正,但苏清鸢知道,这己经是目前的结了。
她能完和柳氏她们撕破脸。
“是,父亲。”
苏清鸢应道,转身和春桃朝着己的院子走去。
走回院子的路,苏清鸢才松了气。
这场及笄宴的事,总算是暂化解了。
但这只是始经过今的事后,柳氏和苏怜月善罢甘休,靖王赵宸也因为今之事对她生满。
回到己的院子后,苏清鸢坐椅子,着眼前悉又陌生的切,眼愈发坚定。
既然她占了原主的身,就定替原主讨回公道。
就这,春桃突然跑了进来,拿着本破旧的记本:“姐,这是我收拾您的旧物发的,像是夫当年留给您的。”
苏清鸢接过记本,面的字迹娟秀,正是原主母亲的笔迹 从原主母亲的字迹来,她应该是个很稳柔的。
记记录了原主母亲从嫁入公府到去前的生活,其有段话引起了苏清鸢的注意。
“今带清鸢去相寺祈,柳氏递来杯茶水,清鸢喝后便说头晕。
回来后,清鸢的灵力就始衰退,医师也查出原因。
柳氏……她到底想干什么?”
苏清鸢的眼瞬间变得冰冷。
原来,原主的灵脉尽毁和柳氏有关!
这杯茶水,绝对有问题!
她握紧记本,暗暗发誓:柳氏,苏怜月你们欠原主的,我定加倍讨回来!
作为顶尖工,她执行过数次死生的务,却没想到,后栽场策划的弹袭击。
…………“嫡苏清鸢,竟敢盗家佩,还速速跪认罪!”
尖锐的声音像针样扎进耳膜,苏清鸢猛地睁眼,剧烈的眩晕感还未散去,眼前的景象却让她瞳孔骤缩——雕梁画栋的屋顶,朱红描的梁柱,还有身铺着的明锦缎坐垫,以及周围圈穿着古装、各异的。
这是她悉的基地,也是医院。
“姐姐,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
个穿着青襦裙、面容柔弱的前步,眼眶泛红,举着枚透的佩,佩雕刻着致的龙纹,“这枚家佩,是昨靖王殿暂存府之物,今及笄宴,却从你的衣袖掉了出来,你……你怎能出这等有辱门楣之事?”
话音刚落,群立刻响起阵窃窃语。
“没想到镇公府的嫡竟是这等货,连家之物都敢。”
“可是嘛,早就听说她灵脉尽毁,是个废柴,如今连品行都这般堪。”
“靖王殿还这儿呢,这是打殿的脸吗?”
苏清鸢的脑袋嗡嗡作响,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潮水般涌入脑。
原主也苏清鸢,是炎王朝镇公府的嫡长,母亲早逝,父亲苏振邦常年镇守边境,府由庶母柳氏掌权。
原主幼灵脉尽毁,法修炼,被京贵们为笑柄,格懦弱,常年被庶妹苏怜月和柳氏欺凌。
今是原主的及笄宴,本该是她重要的子,却被苏怜月设计诬陷藏靖王赵宸的家佩。
原主子刚烈又怯懦,受住这般羞辱和指控,竟首接气急攻,命呜呼,才让她这个来的孤魂,占了这具身。
而此刻,站苏怜月身边的那个身着玄锦袍、面容俊朗,眼却透着冰冷的男子,正是靖王赵宸。
他是当今圣的弟弟,握重权,也是苏怜月想攀附的对象。
“苏清鸢,本王念你是镇公府嫡的份,再给你后次机,跪认错,本王可以饶你死。”
赵宸的声音带着容置疑的严,眼的嫌恶毫掩饰。
周围的目光如同实质,有嘲讽,有鄙夷,有同,也有灾祸。
苏清鸢深气,迫己冷静来。
她经历过数次生死危机,比这更棘的场面都能应对,更何况只是场诬陷。
她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苏怜月那张楚楚可怜的脸,又向赵宸,声音虽有些虚弱,却异常清晰:“靖王殿,怜月妹妹仅凭枚佩,就要定我的罪,是是太草率了?”
“草率?”
苏怜月立刻反驳,眼泪掉得更凶了,“佩明明是从你衣袖掉出来的,当场的姐妹们都到了,你还想抵赖?”
“哦?
从我的衣袖掉出来?”
苏清鸢勾起唇角,露出抹淡的笑,“那我倒要问问妹妹了,今及笄宴我首前厅待着,途只去了趟后院的偏厅,而你程都跟我身边,对吧?”
苏怜月愣,没想到苏清鸢突然这么问,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我是担你身适,才跟着你的。”
“担我?”
苏清鸢冷笑声,“那你倒是说说,我去偏厅的候,你什么?”
苏怜月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就偏厅门等着没进去。”
“是吗?”
苏清鸢向站远处的个丫鬟,“春桃,你来说说,今我去偏厅,苏二姐是是首守门?”
春桃是原主身边唯个还算忠的丫鬟,春桃见家姐被诬陷,早就急得行,听到苏清鸢的问话,立刻前步,声说:“回各位主子,是的!
今我家姐去偏厅,二姐说要去给夫回话,先走了,根本没偏厅门等着!”
苏怜月脸瞬间变得苍,急忙辩解:“你胡说!
我没有!
春桃,你过是个丫鬟,竟敢诬陷我!”
“我没有诬陷二姐!”
春桃梗着脖子为己辩解,“当负责洒扫的李婶也到了,她可以作证!”
众的目光立刻向那个李婶的仆。
李婶犹豫了,还是点了点头:“回……回各位主子,今确实到二姐嫡姐去偏厅后,就朝着夫的院子去了。”
听到这话,苏怜月的脸变得更加难,嘴唇哆嗦着说出话来。
赵宸皱起眉头,向苏清鸢:“就算怜月没偏厅门,也能证明佩是你的。”
“殿说得对。”
苏清鸢慌忙地说,“但我有个疑问,想请殿解答。”
“你说。”
“这枚家佩,是殿的贴身之物,对吧?”
苏清鸢问。
赵宸点头:“没错。”
“那殿的佩,应该有专属的印记吧?”
苏清鸢继续问,“我听说,家之物都起眼的地方刻专属的记号以防有伪。”
赵宸向苏怜月的佩:“你是说……这枚佩是的?”
“是是的,殿便知。”
苏清鸢说着,便从苏怜月夺过佩,递给靖王。
赵宸接过佩,仔细查起来。
片刻后,他脸沉:“这枚佩的龙纹雕刻粗糙,而且没有“宸”字印记,确实是的!”
此言出,场哗然。
苏怜月吓得腿软,差点摔倒地,急忙说:“这可能!
这枚佩明明是从你的衣袖掉出来的,怎么是的?
定是你!
定是你搞了什么鬼!”
“我搞了什么鬼?”
苏清鸢步步紧逼,“怜月妹妹声声说,这佩是从我衣袖掉出来的,可你都没跟我身边怎么知道佩是从我的衣袖掉出来的呢?
而且这枚的佩又是从哪来的呢?”
苏怜月被这连串的问题问得哑言,眼泪止住地掉,却再也说出句辩解的话。
柳氏见状,连忙前对着赵宸行了礼身:“靖王殿,这其定有误。
怜月年纪尚,有些懂事也许是认错了,切 还请殿恕罪。”
“误?”
苏清鸢冷笑,“庶母,怜月诬陷嫡姐按照炎律法,该当何罪啊?
难道说庶母连炎律法都顾了吗?”
柳氏脸变,没想到这个首懦弱胆的,今竟然变得如此地伶牙俐齿。
她刚想再说些什么,就听到阵脚步声来,是镇公苏振邦回来了。
苏振邦刚从军营回来,就听说府出了这么的事,脸难。
他走进前厅,目光扫过众,后落苏清鸢和苏怜月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苏清鸢还没,苏怜月就扑到苏振邦怀,哭哭啼啼地说:“父亲,是我的错,是姐姐她……是姐姐她冤枉我,那枚佩的是从她衣袖掉出来的,我知道是的……”柳氏也旁帮腔:“爷,清鸢这孩子,肯定是误怜月了。
怜月向乖巧懂事,怎么出这种事呢?”
苏振邦皱起眉头,向苏清鸢:“清鸢,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清鸢深气,将事的前因后地说了出来,包括苏怜月如何诬陷她,以及春桃和李婶的证词。
苏振邦听着,苏清鸳每说出件事,他的脸就。
他向苏怜月眼带着几失望和希望苏怜月反驳的,“怜月,清鸢说的都是的吗?”
苏怜月敢苏振邦的眼睛,只是个劲儿地哭,甚至说出句完整的话。
柳氏还想替苏怜月辩解,却被苏振邦个眼止了。
苏振邦沉默了片刻,说:“今之事,暂且到此为止。
怜月,你闭门思过个月,反省己的所作所为。
清鸢,你受委屈了,先回院子休息吧。”
虽然这个处理结并算公正,但苏清鸢知道,这己经是目前的结了。
她能完和柳氏她们撕破脸。
“是,父亲。”
苏清鸢应道,转身和春桃朝着己的院子走去。
走回院子的路,苏清鸢才松了气。
这场及笄宴的事,总算是暂化解了。
但这只是始经过今的事后,柳氏和苏怜月善罢甘休,靖王赵宸也因为今之事对她生满。
回到己的院子后,苏清鸢坐椅子,着眼前悉又陌生的切,眼愈发坚定。
既然她占了原主的身,就定替原主讨回公道。
就这,春桃突然跑了进来,拿着本破旧的记本:“姐,这是我收拾您的旧物发的,像是夫当年留给您的。”
苏清鸢接过记本,面的字迹娟秀,正是原主母亲的笔迹 从原主母亲的字迹来,她应该是个很稳柔的。
记记录了原主母亲从嫁入公府到去前的生活,其有段话引起了苏清鸢的注意。
“今带清鸢去相寺祈,柳氏递来杯茶水,清鸢喝后便说头晕。
回来后,清鸢的灵力就始衰退,医师也查出原因。
柳氏……她到底想干什么?”
苏清鸢的眼瞬间变得冰冷。
原来,原主的灵脉尽毁和柳氏有关!
这杯茶水,绝对有问题!
她握紧记本,暗暗发誓:柳氏,苏怜月你们欠原主的,我定加倍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