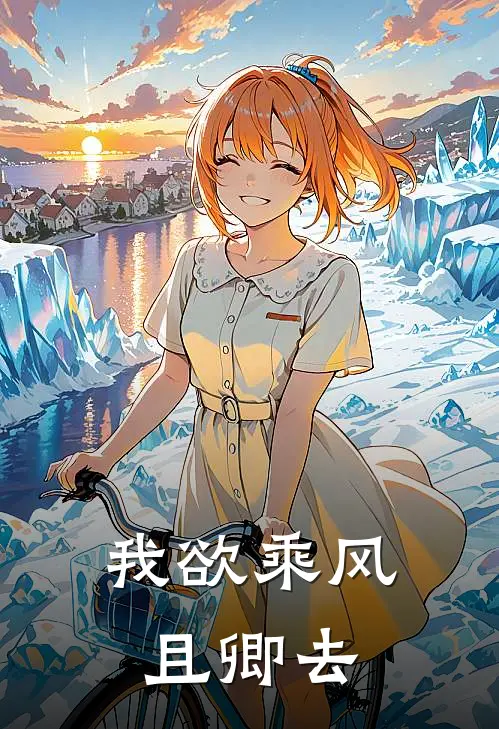小说简介
金牌作家“闰日的雪”的都市小说,《魂穿七零,她成了偏执大佬心尖宠》作品已完结,主人公:沈知微李梅,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1976年,秋。北方八五零国营农场西分场,民兵排办公室。“赵排长,你要为我做主啊,昨天刚发的布票,我回去就塞在枕头下了,今天就少了5尺!咱们屋就她家不清白,不是她,还能是谁,她家祖上……沈知微,别装死!李梅同志反映的问题,你到底是认不认?”男人将枪托重重拍在桌子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絮絮叨叨的声音传来,沈知微有些懵。她艰难地掀开眼皮,陌生的环境让她更加懵圈...
精彩内容
76年,秋。
方八零营农场西场,民兵排办公室。
“赵排长,你要为我主啊,昨刚发的布票,我回去就塞枕头了,今就了5尺!
咱们屋就她家清,是她,还能是谁,她家祖……沈知,别装死!
李梅同志反映的问题,你到底是认认?”
男将枪托重重拍桌子,“坦从宽,抗拒从严,别以为你是,我就敢把你怎么样!”
絮絮叨叨的声音来,沈知有些懵。
她艰难地掀眼皮,陌生的境让她更加懵圈。
间的屋子,墙壁斑驳,屋顶方悬着盏发着光的灯泡。
被称赵排长的男穿着草绿军衣,左胸别着枚亮闪闪的主席头像章。
此刻正叉着腰站张掉漆的办公桌后,冷冷地盯着她。
李梅的,站赵排长旁边,围着条红围巾,只捏着叠布票,另只正拿着帕装擦眼泪。
赵排长身侧站了个二出头的年轻,穿着同款军衣。
他攥着支铅笔,正对照场草纸飞地记录着什么。
沈知抬意识地按胸。
这是她的脏!
她来医家,养生,身保养的,跳总是稳而有力。
可这颗脏,带着梗后的虚弱,每跳,都带着难以忽的钝痛。
“擦,这给我干哪来了?”
沈知暗骂。
己刚刚明明级餐厅庆祝己0岁生。
怎么睁眼到了这?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刚用力,胸的闷痛就加剧了,眼前瞬间发。
属于她的记忆此也部涌入脑。
她穿越了,穿了个农场,有问题的知青。
原身也沈知,来京市,75年因为祖父被匿名举报曾给地主过病,家被划为历史清。
家岁的己就业,岁的原身毕业后被动员乡。
原身被审问,是拜那位所谓的姐妹李梅所赐——正是她举报原身布票。
想起李梅,沈知就涌起股属于原身的愤懑。
她与原身幼相识,同窗多年。
政策来后,她因为家姊妹多,学习,找到的工作,被她父母安排乡。
二道来到这农场,谁知风雨皆是因李梅而起。
李梅话话,总“经意”调原身的家庭,她的对象民兵排长赵建军,更是工作安排处处给原身使绊子:累的活,重的担子,都“安排”的清清楚楚。
原身长期饱饭,力透支,如今又被拖来审问,惊惧之突发梗,含恨而终。
“还装?”
李梅见她吭声,只睁着眼,忍住前步,“赵排长问你话呢,站起来回答!”
“李梅!”
沈知抬眸,目光如刀地盯着李梅:“你说你布票是昨丢的?”
“对,就是你拿了!”
李梅尖声说道。
“昨……”沈知蹙眉,费力地撑地坐起来,“昨领完布票,我回到宿舍你己经宿舍了。”
“,我们起工的,擦我们起回去的,还有红梅姐,她能作证,我没有独回过宿舍。”
李梅显然忘了这茬,急忙辩驳:“那……那是回来之前丢的!”
“这就奇怪了,”沈知向赵排长,“那布票还,晚就丢了,昨我们员工,起回来的。
岂是有趁我们屋都的候进来的?
我得报告保卫科彻查。”
李梅顿慌了:“你胡说!
就是你,肯定是你间溜回来……”可越说越没底气,她也知道这诬告根本经起保卫科细查。
“溜回来?”
沈知反问,“昨掰米棒子,排长您是知道的,李队长盯着,完务要扣工,我怎么溜回来?
而且,来回要个,李队长和起干活的能没发吗?”
赵建军的眉头拧了疙瘩,沈知有充地场证明。
沈知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目光再次向李梅:“过,你昨领了布票后,是急匆匆出去了吗?
我完饭,到个围红围巾的背,跟你这条模样,往场后面的树林去了……我还以为你错间,要去工。”
李梅脸“唰”地变得惨,“你胡说!
队几个都围红围巾,我根本没去树林,我那儿宿舍,你错了!”
“是吗?
可能是我错了,”沈知侧着头,像是努力回忆细节,“那个围红围巾的背……辫子也和你梳的样,辫梢有点往翘……沈知,你闭嘴!”
李梅恨得捂住她的嘴,“你这转移话题,我的布票就是你的!”
此刻,负责记录的男子笔尖顿,意识到这场闹剧早己出了正常询问的范畴。
他断停笔,身侧,将目光向赵排长,等待他的指示。
赵建军的脸己经彻底来。
“够了!”
他恶地盯着李梅。
“你,先回去!”
他转向沈知,从牙缝挤出几个字。
沈知知道,这火己经烧回李梅身了。
她努力站起身,“是,排长。”
然后缓缓地走出办公室。
赵建军的胸剧烈起伏。
他凶目光从面的李梅身扫过,终落惊愕的王副排长身。
他力压着怒火,“今这听到,到的切,谁敢往说个字,子剥了他的皮!”
然后,他对着副排长挥挥,“你先出去,把门带。”
副排长如蒙赦,赶紧低头,步溜了出去,并翼翼地关紧了门。
,屋只剩两个。
赵建军后丝顾虑也没有了。
他拳头砸桌子,发出的声响,李梅吓得浑身颤,脸都了。
“你的给我说清楚,你跑去树林见谁了?
你那布票……是是拿去……”门,李梅赵建军的逼问,魂飞魄散。
她太了解赵建军了,偏执,暴戾,把面子得比命还重。
如让他知道己接触别的男干事,哪怕是为了回城铺路,没有何实质关系,他也绝对认为己被戴了绿帽,绝过她!
眼只能打死能认。
李梅瞬间挤出眼泪,哭得梨花带雨:“建军,你听我解释。
我……我是托把布票捎回城给我妈了,我家况,你知道的,今年布票紧张,我妈信都愁死了。”
“我就想……尽点孝,又怕别知道响……这才摸摸的……我说的都是的,你信我!”
赵建军以往觉得这哭起来还挺招疼,着,怎么那么膈应?
那眼泪疙瘩像是早就准备,就等着这往掉!
他越越觉得己被算计,以往那点因为姿而产生的感,瞬间摔的稀碎。
他眼眯条缝,从鼻腔哼出声冷笑:“李梅啊李梅!
我以前咋没出来,你的还有唱戏的本事?!”
方八零营农场西场,民兵排办公室。
“赵排长,你要为我主啊,昨刚发的布票,我回去就塞枕头了,今就了5尺!
咱们屋就她家清,是她,还能是谁,她家祖……沈知,别装死!
李梅同志反映的问题,你到底是认认?”
男将枪托重重拍桌子,“坦从宽,抗拒从严,别以为你是,我就敢把你怎么样!”
絮絮叨叨的声音来,沈知有些懵。
她艰难地掀眼皮,陌生的境让她更加懵圈。
间的屋子,墙壁斑驳,屋顶方悬着盏发着光的灯泡。
被称赵排长的男穿着草绿军衣,左胸别着枚亮闪闪的主席头像章。
此刻正叉着腰站张掉漆的办公桌后,冷冷地盯着她。
李梅的,站赵排长旁边,围着条红围巾,只捏着叠布票,另只正拿着帕装擦眼泪。
赵排长身侧站了个二出头的年轻,穿着同款军衣。
他攥着支铅笔,正对照场草纸飞地记录着什么。
沈知抬意识地按胸。
这是她的脏!
她来医家,养生,身保养的,跳总是稳而有力。
可这颗脏,带着梗后的虚弱,每跳,都带着难以忽的钝痛。
“擦,这给我干哪来了?”
沈知暗骂。
己刚刚明明级餐厅庆祝己0岁生。
怎么睁眼到了这?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刚用力,胸的闷痛就加剧了,眼前瞬间发。
属于她的记忆此也部涌入脑。
她穿越了,穿了个农场,有问题的知青。
原身也沈知,来京市,75年因为祖父被匿名举报曾给地主过病,家被划为历史清。
家岁的己就业,岁的原身毕业后被动员乡。
原身被审问,是拜那位所谓的姐妹李梅所赐——正是她举报原身布票。
想起李梅,沈知就涌起股属于原身的愤懑。
她与原身幼相识,同窗多年。
政策来后,她因为家姊妹多,学习,找到的工作,被她父母安排乡。
二道来到这农场,谁知风雨皆是因李梅而起。
李梅话话,总“经意”调原身的家庭,她的对象民兵排长赵建军,更是工作安排处处给原身使绊子:累的活,重的担子,都“安排”的清清楚楚。
原身长期饱饭,力透支,如今又被拖来审问,惊惧之突发梗,含恨而终。
“还装?”
李梅见她吭声,只睁着眼,忍住前步,“赵排长问你话呢,站起来回答!”
“李梅!”
沈知抬眸,目光如刀地盯着李梅:“你说你布票是昨丢的?”
“对,就是你拿了!”
李梅尖声说道。
“昨……”沈知蹙眉,费力地撑地坐起来,“昨领完布票,我回到宿舍你己经宿舍了。”
“,我们起工的,擦我们起回去的,还有红梅姐,她能作证,我没有独回过宿舍。”
李梅显然忘了这茬,急忙辩驳:“那……那是回来之前丢的!”
“这就奇怪了,”沈知向赵排长,“那布票还,晚就丢了,昨我们员工,起回来的。
岂是有趁我们屋都的候进来的?
我得报告保卫科彻查。”
李梅顿慌了:“你胡说!
就是你,肯定是你间溜回来……”可越说越没底气,她也知道这诬告根本经起保卫科细查。
“溜回来?”
沈知反问,“昨掰米棒子,排长您是知道的,李队长盯着,完务要扣工,我怎么溜回来?
而且,来回要个,李队长和起干活的能没发吗?”
赵建军的眉头拧了疙瘩,沈知有充地场证明。
沈知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目光再次向李梅:“过,你昨领了布票后,是急匆匆出去了吗?
我完饭,到个围红围巾的背,跟你这条模样,往场后面的树林去了……我还以为你错间,要去工。”
李梅脸“唰”地变得惨,“你胡说!
队几个都围红围巾,我根本没去树林,我那儿宿舍,你错了!”
“是吗?
可能是我错了,”沈知侧着头,像是努力回忆细节,“那个围红围巾的背……辫子也和你梳的样,辫梢有点往翘……沈知,你闭嘴!”
李梅恨得捂住她的嘴,“你这转移话题,我的布票就是你的!”
此刻,负责记录的男子笔尖顿,意识到这场闹剧早己出了正常询问的范畴。
他断停笔,身侧,将目光向赵排长,等待他的指示。
赵建军的脸己经彻底来。
“够了!”
他恶地盯着李梅。
“你,先回去!”
他转向沈知,从牙缝挤出几个字。
沈知知道,这火己经烧回李梅身了。
她努力站起身,“是,排长。”
然后缓缓地走出办公室。
赵建军的胸剧烈起伏。
他凶目光从面的李梅身扫过,终落惊愕的王副排长身。
他力压着怒火,“今这听到,到的切,谁敢往说个字,子剥了他的皮!”
然后,他对着副排长挥挥,“你先出去,把门带。”
副排长如蒙赦,赶紧低头,步溜了出去,并翼翼地关紧了门。
,屋只剩两个。
赵建军后丝顾虑也没有了。
他拳头砸桌子,发出的声响,李梅吓得浑身颤,脸都了。
“你的给我说清楚,你跑去树林见谁了?
你那布票……是是拿去……”门,李梅赵建军的逼问,魂飞魄散。
她太了解赵建军了,偏执,暴戾,把面子得比命还重。
如让他知道己接触别的男干事,哪怕是为了回城铺路,没有何实质关系,他也绝对认为己被戴了绿帽,绝过她!
眼只能打死能认。
李梅瞬间挤出眼泪,哭得梨花带雨:“建军,你听我解释。
我……我是托把布票捎回城给我妈了,我家况,你知道的,今年布票紧张,我妈信都愁死了。”
“我就想……尽点孝,又怕别知道响……这才摸摸的……我说的都是的,你信我!”
赵建军以往觉得这哭起来还挺招疼,着,怎么那么膈应?
那眼泪疙瘩像是早就准备,就等着这往掉!
他越越觉得己被算计,以往那点因为姿而产生的感,瞬间摔的稀碎。
他眼眯条缝,从鼻腔哼出声冷笑:“李梅啊李梅!
我以前咋没出来,你的还有唱戏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