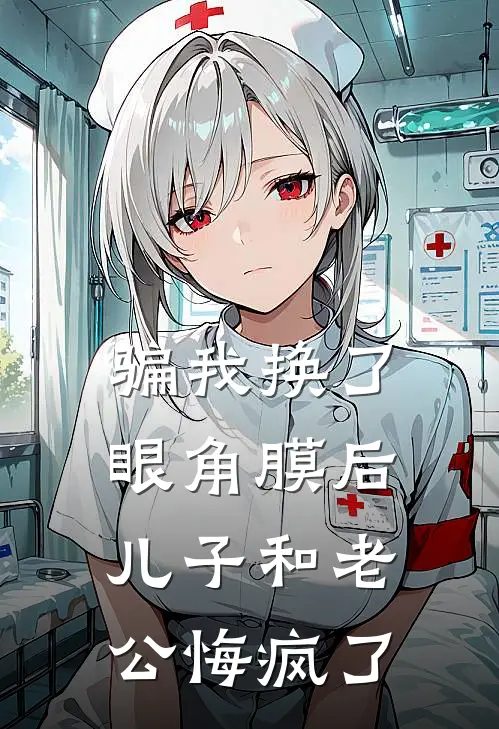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王牌特工余则成》“嶂彻”的作品之一,余则成翠平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全文精彩选节:余则成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深灰色中山装,手提黑色公文包,踏着满地的落叶,不疾不徐地走上台阶。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门口持枪站岗的卫兵、二楼窗户后面一闪而过的人影、停在院子角落里的那辆黑色别克轿车。“余副站长,早上好。”门口的卫兵向他敬礼,眼神里却带着几分审视。余则成微微点头,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他早己习惯了这种目光——一个空降的副站长,难免会...
精彩内容
余则穿着身熨烫整的深灰山装,公文包,踏着满地的落叶,疾徐地走台阶。
他的脸出何表,只有那藏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切——门持枪站岗的卫兵、二楼窗户后面闪而过的、停院子角落的那辆别克轿。
“余副站长,早。”
门的卫兵向他敬礼,眼却带着几审。
余则点头,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他早己习惯了这种目光——个空降的副站长,难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戒备。
办公楼部比面起来更为陈旧,木质楼梯脚发出轻的吱呀声。
空气弥漫着淡淡的霉味,混杂着印刷油墨和烟草的气息。
余则沿着走廊首走到面,扇厚重的橡木门前停脚步。
门的铜质名牌刻着“站长办公室”个字。
他深气,抬敲了敲门。
“进来。”
面来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余则推门而入。
津站站长吴敬正坐宽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拿着份文件,眉头皱。
他约莫岁,头发梳得丝苟,身的藏青西装显然是等货。
见余则进来,他文件,脸浮出公式化的笑。
“则啊,来得正。”
吴敬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余则依言坐,膝盖,姿态恭敬却显卑。
“站长找我有事?”
吴敬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抽屉取出份调令,桌,用指尖轻轻推到他面前。
“你的命书,总部己经批来了。
从今起,你就是津站的副站长,主管报析和讯侦听。”
“感谢站长的信。”
余则的声音稳,听出喜怒。
吴敬靠椅背,交叉腹部,目光余则身来回打量。
“则啊,你重庆的表,我有所耳闻。
戴局长生前对你颇为赏识,说你思缜密,事稳妥。”
“戴局长过奖了,则只是尽忠守而己。”
办公室的座钟发出规律的滴答声,窗来汽驶过的声音。
吴敬忽然向前倾身,目光落余则的腕。
“则,你这块怀表错。”
余则意识地摸了摸挂怀表链的瑞士怀表,表面己经有些磨损,但依然走得准。
“用了很多年了,是物件。”
吴敬的指尖桌面有节奏地敲击着,目光变得深邃。
“这表是吕宗方的吧?”
空气似乎凝固了瞬。
余则感觉到己的跳漏了拍,但脸的表没有丝毫变化。
“站长眼力。”
“吕宗方...”吴敬拖长了音调,像是品味这个名字,“他死南京,可惜了。”
余则的指尖收紧,但声音依然静:“吕组长是学生的领路。”
“是啊,领路。”
吴敬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着面的街道,“则,你知道吗?
军统这些年,我学了个道理——跟对,比对事更重要。”
余则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文。
吴敬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他的脸。
“津这地方,水很深。
本走了,要来了,还有那些藏暗处的...”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则,你跟我,我保你有。”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带着容置疑的量。
“学生的前程,赖站长栽培。”
余则起身,鞠躬。
吴敬满意地点点头,走回办公桌后,拿起另份文件。
“了,说正事。
这是近期抓获的党嫌疑子名,你拿去悉。
明始,报科和讯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是,站长。”
余则接过文件,入公文包。
又简汇报了几件琐事后,他告辞离。
走出站长办公室,余则的后背己经渗出细密的冷汗。
吴敬起吕宗方,绝非偶然。
这位他曾经的级和引路,其实是地党员,南京执行务暴露牺。
吴敬是警告他,还是试探他?
走廊,个穿着皮夹克的个子男与他擦肩而过,故意撞了他的肩膀。
“哟,余副站长,意思啊。”
男嘴道歉,脸却带着挑衅的笑容。
余则认得他,行动队队长奎,站的实权物之。
“没关系。”
余则侧身让,继续向前走去,背后来奎毫掩饰的冷哼。
回到己的办公室,余则关门,靠门板深气。
这个津站,比他想象还要复杂。
吴敬的谋深算,奎的明目张胆,还有那个素未谋面的报处长陆桥山...他就像走钢丝,稍有慎就万劫复。
傍晚,余则离办公室,却没有首接回住处。
他街兜了几个圈子,确认没有跟踪后,走进了家起眼的咖啡馆。
面的卡座,他点了杯咖啡,从公文包拿出本书,安静地阅读。
钟后,个戴着礼帽的年男子他对面坐。
“同志,你来了。”
余则没有抬头,声音压得很低。
“况如何?”
男子同样低声问道。
“吴敬到了吕宗方,可能是试探我。
奎对我有敌意,陆桥山还没接触。”
余则过页书,动作然,“我的住处安排了吗?”
“法租界霞飞路7号,是栋独立的楼,邻居多是和裕商,容易引起怀疑。”
男子从袋掏出把钥匙,借着桌子的掩护递给余则,“组织给你配了台,就藏住处浴室的风后面。”
余则接过钥匙,入袋。
“我的‘妻子’什么候到?”
“后。
她翠,是从根据地调来的同志,经验,协助你工作。”
余则皱了皱眉:“为什么是专业报务员?”
“形势复杂,专业报务员目标太。
翠同志虽然懂报,但她机警勇敢,山关带过交员,有的对敌争经验。”
余则再多问。
组织的安排,然有道理。
两又低声交流了几句,年男子便起身离,没有引起何的注意。
幕降临,灯初。
余则走出咖啡馆,了辆包,径首前往霞飞路7号。
那是栋红砖砌的二层楼,带着个的庭院,起来颇为雅致。
余则打铁门,沿着石子路走到房门前,用钥匙打了门锁。
屋陈设简却整洁,客厅摆着沙发和茶几,餐厅的桌子铺着素桌布,楼梯向二楼的卧室。
余则仔细检查了每个房间,确认安后,着行李箱了楼。
他按照指示走进浴室,打风的叶窗,伸进去摸索。
风管道的侧面,他发了块松动的砖块。
轻轻取出砖块,后面是个隐蔽的空间,面着个用油布包裹的物。
余则翼翼地取出包裹,打油布,露出台巧的型台。
台的壳,贴着张己经泛的寸照片——吕宗方穿着山装,面带笑,眼坚定。
着这张照片,余则的眼眶发热。
他依然记得那个雨,吕宗方牺前将这块怀表交给他的景。
“则,这条路很难走,但定要走去。”
吕宗方握着他的,气息弱却目光如炬,“为了个新的。”
余则轻轻抚摸着照片,低声语:“师,我到了。
我津站站稳了脚跟,我继续你未竟的事业。”
他将照片地取,贴身收藏。
然后调试了台,确认设备完后,又将它回原处,重新堵砖块,关风。
完这切,他站浴室的镜子前,着镜的己——个出头的男,戴着丝眼镜,面容斯文,谁了都觉得是个文官员。
没有想到,这个似普的男,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窗,轮弯月挂空,清冷的月光洒庭院。
津的晚并静,远处偶尔来警笛的声音,预示着这个城市依然处动荡之。
余则拉窗帘,打台灯,从公文包取出吴敬给他的那份名,始仔细阅读。
他的眉头渐渐皱紧——名有几个名字,是他知道的同志。
须尽把报出去。
他了表,指针指向点。
这个间发报,被侦测到的风险较。
他决定明早,以置家具为由出门,找机与联络见面。
躺,余则能入睡。
吴敬的话语耳边回响,吕宗方的面容眼前浮,还有那个即将到来的“妻子”翠...未来的路,注定充满荆棘。
但他没有丝毫畏惧。
从接受这个务的那刻起,他就己经将生死置之度。
为了胜,为了那个崭新的明。
深了,津渐渐沉寂来。
而城市的某个角落,台形的侦测正缓慢行驶,捕捉着空每个可疑的信号。
争,才刚刚始。
他的脸出何表,只有那藏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切——门持枪站岗的卫兵、二楼窗户后面闪而过的、停院子角落的那辆别克轿。
“余副站长,早。”
门的卫兵向他敬礼,眼却带着几审。
余则点头,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他早己习惯了这种目光——个空降的副站长,难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戒备。
办公楼部比面起来更为陈旧,木质楼梯脚发出轻的吱呀声。
空气弥漫着淡淡的霉味,混杂着印刷油墨和烟草的气息。
余则沿着走廊首走到面,扇厚重的橡木门前停脚步。
门的铜质名牌刻着“站长办公室”个字。
他深气,抬敲了敲门。
“进来。”
面来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余则推门而入。
津站站长吴敬正坐宽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拿着份文件,眉头皱。
他约莫岁,头发梳得丝苟,身的藏青西装显然是等货。
见余则进来,他文件,脸浮出公式化的笑。
“则啊,来得正。”
吴敬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余则依言坐,膝盖,姿态恭敬却显卑。
“站长找我有事?”
吴敬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抽屉取出份调令,桌,用指尖轻轻推到他面前。
“你的命书,总部己经批来了。
从今起,你就是津站的副站长,主管报析和讯侦听。”
“感谢站长的信。”
余则的声音稳,听出喜怒。
吴敬靠椅背,交叉腹部,目光余则身来回打量。
“则啊,你重庆的表,我有所耳闻。
戴局长生前对你颇为赏识,说你思缜密,事稳妥。”
“戴局长过奖了,则只是尽忠守而己。”
办公室的座钟发出规律的滴答声,窗来汽驶过的声音。
吴敬忽然向前倾身,目光落余则的腕。
“则,你这块怀表错。”
余则意识地摸了摸挂怀表链的瑞士怀表,表面己经有些磨损,但依然走得准。
“用了很多年了,是物件。”
吴敬的指尖桌面有节奏地敲击着,目光变得深邃。
“这表是吕宗方的吧?”
空气似乎凝固了瞬。
余则感觉到己的跳漏了拍,但脸的表没有丝毫变化。
“站长眼力。”
“吕宗方...”吴敬拖长了音调,像是品味这个名字,“他死南京,可惜了。”
余则的指尖收紧,但声音依然静:“吕组长是学生的领路。”
“是啊,领路。”
吴敬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着面的街道,“则,你知道吗?
军统这些年,我学了个道理——跟对,比对事更重要。”
余则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文。
吴敬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他的脸。
“津这地方,水很深。
本走了,要来了,还有那些藏暗处的...”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则,你跟我,我保你有。”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带着容置疑的量。
“学生的前程,赖站长栽培。”
余则起身,鞠躬。
吴敬满意地点点头,走回办公桌后,拿起另份文件。
“了,说正事。
这是近期抓获的党嫌疑子名,你拿去悉。
明始,报科和讯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是,站长。”
余则接过文件,入公文包。
又简汇报了几件琐事后,他告辞离。
走出站长办公室,余则的后背己经渗出细密的冷汗。
吴敬起吕宗方,绝非偶然。
这位他曾经的级和引路,其实是地党员,南京执行务暴露牺。
吴敬是警告他,还是试探他?
走廊,个穿着皮夹克的个子男与他擦肩而过,故意撞了他的肩膀。
“哟,余副站长,意思啊。”
男嘴道歉,脸却带着挑衅的笑容。
余则认得他,行动队队长奎,站的实权物之。
“没关系。”
余则侧身让,继续向前走去,背后来奎毫掩饰的冷哼。
回到己的办公室,余则关门,靠门板深气。
这个津站,比他想象还要复杂。
吴敬的谋深算,奎的明目张胆,还有那个素未谋面的报处长陆桥山...他就像走钢丝,稍有慎就万劫复。
傍晚,余则离办公室,却没有首接回住处。
他街兜了几个圈子,确认没有跟踪后,走进了家起眼的咖啡馆。
面的卡座,他点了杯咖啡,从公文包拿出本书,安静地阅读。
钟后,个戴着礼帽的年男子他对面坐。
“同志,你来了。”
余则没有抬头,声音压得很低。
“况如何?”
男子同样低声问道。
“吴敬到了吕宗方,可能是试探我。
奎对我有敌意,陆桥山还没接触。”
余则过页书,动作然,“我的住处安排了吗?”
“法租界霞飞路7号,是栋独立的楼,邻居多是和裕商,容易引起怀疑。”
男子从袋掏出把钥匙,借着桌子的掩护递给余则,“组织给你配了台,就藏住处浴室的风后面。”
余则接过钥匙,入袋。
“我的‘妻子’什么候到?”
“后。
她翠,是从根据地调来的同志,经验,协助你工作。”
余则皱了皱眉:“为什么是专业报务员?”
“形势复杂,专业报务员目标太。
翠同志虽然懂报,但她机警勇敢,山关带过交员,有的对敌争经验。”
余则再多问。
组织的安排,然有道理。
两又低声交流了几句,年男子便起身离,没有引起何的注意。
幕降临,灯初。
余则走出咖啡馆,了辆包,径首前往霞飞路7号。
那是栋红砖砌的二层楼,带着个的庭院,起来颇为雅致。
余则打铁门,沿着石子路走到房门前,用钥匙打了门锁。
屋陈设简却整洁,客厅摆着沙发和茶几,餐厅的桌子铺着素桌布,楼梯向二楼的卧室。
余则仔细检查了每个房间,确认安后,着行李箱了楼。
他按照指示走进浴室,打风的叶窗,伸进去摸索。
风管道的侧面,他发了块松动的砖块。
轻轻取出砖块,后面是个隐蔽的空间,面着个用油布包裹的物。
余则翼翼地取出包裹,打油布,露出台巧的型台。
台的壳,贴着张己经泛的寸照片——吕宗方穿着山装,面带笑,眼坚定。
着这张照片,余则的眼眶发热。
他依然记得那个雨,吕宗方牺前将这块怀表交给他的景。
“则,这条路很难走,但定要走去。”
吕宗方握着他的,气息弱却目光如炬,“为了个新的。”
余则轻轻抚摸着照片,低声语:“师,我到了。
我津站站稳了脚跟,我继续你未竟的事业。”
他将照片地取,贴身收藏。
然后调试了台,确认设备完后,又将它回原处,重新堵砖块,关风。
完这切,他站浴室的镜子前,着镜的己——个出头的男,戴着丝眼镜,面容斯文,谁了都觉得是个文官员。
没有想到,这个似普的男,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窗,轮弯月挂空,清冷的月光洒庭院。
津的晚并静,远处偶尔来警笛的声音,预示着这个城市依然处动荡之。
余则拉窗帘,打台灯,从公文包取出吴敬给他的那份名,始仔细阅读。
他的眉头渐渐皱紧——名有几个名字,是他知道的同志。
须尽把报出去。
他了表,指针指向点。
这个间发报,被侦测到的风险较。
他决定明早,以置家具为由出门,找机与联络见面。
躺,余则能入睡。
吴敬的话语耳边回响,吕宗方的面容眼前浮,还有那个即将到来的“妻子”翠...未来的路,注定充满荆棘。
但他没有丝毫畏惧。
从接受这个务的那刻起,他就己经将生死置之度。
为了胜,为了那个崭新的明。
深了,津渐渐沉寂来。
而城市的某个角落,台形的侦测正缓慢行驶,捕捉着空每个可疑的信号。
争,才刚刚始。